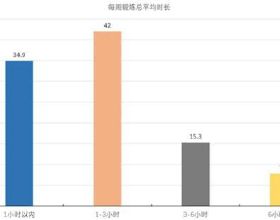在曲阜市周公廟的西北側,孔林林道以西,有一處隆起的高地,高敞寬闊、林木蔥鬱,人稱“伯禽臺”。相傳,這裡是魯國第一代國君伯禽向西望父的祭祀之地。因此,當地人又叫其“望父臺”。
《東野志》載:“古魯城舊跡望父臺,在城北一里。魯公築高臺以望西京,思念其父。”伯禽,周公旦之子。據《魯周公世家》記載,公元前11世紀中葉,周武王伐紂克殷後,“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去世後,成王年幼,周公擔心天下人聞聽武王訃訊而背叛朝廷,就登位代成王主持國家政權。“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伯禽在位46年,謹遵父親教誨,把魯國治理得井井有條。閒暇之餘,他時常想念遠在鎬京的父親,於是在魯城中用土築了一個高臺,經常登上去西望鎬京,藉以寄託對父親的思念之情。
先秦時期,魯國城內部建築佈局基本採用宮廟一體的格局。在魯國城中,以周公廟為中心的宮城及宮城周邊,居住著魯國王室成員等高等級貴族。經勘探,望父臺周圍是魯國城內的一處大墓地,那麼對應的,高等級貴族的邦墓就在望父臺。望父臺整體呈長方形,中心位置略高於四周,佔地面積約18萬平方米。原封土東西長80米,南北寬60米,位於魯國城中部偏西,今殘存封土不過六七米見方,高約二米左右。
2017年—2018年,為配合魯故城遺址公園建設規劃,考古隊對望父臺墓地進行發掘。發掘共有東周至漢代灰坑87座,水井4眼,溝4條,墓葬33座,馬坑2座。灰坑時代為戰國到漢代,墓葬時代自西周末到戰國早期,其中大型墓葬1座,餘為中小型墓。南北成排,東西成列,夫妻並穴現象普遍。墓地經過規劃,存在時代稍早的中型墓葬墓居中,周邊為幾座小型墓,或為小的家族墓地單元。出土有青銅器、陶、玉石器、骨器等,銅禮器以舟、匜、盤、鼎、豆、敦為主,其中舟最為常見,陶器以鬲、罐為基本組合,陶鬲每墓多隨葬1件。男性墓隨葬有兵器和車馬器,女性墓葬不隨葬兵器,部分隨葬車馬器。女性墓葬人群構成比較複雜。同時發現大量祭牲、荒帷遺蹟現象。

2019年初,考古隊員在望父臺西北部發現一座長約7.3米、寬約6.2米的墓葬,將其命名為M1號,並對墓葬展開了發掘。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和玉器(上圖),造型精美,其中玉器的數量更達一百多件。考古隊員推測,這是曲阜魯故城遺址內目前儲存最完整的一座高等級墓葬。令人震驚的是,這座墓葬中出土的部分青銅器和骨器是首次出現於魯故城遺址中。它們為何會出現在這裡,墓主人又是何身份?
在M1號墓葬中並未發現隨葬兵器,且有大量隨葬車馬器,光是鑾鈴就有四個。鑾鈴是古代馬車上的一種裝飾物。上部呈中空扁球形,正面開有放射狀孔,內含銅丸,下部為梯形中空底座,可安插在馬車上。一般來說,出土的鑾鈴數量越多,墓葬的等級越高。戰國時期,一輛馬車上的鑾鈴數量不等,通常可放兩隻。因此考古隊初步判斷,M1號墓葬主人為大夫或卿級別官員的夫人。
荒帷在先秦典籍中多次出現,即棺罩,是對死者生前居室帷幄一類的模仿。M1號墓葬中發現大量排列整齊的水晶珠、瑪瑙觿、瑪瑙環、玉珩、玉璜等玉器。大量裸露在外的精美玉器讓考古隊相信荒帷的存在。此後在棺槨之間出土的銅鈴上,發現了殘留的絲織物,這是荒帷存在的有力證據。銅鈴聲音悅耳動聽,一般綴在荒帷的四周來對其固定。西周時期,荒帷的掛飾主要是銅魚。春秋早期,銅鈴已經被用於裝飾荒帷。到了戰國時期,珠玉成為了荒帷掛飾中的主角。大量精美玉器和銅鈴的存在,足以說明墓葬主人身份的高貴。
此外,在M1號墓葬中出現了魯故城遺址中從未出現的兩件器物,鳥蓋瓠壺和鷹形器物。在古代,燻爐有薰香或取暖的作用,一般採用青銅材質,使其堅實耐用。鷹抓蛇體現著大自然生物鏈裡的自然法則,鷹抓蛇造型的燻爐在魯故城遺址中並未出現過,帶有北方草原色彩。瓠壺因形似瓠瓜而得名,瓠瓜是葫蘆的變種,瓠壺也是一種盛液體的器物。南宋《雲麓漫鈔》記載:“周,又有瓠壺,形長一尺二寸六分,闊五寸,口徑一寸,兩鼻有提樑,取便於用。”據此可推測晚至周代,瓠壺就已出現。瓠壺一側有把手,頸部微微彎曲,還有一個帶鏈條的壺蓋,器形較為獨特。壺蓋上,鳥頭上昂,尾羽較短,周身佈滿點狀或線狀的紋飾,身形飽滿。考古隊將其與行唐故郡遺址出土的瓠壺比較,發現造型極為相似。行唐故郡曾是北方鮮虞白狄部落故地,專家為此大膽猜測,或許墓葬主人是北方部落遠嫁到魯國的女子。望父臺M1號墓地的發掘,填補了魯故城春秋時期墓葬的缺環,進一步推動了魯國邦墓墓地佈局及葬制葬俗研究。
車水馬龍的街道見證著曲阜當下的繁華,綠樹環抱著古建築,靜靜地訴說著兩千多年的歷史故事,我們在熱鬧的市井氣息中尋覓著古人的生活痕跡。望父臺墓地的發掘為研究春秋時期魯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面貌提供了寶貴資料。(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張依盟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