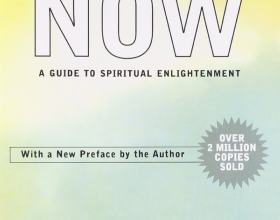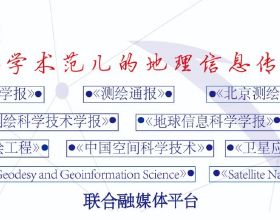卷首語
在主動引借西方再現寫實美術而開啟中國畫學新紀元的現代性轉型中,中國畫反映現實生活、塑造現代人文形象、構建現代社會精神家園的表現能力均發生了質的改變,中國畫已成為中國現代社會一種不可替代的精神審美表徵。但中國畫的這種現代性轉型在藝術語言上,並非是一味地透過引進西方寫實造型、焦點透視來改造中國畫的意象性與平面性,或借用媒介觀念來消解中國畫筆墨邊界的底線,而是在被改良與被改造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反彈和迴歸,甚至改造得多麼深,也便會迴歸得多麼遠。突破邊界與回溯傳統,往往成為20世紀以來中國畫現代性轉型互為拮抗的兩種力量。文人畫並沒有在中國畫的這種現代性轉型中被徹底消解或被終結,這似乎暗示著什麼?或許,我們在文人畫之前習慣性地加上“傳統”這個前置詞,只是20世紀對中國畫推行現代性轉型的某種誤判。文人畫本就是中國畫的一種典型樣態,它和西畫那種以滿足視感觀賞為目標的繪畫,本就不是一類繪畫形態。這和此種藝術是否傳統與現代,是農耕文明的藝術還是工業文明的藝術,可能本就沒有任何關係。這只是我們從西方實證主義產生的觀看藝術方式、從西方藝術與社會形態演變之間所形成的藝術進化模式而對其進行的曲解與想象。眾所周知,奠定中國畫審美理想的莊禪思想是種內觀美學系統,它不是透過主觀反映客觀的模仿,而是透過主觀把握客觀的體驗,繪畫成為主觀對視覺世界的意念控制。山水畫不同於模仿空間真實的風景畫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山”與“水”是作為觀念指代而在畫面上進行的意念化重構。黃賓虹的“黑團團裡墨團團,黑墨團中天地寬”,就是透過筆墨重構“山”與“水”的意念創造。這裡的山水絕不是完全視覺化的所見風景,而是筆墨意念之中“山”與“水”的符號。顯然,“筆墨”是中國畫實現意念體驗的轉換物。山水意念看似是完全主觀的,但筆墨語系卻呈現出一種苛刻的法書美學的規則性。也即,墨雖可呈濃、淡、潑、破、積、焦、宿的千變萬化,但墨僅為筆之象,墨絕不是可以隨意呈現的任意一種形態,而是必須遵從以筆為骨的美學原則。只有具備“平、留、圓、重”的筆法,才能在“變”中呈現真正意義上的內觀之美。20世紀中國畫的現代性轉型在汲取西畫寫實造型的同時,大多是以犧牲筆墨法度為代價的。失去了筆墨法度也便必然弱化筆墨的精妙與精萃,中國畫的內觀體系也便隨之水土流失。於是,中國畫成了另一種西畫演繹,變成現實的反映者與模仿者,意境、境界、格調這些從筆墨體系生髮的中國畫品格也便消失殆盡。因而,中國畫總是在走向描繪視覺真實的過程中出現迷茫,在轉型中不斷折返。其實,文人畫的筆墨法度正像芭蕾舞對形體進行“開、繃、直、立”的終生修習一樣,沒有這四個基本要素也便失缺了芭蕾舞體形與舞姿的美學核心。文人畫的筆墨絕不是一種僵死的所謂“程式”,而是由這種材質決定並通過歷代大師名家探索與積累的一種藝術語言的審美規律,是中國畫固屬的美學核心。與西方寫實造型的嫁接、與抽象形式構成的融合,最多都只是在文人畫筆墨的外圍或邊緣進行所謂的變革,而鮮能深入到這個畫種美學的核心。這或許正是中國畫現代性轉型不斷出現折返溯源的緣由。因為在根本上,這種中西嫁接就始終存在兩種異質文化、兩種美學體系的牴觸。而文人畫的筆墨體系與美學高度卻一直屹立在那裡,不論你如何改良和變革。在某種意義上,筆墨形成了這個藝術品種的“遺傳隔離”機制,使其免受其他物種的浸染與混雜。
尚 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