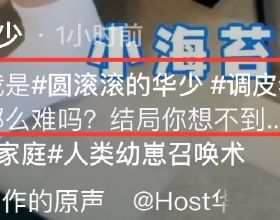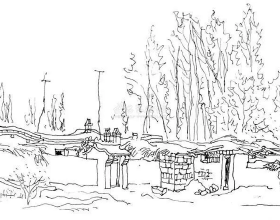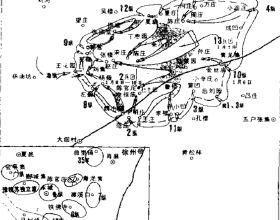整理/雨驛
主題:關於父親的詩與思——關於向迅《與父親書》
時間:2021年7月18日19:00
地點:武漢卓爾書店
嘉賓:向迅散文作家
李修文作家、影視編劇
用自己的寫作讓父親重新誕生一次
李修文:向迅這本《與父親書》,是以父親為主體的散文集,有許多人之為人的難關、要害,和退無可退也進無可進的地方。尤其在父親晚年身患重病那樣一個關口上,當一個人走到生命盡頭,人的尊嚴是如何呈現的?這種被動的呈現既要靠一個兒子對父親真正的體恤,同時一個作家也要有足夠的審美、足夠的力量,把那樣一個左右為難,生也不得死也不得的父親精確表達出來。這都體現一個作家細緻豐富、非常闊達的能力。我在為這本書寫的推薦語中講:“某種程度上,向迅是用他的寫作,使他的父親又重新誕生了一次。”父親在兒子的追懷、體恤、靜穆中,重新出生了一次。
下面請向迅來談一談寫作的緣起,以及創作當中的一些歷程。
向迅:今天到武漢來,在百度上檢視地圖,這個地方好像離同濟醫院很近。我父親生病之後在同濟醫院度過了半年時間,所以今天到這裡感觸還是比較深的。這本散文集的寫作前後跨度五年。最早的一篇是我父親生病的時候,我陪護結束回到江蘇,把一些細節性的東西記錄下來,當時的預期是一部長篇非虛構作品。但直到現在有些事情對我來說,都還是不能完全去面對,所以後來沒有寫下去。現在收錄在這個散文集裡面的有兩篇文章,就是從長篇非虛構裡面拿出來的。
李修文:《與父親書》是這半年以來,我經常出差時在高鐵上看的一本書。許許多多細節都非常打動我,最打動我的是後來父親下樓很困難,他嘴裡不斷髮出若有似無、類似號子般的聲音。年輕時大家做工力氣不足時,工友們一起喊出號子來,那是面對生存艱難,要自己給自己打氣,從困難中誕生出來的聲音,深深長在我們生命中。當年的父親,他面向的是無盡的、廣闊的生命,是許許多多的可能性,也可以說他面向的是希望,是眼前還未展開的生活——只要透過我的努力和奮鬥,我喊出號子來鼓舞自己的生命力,我就可能幫助自己、幫助家庭創造一個有質量的人生。但是當人生將盡,他的生命力受到極大限制,當他下樓都非常困難的時候,那是他面向無能發出的吼聲——面向一切人生的根本侷限。我們看到當生命在生死存亡之間,一個個體到底經由什麼樣的撕扯,最終又經受住什麼樣的痴纏,最終呈現出什麼樣的存在。
我看到這些細節的時候感動淚目。我們寫文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人生是複雜的,黑白之間、彩色與無色之間還存在著許許多多幽微曖昧、難以描述的地帶,這就是我們的人生。我們的人生有時候很難用簡單的是非曲直、道德與非道德來清清楚楚把它表明出來,其實這就是這個文體最高的責任和使命,或者說也是它的最大資本。恰恰在這些方面,我們這幾十年的散文,好像沒有獲得一種本質的進步。所以向迅那麼冷靜、客觀地呈現出複雜的片斷、細節,來激發我們的主觀想象力。他作為一個呈現者,會使我們自行腦補一個細節到一個細節、一個人生片斷到另外一個人生片斷。我們作為一個讀者,作為一個感受者,要自發完成這種主動性,這是非常棒的。
新一代的散文作家已經重新出發了
李修文:我還特別感動一點是,他不是賣慘式的寫作,而是非常冷靜、客觀。美國華裔著名文學評論家、從故紙堆裡打撈出張愛玲、沈從文的夏志清先生講,中國文學非常不同於西方文學的地方在於,西方敘事往往篤信人類必然承受、超越我們要經受的苦難。而中國文學之所以有魅力,之所以有其他民族的作品不能替代的生命力,恰恰在於中國人感受到這個世界上註定有許多困難、悲劇使你沒有辦法承受或者超越,因此生命才被稱為真正的悲劇。如果每一次我們都有辦法、有能力把它超越過去,請問我們還能體察出真正的悲劇嗎?我們還能真正地活在眼見的悲劇中、重新出發建立一個日常生活或者我們內心裡的自我嗎?中國文學在這些方面做出了非常傑出的貢獻。我們不能說向迅的這本書是這樣一條道路上多麼傑出的樣本,但事實上他行走在這條道路上。
這本書很多細節、很多篇章迷人的地方在於,我承認這種失敗,我承認我父親的身體、我父親今天所遭遇到的生命的阻隔與中斷,這種戛然而止,是無論我作為一個兒子,還是作為我父親的主體,都沒有辦法去超越、克服的悲劇。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並不是非常簡單地“他多麼有生命力”“我是多麼堅強樂觀”,不是,父親的膽怯、驚慌、恐懼,甚至他觀察到父親蜷縮著、恐懼著,有大量這樣的細節描摹。這就是生命力,我們的生命力並不體現在所謂的樂觀當中,我們承認這種恐懼,承認我們沉浮於人類缺陷這樣一個事實。經由一個作家的描述,經由這個兒子的重新發現和打撈,我們會發現一個獨特的父親——一個既等同於其他的、居於廣大無名之輩當中的一員,同時又是被其他父親影響、不能被取代的父親,我們看到他準確地被呈現。
我們認同作為一個生命所要面臨的事實,我們既不是一味地向上,也不是一味地淪落。我們平靜注視著我們的生命和存在,從這樣一種漫長的凝視出發,致力於去發現每個生命虛弱的時刻,致力於去探討在這樣的時刻里人之為人的可能性。這就是這本書以及更多作家們近些年來視角越來越豐富,因此帶給我們越來越多寬廣的體驗、越來越遼闊的文字的原因。所以我感到新一代的散文作家,事實上他們已經重新出發了。
我不知道向迅怎麼看,接下來寫散文你會怎麼樣去寫?有什麼樣感興趣的題材,或者會做什麼樣的思考?可以交流一下。
向迅:剛才修文老師提到苦難敘事,當我們生活中面臨親人遭遇重大疾病可能離你而去的事情,當你親自用筆書寫的時候,你會不會寫一些苦難?很多人寫的時候可能帶淚,我覺得這是不可取的。我也沒有想賺取讀者的眼淚,就是想客觀真實,呈現我父親生命中的那些時光。
今年修文老師在我們雜誌開了一個專欄,寫他童年的事情。修文老師的童年也遭受很多苦難,但是我們看他的散文,最後超越了苦難,他的人生是有昇華的。雞湯文可能就是賺取讀者的眼淚,而真正寫文章要超越販賣苦難這個心理。
我們書寫父親是為了
維繫歷史的一個任務
向迅:父親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民,可能他的生命逝去就逝去了,就像我們周圍很多人逝去一樣。除了親人每年中秋和過年會想起他們,其他時刻他們都是被遺忘的狀態。村莊也好,城市也好,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逝去,我們能夠想起誰呢?所以我想為父親寫點東西,不能讓他像我們村子裡其他人一樣消失就消失了。我在後記中說,我們寫父親是為了維繫歷史的一個任務。因為我們的歷史是一代接一代人延續下來的,我們每個人的父親都是其中一環。
我們是一個大家族,我曾準備挖掘家族的故事,給家族寫一本書。但在做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前輩細數自己三代以上的親人,經常說不出他們的名字。當時我就有緊迫感,隨著時間的流逝,關於父親的很多細節我可能也會忘記。我現在回憶父親在同濟醫院、在家裡的細節,很多都想不起來了,現在很後悔沒有當時把它如實記錄下來。
剛才修文老師也說,我渴望寫一個不一樣的父親。雖然我們每個普通人,生活遭遇、物質生活可能比較雷同,但是作為一個生命個體,他在這個世上肯定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地方。寫出不一樣的父親就是我想把父親最真實的一面體現出來。親情散文為什麼容易受到詬病?就是因為我們可能對親人會手下留情,對他進行美化、修飾,把他一些不怎麼光亮的部分隱藏起來。而我儘可能地把最真實的生活呈現出來,包括我父親很多不是英雄的一面,面對疾病他的膽怯、恐懼。這才是一個真實的父親。
李修文:就像向迅剛才講的,我今年在《雨花》雜誌開了一個專欄,在回憶童年的過程當中,許許多多對童年的感受被激活了。而這種被啟用,這種回望和關照,某種程度上一定是帶有想象、虛飾,乃至於審美的部分。在我看來,恰恰因為這種回望、關照,記憶被重新拼貼和組合。有一句話說:“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開始了。”這恰恰是文學的要義。經由這樣的重新發現,我們這樣的一個人或者我們這樣一個文字到底可以何去何從?
當這個念頭湧現之後,實際上我誕生出一種態度——透過這次寫作我完成一次清洗。比如我小的時候在鄉村,因為父母在城裡工作,經常是今天在這家,明天在那家。一個傳統的被認為像田園詩般、桃花源式的父慈子孝的鄉村,我當然見識過。但是,就像向迅寫作中呈現的,那個抽空我們全部抒情、讚美以及肯定他人能力的那個鄉村同樣存在。
比如我小時候老是念念不忘一個瘋子。他當然是真瘋,但是中國很多心理有疾病的人,實際上是間歇性的精神病人,時好時壞。因為我們無法認定他什麼時候是好的、什麼時候是壞的,他居然拿他的瘋狂要挾大家。他本來是不幸的人,可是當他迎來清醒的時刻,作為一個人來講,我們當然要祝願他迎來了正常。可是在正常當中,他的瘋狂馬上得到脅迫他人的合法性,他頓時用自己的瘋狂給他人造成極度的壓迫,他甚至每天進村的時候都會喊,你們注意,哪家的瘋子回來了。
父親說如果病好了回去把花園建設好
李修文:我們行進到現在,每個人作為成年人,當我們面臨這個世界的諸多難處,我們有沒有可能持續不斷地因為恐懼、因為過多的想象產生也許是過度的迴響,來產生不斷的對峙?我們有沒有可能重新得到某種正解?同時我也想,那樣一種童年生活往往給我們內心造成一些不快,甚至是創傷,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這樣一次寫作,清洗完我們的內心,讓我們真正和過去說一聲再見,說一聲“你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們互不相送”。我們總是有過多的痴嗔,過多的貪戀,過多地依存於傷痕,以使自己所謂的成功、前進變得更加其來有之。我們如何平靜地跟自己過去經歷過的生活,既平起平坐,又不再互相糾纏。
我寫這本書,包括寫《詩來見我》,說到底出發點非常簡單,就是在疫情當中,重新覺得“文章千古”這句話變得多麼重要。在相當程度上人和人之間要變成一座孤島的時候,我們如何救自己、我們如何說服自己現在的生活仍然可以活下去?如何在文章中找到各種各樣的前賢、先輩?先輩經歷過的種種苦楚,如何跟我們的生活來印證、來重疊?我們又從這種印證和重疊當中,能夠受到什麼啟發,以鼓舞我們更加平靜,更加能夠與自己和解,更加能夠接受看起來兵荒馬亂的世界?這就是我透過寫作所得到的一些教益。
向迅:寫這本書,其實是為了走近父親,為了瞭解、更理解父親。我父親就是一個沒有什麼遠大理想的中國農民,一輩子就是養家餬口,再建一棟房子。但是我在寫作過程中發現我父親還是有理想的,即使在他生病的最後時刻,他還對我講說:“如果病好了,回去把花園建設好。”因為我們家有很大一個院子,父親是很愛花兒的人,他走到全國各地都會收集喜愛的花種回去。現在我們老家的花園每到春天都會奼紫嫣紅,不僅是我家的花園,所有我們家族的院子裡都有開花。
我們小時候家裡因為是農村,條件不是很好。很多時候交不起學費,就會怪父親:“學費也不貴,怎麼交不起?你們怎麼沒有志氣?”後來我反思,父親其實是挺偉大的人,他自己沒有讀過什麼書,卻把幾兄妹相繼送到讀大學。我後來瞭解到,我父親是特別聰明、很有才華的人,如果他能多讀書可能會是一個藝術家,因為他真的無所不能,周遭的事情,基本一看就會。母親為什麼會嫁給他,就是我外婆覺得父親會手藝,養家沒問題。
剛才說到“和解”這個詞,我和父親每次打電話的時候,真的沒什麼話說。和母親我能說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都可以,但是跟父親最多五分鐘、十分鐘就沒有什麼話說了。有一次記得很清楚,父親在電話裡說,“怎麼跟我沒話說?”父親離開後,我那段時間總會夢見父親,夢見他還活著,在心裡面留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給他。卡夫卡曾給他父親寫信,說:“我寫作就是說那些,我無法撲在你的懷抱裡哭訴的話。”我寫《與父親書》可能也只是一個開頭,後面還有許許多多關於他的事情,可能還會寫。
把複雜的父親呈現出來
這樣的寫作才更具意義
提問:請問向迅老師,在《與父親書》中,您的父親是一個無名的父親,但在閱讀過程中我看到自己父親的影子。您怎樣理解這裡面無名和共鳴的關係?
向迅: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們的父親作為個體的人,在大歷史背景下都是無名之輩。數千年以來,世界上古今中外我們能說出名字來的,其實少之又少,極大部分人都是無名之輩。雁過留聲,但人消失可能就不存在、被遺忘了。為什麼要寫?就是想把這段情感留下來。
李修文:我幫他補充兩句。這就是文學書寫的價值和意義。我們的歷史裡充滿了戰勝者,充滿了他們的功業、他們的成就。但是我們看一下歷史書當中有沒有父親?可能會有,但也多是在政治權謀人生、浩大歷史程序中那些標誌性事件當中,比如九王奪嫡,父子相殘,這時候中國式的父親就存在了。某種程度上,在中國的文學作品,尤其在我們的歷史書裡,一個生命意義上的父親一直是抽空的,這恰恰是歷朝歷代許許多多寫作者給後世造成的匱乏。
為什麼中國人老是不會做父親?因為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中並沒有太多的父親。我們有的只是戰勝者、勝利者。這就是我們今天作為一個作家,以及像《與父親書》這樣作品的意義。當我們要面向未來、面向現代、面向更加廣闊的民族道路的時候,我們應當有人從細部開始入手,重新建立那些無名者的角色,使一個可能的父親來到我們的生存當中,而不是來到我們的神龕上只供我們膜拜。所以這就是這本書的,或者說更多的像向迅式的寫作的意義。
提問:都說最親密的人往往最難寫,我們跟自己的父親、跟自己家庭的牽絆都非常深,您如何客觀寫出一個真實的父親?一般可能要把自己剝離出來,把自己作為第三者,有一種拿自己開刀的感覺,好像重新審視一樣。您在書中說自己花十二分力氣去寫,我想知道多出來的兩分力氣是什麼?在寫作過程中會不會有非常痛苦的時候?
向迅:我先分享王安憶寫她父親的一篇文章,名字叫《父親從哪裡來》。其中寫到,她說我們最熟悉的人可能被忽略掉,因為我們在生活中面對的是柴米油鹽的事情,我們可能把父親的情緒給忽略掉了。這就產生一個問題,我們對最親近的人,我們自以為對他了如指掌,無所不知;但我們在寫作的時候發現對他真的是一無所知。我們真正瞭解他嗎?真正瞭解父親母親嗎?寫特別真實的事情,的確需要勇氣,因為需要打破傳統散文中對父親的歌頌式的寫作。我覺得那種寫作是虛偽的寫作,我想呈現一個人的多面性,把一個複雜的父親呈現出來,只有這樣的寫作才更具有意義。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