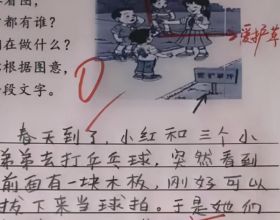街上跑過一群鵝,仰著脖子叫,像是受了什麼驚嚇,又像是很歡快,可以脫離牢籠自由一會兒了。
開啟百度APP看高畫質圖片
駱賓王寫的《詠鵝》,通篇都在用形容詞,毛是白毛,水是綠水,掌是紅掌,波是清波。而開篇的“鵝,鵝,鵝。”既是模擬鵝的叫聲,又寫出描寫的物件。雖然淺顯易懂,但還是有些作詩技巧的。
第一次見到鵝的人恐怕要驚豔於鵝的脖子了,那麼長的脖子高高豎起,仰頭叫喚,頗有一種睥睨眾生的感覺。白色羽毛更顯高貴,只不過肥胖臃腫的身體成了累贅,不然早就振翅高飛了。
或許家養的鵝是天鵝被圈養之後的東西,就好像家雞是野雞的後裔一樣,失去了更多自然屬性,尤其是不能飛翔,成了任人擺佈的家禽。
曾經有鵝跑丟了,家裡人找不到了。那丟了的鵝跑到草叢裡,和麻雀為伴,吃些小蟲子,竟然餓不死,被找到的時候還胖了一圈。
也曾經有人把天鵝當成了家裡的鵝養起來,讓它和家裡的鵝在一塊生活,沒成想,養著養著,天鵝就恢復了體力,展翅飛走了,弄得主人以為自家的鵝得道成仙了,竟然白日飛昇,成了天鵝。
傳說書聖王羲之喜歡鵝,尤其喜歡觀察鵝的脖子,從鵝的脖子優美的形態悟出了書法的訣竅,有武術家從鵝的脖頸悟出舞劍的訣竅,其實都是在模仿一種自然幽美的舞姿,而這種舞姿是鵝本身具備的自然屬性,它們本身並不知道。
人不是鵝,當然不知道鵝是怎麼想的。
鵝不是人,看人似乎只能看到一群渾身沒毛的碩大東西在圍觀自己。
《禽經》中寫道:“鵝鳴則蜮沉,養之圍林,則蛇遠去。”傳說蜮是一種躲在水裡含沙射人的動物,就是射中人的影子,人也會得病的。而鵝卻能降服這種東西,只要一叫,蜮就沉到水底不敢出來了。要是把鵝放在樹林裡,蛇就會避開,逃得遠遠的,不然只會成為鵝嘴裡的美食。
看來,鵝這個東西還很厲害,能把一些對人類有危害的東西趕走。
不僅鵝的脖頸具備審美特徵,而且鵝的白色羽毛也同樣具備審美特徵。鵝毛大雪是說那大雪片就像鵝的羽毛一樣,紛紛揚揚落下來。而千里送鵝毛,就算是禮輕情意重了。
鵝蛋也具備審美特徵,個頭大,有的能達到半斤左右,讓人吃一個就飽了。人們看到沙灘上被水沖刷的小石頭;就說是鵝卵石,看到橢圓臉就說是鵝蛋臉,都要拿鵝蛋來做比喻,算是喜歡鵝蛋的形狀和線條了。
鵝黃也同樣具備審美特徵,原指鵝嘴的顏色,又指小鵝絨毛的顏色,唐代李涉的《黃葵花》詩寫道:“此花莫遣俗人看,新染鵝黃色未乾。”陳毅的《春興》詩寫道:“沿河柳鵝黃,大地春已歸。”鵝黃也指淡黃色的東西,宋代林逋的《初夏》詩寫道:“秧田百畝鵝黃大,橫策溪村屬老農。”王安石的《半山即事》詩之三寫道:“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嫋嫋垂。”還有一種酒稱為鵝黃酒,酒體呈鵝黃色,甘爽醇香,回味悠長。白居易寫道 :“爐煙凝麝氣,酒色注鵝黃”, 陸游的《遊漢州西湖》詩寫道:“嘆息風流今未泯,兩川名醞避鵝黃。”鵝黃還指小鵝,並不只是指顏色和酒。雞黃、鵝黃同用,就是指小雞和小鴨子。
鵝被煮熟了就成了熟鵝,成了一道美食。《水滸傳》中的武松被髮配的時候,施恩送來兩隻熟鵝,武松沒有解除枷鎖,戴著枷就把兩隻熟鵝吃完了。而兩名公人要想在飛雲浦聯合蔣門神的徒弟解決武松的性命,已經不太可能了。畢竟,武松吃了兩隻熟鵝,迅速恢復了體力,當然也就能使出景陽岡打虎的本事,大鬧飛雲浦了。
鵝具備觀賞性,又具備實用性,全身都是寶,肉可以吃,鵝蛋可以吃,羽毛可以做衣服,簡直算是為人類的幸福做出了犧牲。當然,鵝也不是好惹的,還追著小孩兒跑,追著貓和狗跑,還會執勤,夜裡聽到動靜就叫喚,可以當做看門狗——————不,是看門鵝了。
一群鵝在路上跑,嘎嘎地叫,讓人對它們刮目相看,畢竟家養的鵝已經不太多了,都變成養殖戶養殖了,那就沒什麼意思了。以前,家養的鵝要經常出來遛彎。小孩放學後可以去放鵝,算是一種家務勞動吧。
現在的鵝已經沒人放了,自己跑,還不怕跑丟,或許是經濟發達了,人們已經看不上這些長脖子的傢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