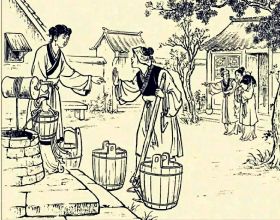一年多的顛沛流離,張訥四處打聽弟弟的訊息,輾轉到了金陵,宛如乞丐般衣衫襤褸、彎腰駝背的在路上慢慢挪動。
這時有十餘人騎馬經過,他便站在路邊躲避,其中有一個看著像官長的,四十來歲,騎著健馬,奴僕簇擁,很快就過去了。
其後一少年騎著小馬,多次打量張訥。張訥見其一副貴公子打扮,不敢抬頭細看。
忽然那少年停馬跳了下來,喊道:"可是我哥哥?”張訥抬頭一看,竟是弟弟張誠,兄弟倆生死別離終聚首,不禁相擁痛哭。
張誠問:“哥哥怎麼流落到這裡了?”張訥便說了自己千里尋弟的經過,張誠更是感傷。
那個官長也下了馬詢問情況,聞言後深受震動,忙令人給張訥騰出一匹馬來,帶著他回家。
張誠歷經生死後他鄉遇親喜不自勝,一邊拉著哥哥洗漱更衣,一邊令人準備宴席為其接風洗塵,一邊又挑空子訴說自己的經歷。
原來,張誠被老虎銜走後,也不知道跑了多遠,後來便把他扔在了路邊,在那裡躺了整整一夜。
恰逢張別駕從京城回來,看見路邊重傷的張誠,便令人給他醫治。
張誠甦醒過來,說起自己的家鄉,才知道距離已經很遠了,因為身體還很虛弱,便一起到張別駕家中調養,過了一段時間才好。
經過張誠敘述,張訥得知原委,對張別駕更是感激不已,連連拜謝。
張別駕言道自己膝下無子,張誠知書達理,友愛孝順,他早已將張誠視為己出,不必如此云云。
席間觥籌交錯,眾人聊起各自狀況,張別駕問起張訥家中情形,張訥言道:“我父親本是山東人,後來才搬到河南的。”
張別駕說:“我原本也是山東人,你們老家在山東哪裡?”
張訥答:“記得聽父親說過,屬於東昌府。”
張別駕一聽很是驚訝:“原來我們是同鄉!你們為什麼搬到河南?”
張訥說:“明朝末年,清兵入關,掠去了先母,家產被毀,由於父親以前在河南做過生意,十分熟悉,所以就搬到了那裡。”
張別駕聞言神色一變,急切追問:“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張訥說了,張別駕驚得目瞪口呆,低頭略一思量,驀然起身進了內室。
一會老夫人也出來了,張訥、張誠連忙施禮拜見。
老夫人不顧其他緊盯著張訥問:“你是張炳之的兒子?”張訥答:“是。”
老夫人一聽頓時熱淚盈眶,對張別駕說:"這是你弟弟呀!”
張訥兄弟倆一臉懵逼,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老夫人說:“我嫁給你們父親三年,被掠到了北方,跟著黑固山過了半年,生下了你們哥哥。”
“半年後,黑固山死了,你們哥哥繼承了他的位置,升到這個官職。”
“現在他已經辭官了,時時刻刻都想回老家,因此脫離了旗籍,恢復了本姓。”
“我們曾多次派人到山東打聽,卻一直沒有音信,原來你們已經搬走了!”
兄弟倆聞言頓時一臉驚愕。
轉頭又對張別駕說:“你把弟弟當兒子,會折福的!”
張別駕汗顏道:“我曾問過張誠,可是他沒有說自己祖先是山東人。想來是那時年紀尚小,還不記事吧。”
三兄弟相認後,按年紀排了大小:張別駕四十一歲,為長兄;張誠十六歲,是老么;張訥二十二歲,是老二。
又各自詳細訴說了離散後的情形,三人感慨之餘都開懷不已,每天形影不離,計劃著和老父親團聚。
老夫人卻有些擔心牛氏容不下自己,張別駕勸道:“能相處得來大家就住在一起,不能的話我們就分開住。總不能因為這樣我就不去認老父親吧?”
牛氏聽後憂慮頓消,於是張別駕便賣了房屋田產,收拾好行裝,一家人踏上了歸途。
一番跋涉到了村裡,張訥和張誠先跑回去告訴父親。
自從張訥走後不久,牛氏無法承受喪子之痛憂病交加也去世了,只剩老父親一個人,形單影隻地過活著。
這天忽然看見張訥回來,又驚又喜,又看到張誠,激動得直哆嗦話都說不出來,只拉著兩個兒子一個勁流淚。
待父親稍微平息張訥又告知張別駕母子的事情,老父親又瞬間就愣在了原地,繼而又顫巍著老淚縱橫,不知所云。
不久,老夫人與張別駕攜帶奴僕進來拜見,老父親和老夫人相扶著聲淚俱下,好不容易止住洶湧的心潮,看著滿屋的奴僕婢女,又不知所措。
張誠半天不見母親,一問之下才知道她已經離世,一聲悲呼摔倒在地,很久才緩過勁來。
後來張別駕領著倆兄弟蓋起了寬敞明亮的新房子,還專門請了西席教授兩個弟弟。、
經過三人不斷地辛勤努力,成了十里八鄉的大戶人家,一家人的歡聲笑語不時迴盪在依山傍水炊煙裊裊的莊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