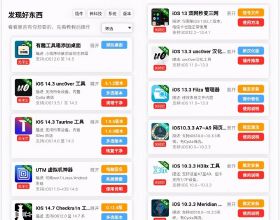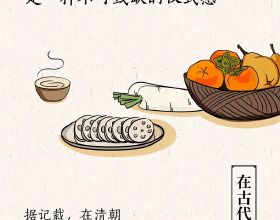這幾天在公司曲仙茗似乎變了一個人,不但沒有跟我鬧彆扭,還時不常地還給我幫點小忙,端個茶倒個水什麼的的,查個資料找個檔案什麼的,而且穿著一天比一天性感,打扮一天比一天妖嬈,臉上時常蒙著一層曖昧不清的迷人微笑,尋找各種藉口在我面前扭阿晃阿的,變著法用各種部位的雪白肌膚給我保養視力。
我知道這小妞什麼意思,就是想看我“下面”出醜嘛,嘿嘿(冷笑)老子有的是病,壓根就不會搭帳篷,你扒光了衣服跳豔舞老子一點反應都沒有!(當我寫到這一段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前幾天在宿舍樓下的櫥窗裡看到的一張海報:2008世界帳篷大會,自然的盛典,戶外的狂歡,期待您的參加……我突然很想笑……
儘管識破了她的險惡用心,但是時間長了,在下還是被她搞得有點浮想聯翩了,難道是那天晚上我王八之氣大盛,把她給鎮住了?這個念頭在我的腦海裡也僅僅存在了0.01秒,然後馬上就被我丟到爪哇島去了,MD,這個想法太羞人了,“王”跟“八”這兩個字組合在一起讓我有一種天然的羞愧感,主要是這個詞太猥瑣了,集天下猥瑣之大成,天下猥瑣三千種,三千猥瑣在一身……平時看到老鱉我寧可故意很正經地叫人家甲魚,也不肯直呼其名為王八,就像古代的草民對帝王的名諱一樣不敢呼諸口端。
我知道曲仙茗的詭計不會僅僅是色誘而已,這是在迷惑我的視線呢,等我什麼時候不注意了,嘿嘿……(替曲仙茗冷笑一聲)既然不能往好的方面想,那麼我就開始朝壞的方面想,人之常情嘛。
敵人是狡猾滴,手段是陰險滴,總之我就是不知道滴,我可不認為這個女人會寬宏大量任由我大吃冰淇淋,可是我還真想不出曲仙茗的陰謀在哪裡等著伏擊我呢。
在下心裡那個彆扭啊,明明知道人家要伏擊,可是死活不見動靜,這種等著挨死的滋味比直接湊我一頓殘酷多了,同志們(一個高尚而純粹的稱呼,勿作他想)考驗我們(主要是我)的時候到來了!
幸虧王欣怡那個傳說中的建寧公主暫時還沒有搬過來,要不然一天到晚淨要提防人了,白天在公司提防曲美女,抵禦制服誘惑;晚上在家裡提防王丫頭,小心蠻女發飈。這心理壓力大了去了,指不定什麼時候抗不住就要玩一回精神崩潰。
不過,估計好日子也沒有幾天了,聽趙馨說,王欣怡跟她老爸的談判已經差不多了,隨時都可能搬過來,媽呀,頭疼!
可是眼前最恐怖還是星期六要到來了,火燒眉毛啊。
問我為什麼?太陽啊,你對不起我辛辛苦苦碼的字,都沒有仔細看,前面不是說了麼,趙師妹要拉我去醫院檢查!
檢查本身沒有太大關係,可偏偏要檢查的是那個地方!
檢查那個地方沒有多大關係,可偏偏那醫生還是個女的!
醫生是個女的還沒有太大關係,可偏偏她還是個妙齡女郎!
是個妙齡女郎仍然沒有太大關係,可她偏偏還是個婦科醫生!
這麼多偏偏羅列出來,你總該知道我為什麼害怕了吧?要你去你去嗎?說害怕那都是比較委婉的說法,其實是害羞,男人看婦科醫生,說出去我就沒臉見人了我!
星期六的早晨並沒有因為我的恐懼而遲些到來,這天早上趙師妹沒有做我的那份師妹牌早餐,我洗漱完畢下了樓,卻看見趙師妹一個人吃得津津有味,不像往常等我一起吃。
我道:“今天怎麼一個人先吃上了?”
師妹道:“等我吃完我們就要出發了,所以我要提前吃。”
我道:“我的呢?”
師妹理所當然地道:“你的?沒做啊。”
我心裡覺得很委屈,肚子覺得更加委屈,不甘地發出“咕嚕嚕”的抗議聲。
“為什麼啊?”
“今天要檢查,不能吃東西。”
我不屈不撓地道:“沒聽說過這種檢查也需要空腹。”
師妹據理力爭道:“也沒有聽說過這種檢查不需要空腹。”
我沒聲了,堅持下去,不過堅持多久,最後結果都是一樣,這是我這麼多天來總結出來的規律性的經驗,師妹的脾氣很倔,認定的事情還從來沒有改變過,我知道,這次,她不改態度的紀錄要繼續延續了。
我陪師妹“一個人”吃完早餐,該丫頭很瀟灑地把盤碟往水池裡一泡,道:“今天趕場子,回來再洗!師兄,LET’S GO!”
“我討厭中國人說英語,特別是中國美女說英語,那感覺好像從思想到嘴巴都被西方帝國主義強姦了!”
我憤恨地想著,什麼趕場子嘛,是趕鴨子上架才對,我就是那鴨子,還帶病的!
我想完,忽然覺得這麼咒自己有點殘忍,那鴨子的名聲和雞有得一拼,反正都不是怎麼好,所以有必要把這個俗語改一下,就改成是趕鵝上架,反正都是家禽,還都是喜歡水的種類,雞就不行,見水就死……呃,純粹的水,可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啊,差不多得了,鵝的名聲比鴨子和雞都好多了,不管是孤陋寡聞還是什麼,反正俺至今沒有見誰拿鵝來做不良比喻的,相反,還有人拿鵝來作詩: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好詩阿,就趕鵝上架了……(我要是山西人就好了,人家嘴裡的“鵝”就是“我”的意思,那就是趕我上架了,我多麼希望有書友趕我上架阿,不過呢,我不敢妄想當最火熱的作者,那就當最厚道的作者吧,一定晚點上架,晚點!
剛走出家門,趙師妹扭過頭來道:“師兄,你的臉色可不太好啊,是不是病了?”
我聽了師妹的話,心裡一陣驚喜,就像寂寞的暗夜行者忽然看見光明裡的按摩店一樣,就像乾渴的沙漠旅人突然撿到一瓶礦泉水一樣,就好像在物資貧乏的非洲轉遍方圓120公里內的超市終於買到避孕套一樣,太興奮了,趁機道:“是啊,是啊,我病了,都有點發燒了,要不咱改天再去?”
拖一拖緩一緩,能拖一時是一時啊。
趙師妹一點機會都不給我:“呵呵,沒關係,頭疼腦熱的,所有醫生都會看,等下讓我那同學給你開點藥就好了。”
我無語,既然都這樣了,那你還提這茬幹什麼?簡直是欲擒故縱阿,我又不是那孟獲,你要是想當諸葛亮你換個人好不?太殘忍了,我最後一點掙扎的念頭湮死泯滅了!師妹,真有你的,能把一世英名斷送在你的手裡,我一點都不覺得冤,我瞑目了!
“師妹,咱是擠公交還是打個的?”
“師兄,你說呢?”
“我覺得吧,擠公交有擠公交的優勢,打個的有打個的的好處。”
“廢話!”
“師妹莫要動怒,開個玩笑,開個玩笑,我這就攔車,師妹你就先原地休息下!”
現在,我覺得我就很入戲,不知不覺地,我已經對師妹太好了,簡直是卑躬屈膝、唯命是從了,雖然還沒有正式成為我的女皇陛下,但是我已經照著這個標準給她相應的待遇了,本段上面的那句話為證!
師妹啊,什麼時候你才能真的成為我的女人呢?是啊,是女人,不是女孩,是有點區別的,嘿嘿……
我忽然想給師妹作首詩了,只是不知道怎麼來形容一下。人家都形容女孩是掌上明珠,可是師妹是要做我的女人的,我說過了啊,女孩跟女人的內涵是不一樣的,要形容女人這個明珠的比喻就很吃力了,怎麼也要升升級吧?叫什麼掌上鑽石?還是掌上白金?總之就是什麼貴用什麼形容,我這人俗,也很粗鄙,就知道鑽石和白金比較值錢了,要不然人們總說什麼鑽石王老五、白金級作家(或者客戶)什麼的,貴阿,值錢阿,我就YY著自己就是一白金作家,等揭不開鍋了,把自己一賣,白金的價阿,那可是好多錢,我估計吃三頓北京烤鴨還有富裕的,餘下的還可以買包面巾紙,帶茉莉花香的那種高階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