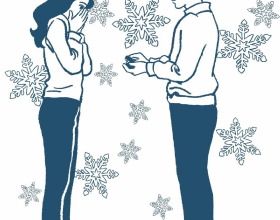龍肉先生,你有過三次生命危險。你將這三次經歷視為命運上的轉折。你用刻刀和顏料畫了三幅壁畫,就在你的牧場中那片懸崖之下。有心人可以專門去看,因為你畫畫的水平絕對不差。你畢業於河北藝術學院,並且在另外一個大學進修了一年。然後你出於尊重自由,選擇回到牧場,舒舒服服當起了牧場主。你母親一氣之下病倒了,再沒站起來。回想那些“氣死母親”“殺母兇手”之類的流言蜚語,你,龍肉先生,不置可否,淡然一笑而過之。你僅有一次吐露心聲:“欠母親的命,我會還給她的。”
如同應驗一般,你很快遇到了第一次生命危險。
這個危險來得很緩慢,慢到你事先就已知曉。那天你走在一條常年踩踏的路上,可是某一段地方突兀地出現了一塊石頭。你想,我怕是繞不過這塊石頭了。於是你去繞石頭,陰面的那部分在並不很傾斜的光線下特別黑暗。這是一塊有汽車引擎那麼大的石頭,但背陰的部分更大,你在此遭受了一條什麼蛇的攻擊。你看見從黑暗中飛上來一個東西,迎面而來,飛到你的腰的高度時碰到你的手。這時候你看清楚了。這條蛇咬了你的手背,你陷入了一種持續的恐懼之中,並因此產生了不好的反應。首先你開始覺得暈眩。這時那條蛇已經完成攻擊而逃走,你眼前的東西並不是路面,你想這不正常,所以需要坐下來休息,看看傷口有沒有中毒,毒性是否蔓延。你聽說過一句話:青海沒有無毒蛇。你覺得自己要死了。你想說點兒什麼,或者笑出聲音來,但你開不了口,是中毒的徵兆嗎?接著你很清楚地感受到一種痛苦。這痛使你喊叫了出來,但你不知道哪裡痛,就好像有時候你感覺很癢,但不知道是哪裡癢,那滋味真難受。你覺得自己流了一攤口水,但低下頭,卻找不到。西北大地的土地太渴了,任何一滴液體也不放過。你當然沒有死,你被一輛車送到了醫院,但你一點兒也記不起來這中間發生了什麼。
然後是第二次危險。這次你沒有任何察覺。當時,你正從醫院出來。你住了三天院,但覺得已經夠了,因為你之前從未住過院。住院是另一種折磨,因為你活生生地看到一個人在你旁邊的床上死去,看到那些醫生和護士冰冷的反應和態度。你知道那是對的,但你接受不了。你過馬路時腦袋突然震盪了一下,你感受到危險了,但已經晚了。你很敏銳地發現自己正往高空中飛去,然後你在轉動,這時候你什麼也聽不見。世界安靜的時候真好啊!你感慨得太早了,你沒有感到疼痛,但這會兒你以為自己真的要死了。是啊,被汽車撞飛那麼高,能不死嗎?可是老天就真的好像在跟你開玩笑,你高高地飛上去,卻遲遲沒有落下來。這時候你頭朝著地面,可以看見一些人在看著你。你想起一句詩:“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看你的人發出一陣驚呼。你很費力地往空中抬頭,發現自己被掛在電線上,你的腿和那些密密麻麻的電線纏在一起。有粗有細、已經很陳舊了的電線救了你。你又逃過一劫。兩次劫難緊密連線,你都沒有好好消化第一次面臨死亡的感受。所以你是把這兩次劫難放在一起研究的。你一遍遍地回憶,想起來很多被忽略的細節。你能慢慢地回憶,因為你有時間——這次你的腿斷了。你真幸運,只是斷了一條,而且還很有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你可能不會成為一個瘸子。所以,現在,你已經回到家,你還要躺在床上半年時間。你將思考死亡。你回憶,還原當時的場景,你知道記憶一定在某些地方欺騙了你,或許就在最關鍵的地方。這你沒有辦法。你對記憶有了強烈的興趣。但是更多的時候,你開始預測未來。你開始預測,下一次生命危險,會在什麼時候到來。這種預測就如同遊戲,又彷彿在做試驗。於是你覺得死亡就在身邊,到處都是。起先你有些不敢接受這樣的觀念,你試圖重新構建健康的觀念,可你很快發現,這就是最健康的——能夠直視死亡,不被其嚇住,就是最好的。於是你認為第三次生命危險,第三次劫難,雖然還沒有發生——或者已經在發生——卻已經在改變你。於是你不得不感到驚奇。你又想起一句哲語:人思考得越多,就越顯得愚蠢。(作者 索南才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