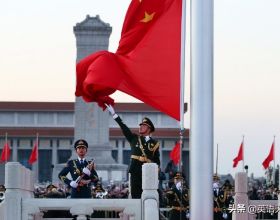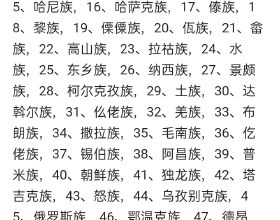“趙老四,我操你祖宗。”
文化人陳宏生終於忍受不住了,多年來的忍辱和委屈終於在此刻爆發。他揮舞著年前還給趙老四家寫過對聯的拳頭撲向滿口唾沫橫飛的敵人。
“媽的,還反了你了,連吉連祥快過來,給我打死這個老雜種!”
不遠處正在鋤地的趙家老大老二扔掉鋤頭跑過來,這一頓打啊,讓土秀才陳宏生刻骨銘心。
“爹……”
陳繼元扛著鋤頭飛奔而來。
一場實力懸殊的戰鬥由於手持“長兵器”繼元的加入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繼元發瘋似地把一把鋤頭舞得虎虎生風。站在一旁有些發抖的陳德來被差點驚掉了下巴,平時連只雞都不敢殺的小秀才竟然這麼男人。
平生頭一次和人打架的陳繼元此時有如神助,開天闢地、黑虎掏心、神龍擺尾、大海撈針……
可憐趙家兩兄弟除了閃展騰挪和抱頭鼠竄只有跪地求饒。
殺紅了眼的陳繼元一招泰山壓頂剛使了一半就被陳德來死死地抱住了鋤把。
“繼元,快放手,要出人命的。”
滿身是土的陳宏生趴在地上拼命抱住了兒子的大腿哀嚎道。
旁邊的趙老四被眼前的一幕驚得目瞪口呆,俗話說狗急了跳牆,兔子急了咬人。誰能想到陳家平時連鋤頭都不會拿的小兔崽子竟是這等身手。
眼前的戰鬥本來就是實力懸殊尤其是自己家佔理,因為是陳家老東西先動的手。明明是自家穩操勝券,誰知戰場瞬息萬變,由於陳家秀才的加入使戰鬥發生了質變。
老大趙連吉已經腳底抹油開溜了,右手捂著頭頂的老二趙連祥此時正被陳繼元踏在腳下。跪在一旁的趙老四慌張地拿出記載著中國五千年曆史和文化的破毛巾捂著趙連祥的頭。鮮血漫過破毛巾汩汩地往外流,把散發著汗臭味的發黃的白毛巾染的鮮紅。
“在那在那,快快,別讓那小子跑了。”
趙連吉跑在前頭,後面跟著扛著鐵鍬的趙連如和二狗。
“繼元,快跑!”
陳德來拉著陳繼元就跑。
“我爹……”
“快跑吧,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們的目標是你,不敢把大爺怎麼著。”
陳德來奪過繼元手中的鋤頭扔到一旁,拉著還在猶豫的繼元撒腿就跑。
趙家哥仨沒攆上陳德來和繼元,回來把氣全撒在陳宏生身上。可憐的土秀才陳宏生剛吃了一頓拳腳,又加了一頓鐵鍬小灶。
一聲春雷在天空炸響,不知何時天空中陰雲密佈,霎時淅瀝的小雨下了起來。
招娣弓著腰抱著籃子快步走在去縣裡監獄的路上,用炮捻子撐起來的紅頭巾已經被雨水淋透了。雨滴正順著頭巾的下角流進招娣的後背,真涼啊,懷裡的籃子確是滴水未沾。
這條路三年來自己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今天是最後一趟了。三年前的那場鄰里糾紛被趙老二授意定性為持器械故意殺人未遂,並被判蹲了三年監獄。
監獄在縣城西北角,離趙家老莊足足五十里。可憐招娣一邊當男人下地幹活一邊還要照顧年邁的公婆,還要抽空去探視監獄裡的丈夫。
幸虧小時候家裡窮又缺人手幹活,所以大人沒給招娣裹腳。為這事招娣沒少被人笑話,都說長大了找不到婆家。
沒想到千里姻緣一線牽,招娣在17歲那年被本家姑媽做媒說給了老實人家的陳繼元。
婚後小兩口倒是相敬如賓,招娣沒念過書,人勤快能幹,一雙大腳走起路來虎虎生風。過門沒多少日子就把家裡裡裡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條。
婆婆陳氏看在眼裡喜在心上,自己沒有閨女,心裡其實早已把招娣當閨女看待了。
最近地裡活忙,婆婆又病了需要天天煎藥,所以快三個月沒來看望繼元了。
監獄大鐵門上的一扇小門在一陣嘩啦啦的開鎖聲中打開了,衣衫襤褸的陳繼元蹣跚著走了出來。雨後的陽光不是太強烈,一道罕見的彩虹掛在遠處的苞米地上方。
陳繼元揉了揉被陽光刺得生疼的眼睛,這才注意到身前被雨水淋成落湯雞的招娣。
“當家的,你手咋了?”
招娣扔掉籃子幾乎是撲到陳繼元身上,抓起陳繼元的左手,望著剛剛結痂的光禿禿的無名指和小拇指急得哭出聲來。
“你快說啊,手咋的了?”
“走,回家說。”
陳繼元抬手擦了擦招娣眼角的淚水,彎腰拾起地上的籃子,翻出一件灰色的長衫套在身上。甩掉了腳上爛得不成樣的布鞋,又從地上撿起沾了泥水的新布鞋蹬在腳上。
“嘿,正好,媳婦做的鞋穿著就是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