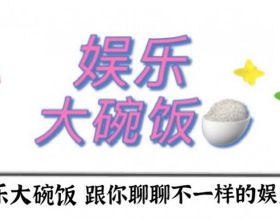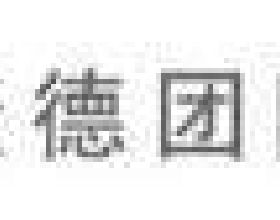我常想,若牧晚還在,這許多年過去了,他是不是也已經娶妻生子了?不,不會的,即便他還活著,也永遠不可能過上平常人的日子。
牧晚與我是同鄉人,比我大三歲。從小和奶奶住在最靠近山邊的那一棟破舊的平房裡。據說他的爺爺就吊死在那個房子,家人認為房子不吉利,早已遷往別處另起新居,那個房子就一直空著。
聽長輩們講牧晚一出生就是個不招人待見的孩子,尚在腹中,母親勞作晚歸,牛突然發狂將她撞倒踩其背而過,被人發現時,已經倒在一片血泊中。
尚不足月的牧晚就是在這種境遇下來到人間的,雖然左腿殘疾,但好歹是活下來了。他的母親沒那麼幸運,失血過多,當晚就死了。
愚昧專橫的大伯作為家中最權威的長者,他極不歡迎這個孩子的到來,認為這個孩子是惡鬼投胎轉世,一身的戾氣。對他那膽小懦弱的弟弟說:“就把你家這半個殘廢叫做牧晚吧,養得活就去放牛懺悔自己的過錯,天沒黑盡都不允許回來。養不活,就拿去山裡丟了!”
不幸接踵而至,牧晚尚還沒滿週歲,他的父親在煤礦挑煤,窯塌了,就唯獨他沒逃出來。
至此以後,牧晚的境遇更加淒涼,大伯對他的怨恨也更深了。只要是家裡出點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怪罪到他的頭上,養的雞死了,鴨子丟了,牛幹活不利索了,家裡人生病次數多了統統都是牧晚的錯,他給這個家庭帶來的黴運。
牧晚三歲那年,尖酸刻薄的大伯母田間勞作不小心崴傷了腳下不了地,從此再也容不下他,連夜就要把牧晚丟到山裡去。
牧晚的奶奶哭著求了許久都無濟於事,最後不得不帶著牧晚去山邊那所舊居。童年的牧晚能活下來,全靠他的奶奶東討西求地要來殘羹剩飯喂他,哪家孩子不要的舊衣丟出來了,也撿起來縫縫補補給牧晚穿。
從我懂事起,我記憶中的牧晚從來就沒有乾淨過。拖著一條跛腿吃力地走路,小小的身子一高一低地搖動著。破破爛爛的衣服,露著腳趾頭的鞋子,冬天,滿臉都是北風吹裂的一道道小小的黑口子,烏黑的嘴唇滲著血絲,即使是大熱的天,也流著鼻涕。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會有一群的大孩子對著他拍手唱:“牧晚郎,牧牛羊,剋死爺子剋死娘”,爺子是我們客家話方言,父親的意思。
牧晚也不惱,對著嘲笑他的人憨厚地咧著嘴笑,即便是嘲笑完連帶著扯他頭髮,他也不會哭,就任由人家欺負。哪家的大人看見了,頂多也是喚自己的孩子回來,卻鮮少責罰。刻薄一點的婦人還會教自家的孩子不要靠近牧晚,否則家裡就會倒黴。
我第一次偷偷靠近牧晚,他一個人在田埂上的大樹下寫數字,雖然歪歪扭扭的,但是非常認真,邊寫邊用衣服的袖口抹鼻涕,抹完又再接著寫。那時我已經上一年級了,放學路過,虛榮心作祟,一時想顯擺一下自己的學問。便走到他跟前將他寫得歪歪扭扭且順序錯亂的數字全部抹去,又寫了一遍正確的給他,我抬起頭,得意地看著他,他有高高的鼻樑,眼睛像一汪清澈的湖水。
牧晚看著我笑了笑,連一個謝字都沒有。只是拿了一把稻草將字蓋起來,然後拉我起身,細心地將我衣裙上的草屑拍乾淨,末了,指手劃腳地指著我家的方向。
我這才反應過來,同時也為自己這種魯莽的行為懊悔不已。雖然我的母親沒有教過我不許跟牧晚玩,我家也沒有那麼迷信。但是我卻害怕極了,生怕真的就會像別人說的一樣,只要接近過牧晚,家裡就會倒黴。
我至今還記得那天晚上我是怎麼躡手躡腳地趁父母不注意偷偷溜進自己的房間換下衣裙。晚飯的時候,母親往我碗裡夾菜,我心不在焉地吃著,頭也不敢抬,快吃完了我問,我們家有幾隻雞?
母親摸了摸我的額頭問我有哪裡不舒服嗎?我搖搖頭,然後她和父親說:“怎麼覺得這孩子今天有點不對勁?”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每天都很積極地餵我們家那七隻雞,三大四小。生怕它們丟了,我在每個雞翅膀上繫上不同顏色的小繩子,傍晚了總要數一數雞是不是全部都回來了。
後來,等小雞們都已經全部長大了。而且我們家也沒有發生什麼不好得事情,我才敢再一次和牧晚玩。
等和牧晚漸漸熟悉起來,他常常跑到田埂上那棵大樹下等我和敏哲放學,這麼遠的路,也不知道他拖著那條跛腿是如何來的。遠遠地看到我們,他就會向我們直招手,滿臉熱切的期盼。偶爾會從口袋裡掏出半截玉米或是紅薯分成兩半遞到我們手上,分之前總是將手往他自己破舊的衣服上反覆擦了又擦,直到他自己認為已經乾淨了。
牧晚很聰明,學東西很快。我們在學校學的漢字,算術題,教他幾遍,他就會了。拿出書本給他讀課文,雖然會有一點小磕巴,但全部都能讀出來。常常會下意識地望著敏哲的紅領巾出神,我們都知道,牧晚該有多想和我們一起去上學啊!
有一年暑假,我去縣城的舅舅家玩了一個月回來。牧晚已經不在了,聽哲哥哥說,牧晚的小堂弟跑到小溪游泳時腿抽筋,腦袋已淹沒在水中,兩手直撲騰,眼看著就要被水沖走了。剛好路過的牧晚毫不猶豫地跳入水中把他堂弟拉了起來緊緊拽著溪邊的水草,自己體力不支順水而下。
牧晚被人救起時尚有微弱的氣息,已經說不了話了,只是流眼淚望著和他相依為命的奶奶,許是良心發現,他的大伯母也嚎嚎大哭。因為牧晚尚未成年,按照客家人的風俗,他被葬在了一小塊荒地上,一小堆土,無墓,無碑。
不知道,如果真有來生,牧晚再世為人,是不是就有吃不完的紅棗糕?而不必我再從家裡偷偷拿出來塞進他手裡;是不是就有一雙健全的腿,有一個健全的家,可以去上學,可以像我和哲哥哥一樣爬到高高的山頂去看星星……
(小溪:不是我們客家話的叫法,我們叫大圳,灌溉莊稼引水用的溝渠,水深時可達一米有餘,溪邊無任何防護,極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