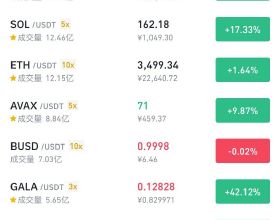來源:經濟日報
在紐約這座慾望都市,百老匯的歌舞昇平只是“面子”,華爾街的驚濤駭浪才是“裡子”。它信仰的,是對利益的極端追求,乃至於向死而生。在一次次創造與毀滅的週期中,華爾街資本一邊高歌勁舞,一邊豎起耳朵甄別樂曲停止的訊號,隨時準備奪路而逃。每家金融機構的掌門人都明白,第一個成功出逃的不是懦夫而是智者,唯有下手快才能活下來,得到參加下一場盛宴的資格。
《MARGIN CALL》是一部反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片。片名本意是追加保證金,但卻很奇怪地被翻譯為《商海通牒》。片中的董事長在公司生死存亡之際,道出了華爾街的真諦,“要麼動作快,要麼人聰明,要麼得會騙”。
這一幕也許會讓不少人感到不舒服,不過對於華爾街來說卻是見怪不怪。華爾街是個沒什麼顧忌的地方。它信仰的,是對利益的極端追求,乃至於向死而生。
在美國,紐約被稱作“city”,華盛頓則被稱為“town”。當一個小鎮青年選擇離開家鄉,首選目標多半就是紐約。而紐約的獨特吸引力很大部分源自於華爾街。
華爾街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下城的狹窄街道,西起三一教堂,向東一路延伸至東河旁的南街,是橫跨紐約曼哈頓的金融中心。儘管多數金融機構已經遷往曼哈頓中城和新澤西州,但這條長度僅1000多米,寬10米的“牆街”(Wall Street)依然是美國金融中心的象徵。
即便到了今天,無論是在歐洲還是亞洲,依然有不少人覺得美國是個“暴發戶”。這其中自然少不了華爾街的“功勞”。更何況,不到250年曆史的國家能有多少文化底蘊呢?
不過,如果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把美國曆史與西方文明歷史割裂開來,多少有些欠妥。一旦將二者視為同一個文明體系,則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千年以來,西方文明的“首都”頻頻遷徙,從羅馬遷到維也納,從巴黎轉向倫敦;直至二戰後又分割為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其中政治中心遷到了華盛頓,金融中心遷到了華爾街。
從金融史的角度來看,華爾街與西方金融體系的發展更是一脈相承。相較於波士頓和費城,紐約更為年輕。它從哈德遜河谷下游地帶興建的一個叫新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成長而來,因此具有明顯的荷蘭風格。在1664年9月8日被英格蘭佔領後,為紀念英國的約克公爵,新阿姆斯特丹更名為紐約(New York,意即新約克城)。由於當時的城市仿照阿姆斯特丹規劃建設,所以直到今天曼哈頓的一些地名仍可看出歷史的痕跡,比如,運河街、水街。華爾街即是新阿姆斯特丹的北城牆所在地。
荷蘭人在本土設立了彼時最先進的金融制度,並把它直接移交給了新阿姆斯特丹。它的商業模式以書面檔案為基礎,比英國更依賴書面合同、公證協議、賬簿和抵押,以及債券等金融工具。來到華爾街的各色人等,要麼在傳奇裡面尋找普通人,要麼在普通人裡尋找傳奇。正是荷蘭人的這一系列制度創新,給了華爾街創造傳奇的機會。
美國的政治體制被稱作“華盛頓—華爾街”軸心體制,華盛頓是政客交易的場所,華爾街則是資本交易的中心。
前者偏好寂靜。四年一次大選、兩年一次中期選舉,整個華盛頓都按照幾近相同的節奏運轉。府會兩黨的政客、希望穿過旋轉門躋身白宮和國會官員行列的學者、想透過資助在政府獲得一官半職的公司高管或顧問,往往因循舊例,在各自劃定的圈子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後者則喜愛喧囂。華爾街也有周期,從創新帶來信貸擴張,吸引資本進入新領域,出現泡沫,到最終破滅,在一片蕭條中震盪調整,然後重新進入輪迴。金融的潮起潮落,在華爾街的歷史上真是再平常不過了。
在紐約這座慾望都市中,百老匯的歌舞昇平只是“面子”,華爾街的驚濤駭浪才是“裡子”。
1929年大蕭條,熊市持續了32個月,股票市場下跌了86%;1937年,由於美聯儲過早緊縮,導致股票市場出現了60%的跌幅,熊市持續了61個月;二戰結束後,美國的戰爭財路斷了,信心崩盤,進入歷史上第三次熊市,並持續了36個月;古巴導彈危機引發1962年的閃崩;1973年發生了被寫進教科書的滯脹;1980年的沃爾克緊縮,利息升至20%;再後來是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伴隨“9·11”恐怖襲擊,網際網路泡沫破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讓人心有餘悸。
在一次次創造與毀滅的週期中,華爾街資本一邊高歌勁舞,一邊豎起耳朵甄別樂曲停止的訊號,隨時準備奪路而逃。每家金融機構的掌門人都明白,第一個成功出逃的不是懦夫而是智者,唯有下手快才能活下來,得到參加下一場盛宴的資格。
今年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二十週年。當年恐怖襲擊發生後,為提振大家對紐約的信心,好萊塢拍攝了一部以紐約為背景的浪漫電影,名叫《緣分天註定》。儘管在現實中,劇中甜品店的冰淇淋確如女主角一般甜美,但經歷過一次次危機的人都知道,華爾街的“甜美”只是表象,真相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紐約這座華美而悲哀的城市以及華爾街的高樓大廈,既是天堂,又是地獄,若無向死而生的勇氣,還請遠離。(關晉勇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