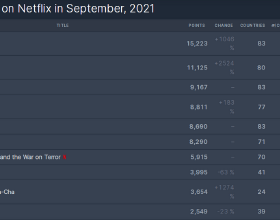戴桃疆
2018年,由百名經濟研究者組成的全球不平等實驗室(World Inequality Lab)出版首份《全球不平等報告》,預言如果繼續忽視財富集中化趨勢,到2050年全球百分之四十的財富將集中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全球貧富差距將倒退到兩個世紀前的狀況。
貧富差距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韓國也不例外。縱然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和次信貸危機的影響,有資料顯示韓國前百分之十的富人收入佔比仍然從八十年代的29%增長到2016年的44%,而這一趨勢近五年來仍未停止。換言之,百分之十的韓國人掌握了國家一半的收入,留下剩餘百分之九十的人為生存爭鬥掙扎。貧富差距是女性主義運動之後又一社會熱點問題,韓國大眾娛樂文化也熱衷於在此處大做文章,2018年韓劇《天空之城》、2020年摘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電影《寄生蟲》和同年開播的電視劇《頂樓》,貧富差距始終是這些創造各種收視紀錄的熱門作品最核心的矛盾。網飛(Netflix)近期推出的韓國原創劇集《魷魚遊戲》亦然。
作為一部影視工業流水線上的標準化產品,《魷魚遊戲》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預告片像日本電影《誠如神之所說》和美國電影《飢餓遊戲》的合體——富人為了娛樂旁觀窮人在兒童遊戲裡彼此廝殺;正片則讓人嗅到一絲《寄生蟲》的味道——不算窮兇極惡的富人和並非盡善盡美的窮人近距離互動,展示一些韓國貧困人口典型形象的同時,用最大的聲量哭訴窮苦的無奈、用最輕柔的聲音控訴富人的罪惡。
頭號玩家
《魷魚遊戲》中編號001的老人是遊戲的參與者也是主辦人,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頭號玩家”。老人在眾人中因年齡顯得格格不入,劇中處處伏筆暗示他身份複雜,不過憑藉殘酷的韓國社會現實做背書,劇中人和觀眾都沒有第一時間對他產生懷疑。參加魷魚遊戲需要兩個條件,一是窮,有足夠的動機,二是不怕死。韓國《每日經濟新聞》援引韓國經濟研究院報道稱,以2018年為基準,韓國65歲以上老年貧困率達43.4%,位居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之首,是組織平均水平的三倍;韓國老年人的自殺率位居全球之首。兩項參賽條件,韓國老人全佔。
韓國老人自殺率高達千分之八,老年人自殺問題也是導致韓國自殺率長期在全球排名中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而導致韓國老人走上絕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貧窮。缺乏有效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缺乏有尊嚴的晚年生活以及不想成為子女負擔的家庭觀念共同作用,將老人逼上絕路。
直到1981年6月韓國國會透過《老年人福利法》,韓國老人福利保障才有法可依。雖然從朴正熙政府時期韓國就提出了建設福利社會的口號,但是歷屆政府一直將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標,社會福利保障並沒有被列入必須考慮到問題,養老在官方語境下延續儒家傳統被視為家庭內部問題而非社會問題。遲來的老年人福利法幾經修訂,福利仍然主要體現在每兩年為6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費體檢以及乘坐公共交通免費等“小恩小惠”上,法律規定的養老年金申領有嚴格的限制,只有在職期間受惠於公共保險或者勞動保險等國民年金的公民才能夠在年老時享受養老年金,而符合條件的韓國公民僅佔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僅有8%的韓國老人符合養老年金領取條件,絕大多數韓國老人缺乏社會系統性保障。
眼下的韓國老人很大一部分是曾為韓國經濟騰飛一天工作十五個小時的“功勳戰士”,這批人中一部分在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遭遇“提前下崗”,55歲領取遣散費開始退休生活。由於缺乏合理的經濟規劃,許多人快速花光遣散費墮入貧困。由於缺乏經濟保障,也缺乏規劃養老生活的能力,許多韓國老人靠再度投入勞動力市場解決經濟問題,韓國65歲老年人就業率為9.4%,位居世界第二(冰島位列第一,但原因與韓國截然不同)。然而高就業率並不意味著高收入,高齡勞力仍難免滑向貧困邊緣。
與此同時,對於韓國老年人而言,家庭養老未必是構成一種選擇。一方面隨著家庭觀念的不斷變化,部分年輕人並不認為贍養老人是一種家庭必須負擔的責任,持有這種觀念的人數比率每年仍在不斷增高。另一方面,在貧富差距過大的大環境下,絕大多數家庭並不富裕,許多貧困老人需要依靠政府提供的低收入戶補助金維持生計,而補助金領取條件之一即為獨居,與子女同住則被視為家庭贍養,政府不再發放補助。韓國老人中53.2%為獨居老人,接近老齡貧困人口比例。
韓國老齡速度是經合組織成員平均水平的1.7倍,每年以29萬人的數量不斷增加,預計在2050年韓國老齡人口將達到37.3%,這意味著韓國將有大量老齡貧困人口。作為韓國對外展示社會現實的一面鏡子,韓劇中獨居老人的形象並不鮮見,他們多半作為溫和睿智的長者形象出現,並常常突發疾病為男女主人公順遂的愛情道路提供一些必要的戲劇衝突。文藝加工的過程中總是有意無意地迴避展示老年人的貧窮,就連做窮人展覽的《魷魚遊戲》裡也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窮困的老年人,當頭號選手揭開面紗露出玩家身份,韓國老年貧困問題再一次從觀眾眼前隱身,人們在回味劇中老奸巨猾身份伏筆之餘遺忘現實中的老無所依。
賭博默示錄
早期在華爾街股市從事投機的瑞士人總結出一套十二條的蘇黎世投機定律,第一條內容是“如果你對自己從事的投機不感到憂慮,那麼你冒的風險一定不夠”,這一定律有一個更直白的說法,“脫離貧困的唯一辦法就是去冒險。”蘇黎世投機定律或許不能完全解釋華爾街資本家的行為,卻能夠從一個側面解釋賭博在貧困人口中更盛行的原因。魷魚遊戲的邏輯顯然也遵循著這一定律,要麼拿走456億要麼死,它是一個巨大的賭局,劇中的主角也被設定成為一個賭徒。
賭博是韓國吸引海外遊客的重要手段之一,韓國全境二十三家賭場盡數面向外國人開放,韓國人僅能出入江原道娛樂場一家賭場。韓國對本國國民賭博管控嚴格,刑法採用屬人主義原則,規定以盈利為目的參加賭博最高可處500萬韓元罰款,習慣性賭博者可處2000萬韓元並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韓國人在海外賭博也可能會受到刑罰制裁。《魷魚遊戲》從整體上與韓國博彩業異曲同工,拿本國同胞的性命開盤以接納外賓收割金錢。因為無法拒絕博彩行業高額利潤,韓國近二十年來向本國成年人開放賽馬、賽車、賽艇等競技專案的線下投注,尤其是賽馬,在2016年中國“限韓令”之後一度被視為韓國影視工業之後下一個吸金專案,這一專案每年給韓國政府帶來了約兩千億韓元的稅收。
賽馬繁榮的背後則是賭馬盛行。一方面是稅收的誘惑,一方面是家長制國家規範國民行為的執政理念,韓國在博彩問題上不允許國民大賭傷身卻縱容小賭怡情,使得賭博行為的社會評價介於對錯之間的灰色地帶,加上社會貧富嚴重失衡的大環境催生的投機心理,導致韓國國民賭博成癮率高出其他國家兩到三倍。疫情期間,韓國線上賭博成癮人數激增兩倍。類似的投機行為還有在年輕人中十分流行的炒虛擬貨幣。然而韓國政府對待上述問題的官方口徑是將問題一律歸咎於網路,對投機背後的社會問題避而不談。《魷魚遊戲》同樣將賭博問題作為主人公缺陷進行展示,併為主人公參加遊戲做了行為邏輯上的鋪墊。一個人以命做注賭上一筆或許是個人問題,456人加入魷魚遊戲必然是社會問題。劇中第一屆魷魚遊戲是1988年舉辦的,三十多年持續不斷,就是沒人管,貧富差距及其衍生的社會問題似乎也是如此。
天空之城
許多觀眾不滿《魷魚遊戲》的一大原因在於男主角人物扁平,自始至終缺乏成長,人物魅力全靠演員強撐,47歲的年齡和他的閱歷與角色的行為邏輯存在偏差,如果是年輕人或許說得通。可如果男主角換成年輕人,那麼他的發小曹尚佑就沒辦法只靠努力學習考進當時還叫“國立漢城大學”的首爾大學,畢竟靠寒窗苦讀金榜題名早已是韓國二十多年前的老故事。
1980年,時任韓國總統的全斗煥開始透過行政手段調整教育結構,禁止所有課外私人教培機構,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使弱勢階層子女獲得更公平教育機會,變相推動韓國生育率提高。這一政策在貧富兩個群體中遭遇冰火兩重天,有能力為子女購買更優質教育資源的富人階層表示不滿,認為政府措施限制自己後代獲得更好發展機會的自由,平民階層則廣泛支援這一政策——值得一提的是,魷魚遊戲中強制統一校服也是政策的一項內容,統一服裝消弭了學生差異化,幫助學生獲得更加平等的體驗。
然而隨著青瓦臺城頭變換大王旗,政策也在九十年代發生鬆動,韓國補習班春風吹又生,升學不再單靠學生一己之力,家庭掌握的財富逐漸成為升學更強有力的保障。進入購買力決定受教育權的時代,教育也不再是實現階級躍層的階梯,透過教育改變人生成為一代人一去不返的夢。韓國一直是一個由血緣、地緣、學緣和師緣“四緣”構成的社會,組成“SKY大學”的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在世界高校排名未必比韓國其他高校靠前,卻一直是韓國精英的聚集地,進入三所高校意味著獲得“學緣”支撐,為未來鋪路。韓國一半的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韓國一半的領導位置則掌握在SKY大學校友手中。當教育不再是階梯時,它就成了鞏固階級壁壘的另一扇門、另一塊磚,資源被牢牢把握在某個特定的群體中並實現流動的閉環。
和血緣、地緣不同,教育,尤其是現代教育中流淌著自由主義思維的血液,這種從人類文明進入近代史起開始主宰全球的思維給人一種“越努力越幸運”的錯覺,從而使在教育中得益並獲得成功的精英群體忽略自身所處的社會優勢資源群體提供的幫助,將個人的成功歸功於自己的努力。當階級流動成為教育的目的,學習成為晉身上流的工具,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自然紮根在一代人的意識中,成為最有效率的思考模式。正如一度進入精英集團又被打回原形的曹尚佑在遊戲過程中表現出的自私自利,當工具理性成為精英普遍意志,精英主導的國家是沒有動力去改變貧富嚴重不均的現狀的。
英國社會流行病學教授理查德·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曾指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導致諸如犯罪率增加、國民之間缺乏信任、心理疾病患病率提高等社會問題,多數負面影響都直接作用於已經陷入貧困的人口,對於從事精英職業的家庭以及富人的影響很小。換言之,如果一個人自信有條件避免陷於貧困,那麼貧富差距問題對他而言或許並不算是問題。多數《魷魚遊戲》的觀眾或許也有類似的想法。作為影視工業流水線上的產品,《魷魚遊戲》將觀眾和操縱遊戲的富人放置在同一視角上旁觀殺戮、獲得娛樂,讓觀眾產生自己不屬於456人之一的錯覺,用缺乏成長的扁平人物、老套陳舊缺乏創意的情節和過度的營銷擾亂觀眾思考,忽略窮人拼命的真正原因。而真正的魷魚遊戲正在現實中發生,富人為富不仁,窮人在富人制定的規則中和同類拼命。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