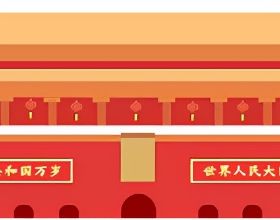我生長在一個具有愛國情結、自愛自立的家庭裡。外祖父仇鰲(亦山)是同盟會元老。他年輕時在日本留學,積極反清救國,是一個為人正直的、反帝愛國者。還記得我七歲左右,一天家裡人都在興奮地議論:明日十九路軍軍長蔣光鼐來訪。這是位抗日英雄,是最受尊敬的人,要隆重接待,再三關照不許打擾,連客廳與餐廳之間的門簾也不能拉開一條縫去張望。我想,平時徐悲鴻、蔣碧薇夫婦常來玩,坐在外公書房,我可以跑來跑去,可以依膝聽他們聊天,雖然我聽不懂。為什麼這次這麼隆重?懷著對“英雄”崇拜的心情,想看一看。
“反對美帝扶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
回想起來,我這個小腦袋還算靈活,就從後面走廊繞到客廳前的小花園玩。外公送蔣軍長出來時,我就跑過去,外公只好慈愛地說,這是我外孫女,蔣軍長摸摸我的頭,我抬頭望去,這是位高大的抗日英雄(年長後才知道他並不是很高)。這就在我幼小的心中埋下了抗日愛國的種子,加深了外祖父言傳身教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反帝愛國的認識。1949年外祖父拒絕去臺灣,與程潛、陳明仁、唐生智等一批愛國人士,在黨的感召下,努力促成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我的母親仇弘之是位賢良、有志氣的女子,她追求婦女解放,自強自立。在生了我弟弟鍾在璞後,毅然把他交給奶媽,將我交給外婆,於1928年考入上海美專。抗戰時,她隨外公參加湖南省賑濟難民難童的工作,設立難民收容所、辦難民醫院、難童教養院,還組織難民生產自救。我在寒暑假回家也去幫忙,親眼看到流離失所的難民的慘狀。特別是那些失去父母、流浪在外的難童,不僅面黃肌瘦,而且滿身蝨子、疥瘡,參加救護的女同胞含著淚為他們清洗。1942年母親不幸因病早逝。她從小教我唱“蘇武牧羊”“滿江紅”“漁光曲”等有正義感、追求民族自強的歌曲,她還有看書看報的好習慣,我也跟著看,不僅看一些古代名著,還看巴金的《家》、鄒韜奮的《萍蹤寄語》等當代的以及世界名著。她也教我們一些古文、詩詞……母親那種追求婦女解放、自強不息的思想深深影響著我,刻在我心中。
1946年我進入復旦大學學習,遇到了同班兩位地下共產黨員金雪南、施宗仁。參加1946年開始的反美暴行運動,1947年“5·20”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1948年5月開始的“反對美帝扶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還參加反迫害,到杭州悼念被國民黨殺害的於子三同學、同濟事件(這次我弟弟鍾在璞被捕)、參加支援港九事件的外灘大遊行……我們還動員同學參加進步的中國農業科學研究社,這種“科學研究”團結了大部分同學。到反美扶日運動時,農學院絕大部分同學都參加了。
透過一系列愛國運動的教育,看了進步的書籍、刊物,到東湖電影院看蘇聯電影,躲在被子裡、打著手電筒看《新民主主義論》等,還參加救濟救寒運動,在募捐和分發寒衣中,深入社會底層,接觸了城鄉勞苦群眾、孩子,受到了社會階級對比教育,看到了飢寒日子的根源。那時施宗仁曾組織少數積極分子小小組學習,他簡單的一句話點醒我,“你追求婦女解放,不推翻三座大山,怎麼能解放?”這一切使我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跟黨走,才能救國救民,才能爭取婦女解放。1948年8月,得知自己上了國民黨特刑庭要逮捕的黑名單,我義無反顧奔赴解放區參加革命。黨組織一直在我身邊,指引我走向正確的人生道路,我永遠將這一切銘記在心,感恩在心。(鍾在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