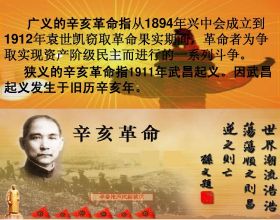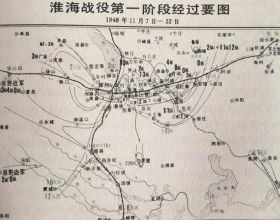辛亥革命是中國由封建專制社會走向民主共和過程中的重大歷史事件。揭開這場鉅變大幕的武昌首義“第一槍”到底由誰打響,一直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也湧現了不少的學術成果。本文擬從狹義和廣義兩個角度對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和點評,並對今後研究提出展望。
一、狹義的“第一槍”
狹義的“第一槍”也就是指時間先後上的第一聲槍響。曹忠生曾對“第一槍”的概念作過說明,即武昌首義“第一槍”特指1911年10月10日晚時間順序上的第一聲實實在在的槍響。他還特別強調,只要這一槍是在約定的起義條件下打響的,且在客觀上取得了眾人響應的效果,那麼無論這一槍打響的主觀目的為何,也“不管是自行走火,還是蓄意放射”,都必須承認其為首義的“第一槍”。那麼到底是誰打響的第一槍呢?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金兆龍打響“第一槍”說
萬耀煌先生在《辛亥首義答客問》一文中提到首先開槍的是金兆龍。黎澍在《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一書中說:“夜晚七點鐘,工程第八營後隊的一個排長巡查營房,與該排士兵程正瀛及該排副目金兆龍發生衝突,排長被猛擊倒地。”一些首義人士的回憶文章也證實了10月10日晚是金兆龍第一個直接與清兵進行生死對壘的,如熊秉坤的《金兆龍事略》對當天起義謀劃經過有較為詳細的說明:“翌日,龍遂與陳振武、程正瀛、鍾士傑三君會議,各給子彈三顆……令鍾士傑刺本隊隊長,程正瀛刺二排排長,陳振武刺三排排長,龍與王忠威在後援助。”胡石庵的《湖北革命實見記》也引用了朱思武對當晚起義情形的具體描述:“陶啟勝巡查各處營房,窺見金兆龍皮盒內有真子彈數排,呵斥其是否準備謀反,金大怒,回答道‘反!反!即反矣!’,即撲向陶啟勝,雙方開始扭打起來。”賀覺非、馮天瑜根據熊秉坤等親歷者早期文獻的具體描述,認為金兆龍應該是10月10日晚第一個和清兵扭打的人,說是“第一打”應該是可以的,但並非是開“第一槍”的人。
(二)程正瀛打響“第一槍”說
馮天瑜在《誰打響“辛亥首義第一槍”》一文中搜集整理了很多首義親歷者的早期文獻,特別是熊秉坤本人的早期文獻,以翔實的材料說明程正瀛打響“第一槍”才是真實的歷史,並對“熊一槍”說流行的緣由提出了自己的解釋。他指出熊秉坤在1912-1913年間曾為當時的湖北革命實錄館撰寫過《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前工兵八營革軍各執事暨各會員事略》等4篇文稿,對起義功勳人物及其事蹟都有較為鮮活的記載,這些文稿無一例外都承認是程正瀛打響的“第一槍”。只是後來因為這批原始文獻長期湮沒,程正瀛因為背叛革命而被人逐漸遺忘,孫中山對“熊一槍”的倡議,熊秉坤本人的記憶變化及其各種名位利益的考慮,“熊一槍”說才逐漸成為主流觀點。白雉山在《到底是誰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一文中特別強調,面對程正瀛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鐵證如山的史實,必須尊重歷史,拂去“歷史的灰塵”,恢復“程一槍”的本來面目。範熒亦認為,武昌首義“第一槍”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不會因人的忠良賢愚而改變,不能因為程正瀛的晚節不保就抹去他打響“第一槍”的歷史功勞。
(三)熊秉坤打響“第一槍”說
目前的教科書和主流媒體都堅持這一觀點。“熊一槍”說得力於幾位重要歷史人物如黎元洪、袁世凱、孫中山、居正等人的堅持。1913年1月,袁世凱政府根據黎元洪的報告授予當時陸軍少將熊秉坤勳五位證書,中有“蓋聞時逢走鹿,難每發於一夫;勢等連雞,功莫先於首”這樣的溢美之詞。孫中山考慮到熊秉坤是革命黨在新軍工程第八營的正式黨代表,為了爭“革命黨人推翻滿清之功”,自然力推“熊一槍”說。1914年,熊秉坤陪孫中山到日本,在一次聚會中,孫中山向在座客人隆重介紹熊秉坤,說:“這就是武昌首義放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雙十節,孫中山又在《晨報》撰文,稱“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槍起義之日乎!”1919年雙十節,孫中山在《八年今日》中再次提及:“今日何日,乃革命黨員熊秉坤開槍發難,清朝協統黎元洪被迫效順而起革命軍於武昌之日也。”同一時期,孫中山在撰寫《建國方略之一》時,在《有志竟成》一章中寫到“為自存計,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對熊秉坤打響“第一槍”可以說是不遺餘力地肯定和宣傳,這自然讓熊秉坤聲名鵲起,再加上革命元勳居正等人也力倡“熊一槍”說,“熊一槍”說便逐漸成為史學界的正統觀點。
(四)羅金玉打響“第一槍”說
竺柏松指出,10月10日晚,城外輜重隊李鵬升燃草引火示警,羅金玉鳴槍示威為號,在時間上首先發難。輜重隊革命代表李鵬升在其回憶文中描述:“萬分緊張之際,羅金玉發一訊號槍,全營同志蜂擁集合。”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也採納了這一說法,“屆時,羅金玉首發一槍,輜重隊的革命者即將馬草房點燃,舉火起義。”首義人士胡祖舜在《武昌開國實錄》中更是大談羅金玉“第一槍”的歷史貢獻,“城外起義總指揮李鴻(鵬)升指揮羅金玉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時間是10月10日晚上6時零5分,‘幸是一槍,而民國從此聲一響而專政倒矣’。”筆者認為,胡祖舜的評價未免有點言過其實,另一位首義人士邵百昌的說法倒是比較符合實際,“七時許,由李鵬升等前往馬廄,燃草引火,同志羅金玉鳴槍示威。此槍實系辛亥武昌首義第一槍。因該營距其他營房過遠,未引起大作用,故各書鮮少提及。”[14]很多史料也證實,羅金玉打響的“第一槍”的確比程正瀛的時間更早,只不過,羅金玉在發槍為號後,僅有該營士兵進入軍裝房搶出子彈一箱,城外駐紮的其他兩隊的人響應不多,最終因其力量薄弱又無後續重大行動,其在武昌起義中所起的實際作用和影響不大,導致此槍既不為外界所知,也少有著作記載。
(五)呂中秋打響“第一槍”說
伍立楊著《中國1911》提及呂中秋曾在1946年的首義同志會上爆粗口罵人,自稱自己打響“第一槍”,但功勞卻被別人領了去。此書出版後,引起了史學界對呂中秋打響“第一槍”的探討與爭論。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呂中秋的確是武昌首義當晚工程營的發難士兵,他也確實開槍打死了黃坤榮、張文濤兩名隊官,只不過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他打響的並非是“第一槍”。《辛亥首義回憶錄》中載有呂中秋口述的《辛亥回憶一則》,他自己說道:“程正瀛、金兆龍槍殺陶啟勝,我亦槍殺黃坤榮、張文濤。”首義人士邵百昌的回憶文中有“右隊隊官黃坤庸(榮)阻止本隊士兵參加,呂中秋擊殺之,彈貫穿黃身而出,該隊司務長(張文濤)立於旁,亦中彈而死。”裴高才詳查史實,認為呂中秋打響的應該是繼羅金玉、程正瀛等人之後的第三槍或者第四槍(如果熊秉坤在他之前放槍的話)。根據現存的史料判斷,第三槍或者第四槍的說法較為可信,比較熊秉坤、周全勝、金兆龍、程正瀛等人的回憶文章以及胡繩武、楊玉如、章開沅等辛亥革命史家的專著,極有可能的情況是,武昌首義當晚程正瀛先以一槍擊傷清兵排長陶啟勝,“熊秉坤聞聲放槍為號,右隊隊官黃坤榮挽本隊兵士暫留房內,呂中秋擊之,坤榮死,彈貫司務長張文濤亦死。”如果是這樣的話,呂中秋應是在熊秉坤訊號槍響之後開的槍,他應該也知道自己打響的不是“第一槍”。因此,呂中秋打響“第一槍”說很難成立。
誰打響的“第一槍”仍是一個歷史之謎。尹呈輔在《參與辛亥武昌首義之回憶》中講道:“武昌首義‘第一槍’到底是誰放的?這可能還是一個歷史之謎”。郭國祥、朱喆對此也持相同看法,他們認為武昌首義是一場倉促之間由恐慌引起的基層士兵發動的兵變,兵變不是一處兩處,又是混亂情形之下,那麼打響“第一槍”的人、準確時間和確切地點實在難以考證。就時間而言,當時只有排長以上的軍官才有懷錶,普通士兵沒有表也就說不清楚具體時間,因此各自放槍的準確時間就不是很確定;就地點而言,有人在工兵營放槍,有人在輜重隊放槍,有人在炮兵營放槍,但到底誰先誰後很難考證。因此,是誰實際打響的武昌首義“第一槍”在今天只能是一個歷史之謎。
二、廣義的“第一槍”
狹義的“第一槍”特指揭開武昌首義序幕的第一聲槍響,但這個“第一槍”具有太多的侷限性。首先,開“第一槍”具有太多的偶然性,一個恐慌引起的兵變,誰開的“第一槍”,當事人恐怕也不太清楚,也沒有那麼重要。我們更應該從發動這次起義的歷史必然性去考慮“第一槍”的問題,如果是發動起義的標誌性的訊號槍就更有意義。其次,既然是恐慌引起的兵變,放槍肯定就不是一處兩處,緣由也就多種多樣,有人在工八營因應對突發檢查向清兵開槍,有人為發動起義鳴槍為號,還有人在沒有放槍之前就打了起來。有人在輜重隊燃草引火示警,有人鳴槍示威為號,有人在炮兵營放炮為號。這些人誰的時間早,誰的功勞大,就很難說清楚。再次,“第一槍”不能拘泥於有形的第一聲槍響,“第一爆”“第一打”“第一把火”“第一炮”等難道就不是揭開起義序幕的重大歷史事件嗎?既然如此,那就應該把“第一槍”這個問題泛化,提出無形的“第一槍”。最後,歷史研究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史實問題,還涉及到後人對歷史事件進行分析的立場、視角、方法和理論問題,如把“第一槍”可以看成是一個群體行為。這樣關於“第一槍”的研究就更加精彩紛呈,觀點多樣。目前,主要的觀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起義訊號的“第一槍”和實際打響的“第一槍”
郭國祥、朱喆認為武昌首義的發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第一槍”既有程正瀛在緊急狀態下戲劇性和偶然性地實際打響的“第一槍”,也有熊秉坤按照預定計劃打響的標誌起義訊號的“第一槍”。兩個“第一槍”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不能輕易抹殺其中的任意一個,但熊秉坤的“第一槍”更符合歷史的必然法則,更有象徵意義和歷史意義。
賀覺非在《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中多次強調了熊秉坤打響標誌起義訊號的三槍,在《熊秉坤》篇中記:“熊走到本隊……聽到樓上有扭打聲,即取槍實彈。方擬上樓,見排長陶啟勝狼狽跑下,即開槍擊中陶小腹,陶捧腹而逃。隨即對空放了三槍,表示已經發難。”在《金兆龍》篇中記:“熊向天鳴槍三聲,才是發難訊號。”吳劍傑在《熊秉坤與辛亥武昌首義》一文中指出,從微觀、狹義上來說,“第一槍”確實不是熊秉坤打響的,但如果沒有工程營黨代表熊秉坤在發難前卓有成效的串聯、策劃、動員和組織,如果沒有他的“鳴槍三聲”和之後的臨機指揮,那麼武昌首義也許就熄火了,也許就不可能出現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重大歷史事件了。因此,從宏觀、廣義上來說,熊秉坤榮膺首難“一槍之功”是當之無愧的。嚴昌洪對此表示贊同,認為如果從發出正式起義號令這個廣義的角度來看“第一槍”,熊秉坤可以說是名副其實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的功臣。
陳家琪認為“熊一槍”更符合革命敘事,更利於革命神話的塑造。他認為孫中山對於“熊一槍”的強調就是一種宏大的革命敘事,是革命者爭“推翻滿清第一功”的自然反應,是渲染革命道統和法統的必然之舉。黃逸梅、鄭一奇、武雲溥等學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黃逸梅認為羅金玉雖然打響了武昌城外的“第一槍”,但是在事後竟人間蒸發,程正瀛雖打響了城內的“第一槍”,但他不知珍惜榮譽,在武昌起義後不久叛變革命,投靠了袁世凱,唯有熊秉坤在武昌起義後再接再厲,因此,承認他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更具正面意義。鄭一奇認為整個發難過程中熊秉坤自始至終都是革命的領導者,他開的三槍具有特別的意義,是工程八營正式起義的訊號,再加上程正瀛後來墮落為軍閥爪牙,承認“熊一槍”的說法更能服眾,也是對首批發難的革命士兵的讚譽。武雲溥亦認為熊秉坤是革命黨人的代表性人物,也是10月10日群龍無首時發難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加上還有孫中山等人對他的褒獎,將他視為廣義的“第一槍”有其合理性。
(二)城內“第一槍”與城外“第一槍”
武昌起義當晚的發難單位,既有城外李鵬升帶領的輜重隊,又有城內熊秉坤帶領的工程八營,兩個發難單位誰是“第一槍”,如何評價他們當晚的行動,這在學術界也是爭論很大的一個問題,代表性觀點如下:
1. 城外輜重隊首義說
張紹春根據塘角黨人、城內黨人、湖南黨人、立憲黨人等四類人的回憶,提出是“輜重十一營放火在先,工八營鳴槍在後”。竺柏松也力主此說,並引當時領導輜重隊發難的李鵬升自述和其他目擊者的記述,證明是“塘角輜重隊比城內早發難一小時左右”。胡祖舜在《中西報》上質疑“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時,公開提出輜重隊發難在10月10日下午6時許,而工程營則在8時左右,且從輜重隊放火,又經武勝門,繞至通湘門,最後從中和門進城到楚望臺會師的路程來看,可以推算出輜重隊發難在先,胡祖舜還曾舉出章炳麟所作黎元洪墓碑初稿作為佐證。
2. 工程八營首先發難說
《辛亥革命史稿》第3卷《1911年的大起義》中詳細列舉了工程八營在10月10日晚擔當率先發難任務的幾個有利條件,其一,楚望臺軍械庫由工程八營負責防守;其二,工程八營駐紮城內,又獨守紫陽橋,行動便利;其三,工程八營組織基礎良好,工程八營內的革命黨人佔該營士兵人數的十分之四。學者黃逸梅認為,人們在談論是誰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時,往往特指武昌城內發難,鮮少提及城外發難,因此,武昌首義“第一槍”就是特指工程八營打響“第一槍”。肖承勇認為,雖然程正瀛的一槍事出偶然,但他這一槍在客觀上取得了眾人響應的效果,城內步兵中幾乎所有革命黨人聞聲起義,繼而奪取了對起義成敗具有關鍵作用的楚望臺軍械庫。因此,城內程正瀛打響的“第一槍”的地位和作用是城外羅金玉所打響的“第一槍”所無法比擬的,武昌首義“第一槍”就是特指城內“程一槍”。
3. 城內城外兩相宜說
張玉田、陳崇橋認為,1911年10月10日晚7時左右,駐武昌城內的工程八營和駐武昌城外的工程、輜重兩隊首先起義,各標營基本上仍按原作戰計劃同時行動,武昌首義的成功是城內、城外兩個發難單位協同作戰的歷史成果。著名史學家章開沅、林增平在《辛亥革命史》中認為:“武勝門外塘角輜重隊,……差不多與工程八營同時舉起了義旗。”賀覺非、馮天瑜合著的《辛亥武昌首義史》也認為:“就發難時間而言,應以城外第二十一協輜重隊為最先,但工八營地處城內,打響第一槍,影響最大,該營又是首先搶佔楚望臺軍械庫的。因此,城外輜重隊和城內工八營均可視為武昌起義的發難單位。”吳劍傑認為拋開武昌首義及其開創的辛亥革命全域性去計較兩個發難單位的輕重之分是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歷史事件之所以被大家銘記,就在於該事件對當時及今後其他事件產生重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將首難之功歸諸工程營,是當之無愧的,承認輜重隊縱火在先,也絲毫不會減少工程營首難的光彩裴高才也持相似觀點,既肯定城外輜重隊先行發難的史實,又認為城內城外兩相宜,兩個發難單位的歷史功績不分上下,各有千秋,應承認兩個“第一槍”的合理存在。
(三)有形的“第一槍”和無形的“第一槍”
有形的“第一槍”就是實體的“第一槍”,就是真正的第一聲槍響,不管它是起義訊號還是偶然之間的擦槍走火。無形的“第一槍”則是廣泛意義上同清軍展開戰鬥的第一個行動。單從10月10日晚的發難來看,金兆龍是和清兵展開生死對壘的第一人,他的“第一打”揭開了當晚革命的風暴,就是“第一槍”。郭國祥、王欣欣在《武昌首義“第一槍”新探》中提出,我們理解“第一槍”不要侷限於實際開的第一聲槍響,而應該從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第一槍”,即無形的“第一槍”,也就是和清兵進行的直接的尖銳對壘的標誌性事件,如“第一把火”“第一聲炮”也是“第一槍”,甚至“第一爆”“第一炸”“第一打”也是“第一槍”。無形的“第一槍”更符合特定狀態下的語義,也更有利於分析首義志士們敢為人先的先鋒作用。
也有人糾結於武昌首義的發動到底是“第一槍”在先還是“第一把火”在先,誰在先誰就更具歷史意義,因此提出武昌首義不是“第一槍”,而是“第一把火”揭開起義大幕的。金衝及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認為,武昌起義是以城外輜重隊李鵬升首先點燃草料庫為發難訊號的,因此不應該叫武昌首義“第一槍”,應該叫“第一把火”,承認城外首先發難的歷史地位。實際上“第一把火”也好,“第一槍”也好,它們都是強調哪個事件是揭開這次起義大幕的標誌,也就是一個符號和象徵,都統稱為“第一槍”也未嘗不可。
(四)將工程八營發難一事整體視為起義的“第一槍”
羅華慶在《武昌首義第一槍》一文中指出,武昌起義是工程八營的革命黨人率先發難,而組織、領導發難的熊秉坤又是工八營革命黨人的總代表,將工八營發難之事整體視為起義的“第一槍”,更能渲染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馮天瑜先生在其專著《辛亥首義史》與《辛亥武昌首義史》當中,分別以“1911年10月10日夜,城內工程第八營率先打響起義槍聲”和“1911年10月10夜城內工程第八營打響起義第一槍”作為段落小標題,詳細講述了武昌首義當晚工程第八營革命士兵與清兵戰鬥的英勇事蹟,並以“是夜,城內工程第八營率先打響第一槍”作為最後總結。王天獎、劉望齡也認為工程八營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隨後,熊秉坤“即命令整隊猛撲楚望臺軍械庫,以求一舉奪取軍事”。毛磊、毛傳清等人認為,“以熊秉坤為黨代表的工程八營的革命者打響了武昌首義的第一槍”這個說法強調了集體的作用,更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伍立楊亦認為熊秉坤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事發時的實際領導組織者,他率領工程八營“冒險發難”,打響的是“首義的第一槍”。
(五)將推動武昌首義走向勝利的關鍵性行動都看作是“第一槍”
武昌首義,既是一場恐慌之中由基層士兵發起的兵變,也是一場由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大革命組織經過精心準備、精心策劃發動的起義。從歷史的必然法則和歷史的合力理論來思考,我們更應該把“第一槍”的標準放寬,即推動武昌首義走向勝利的關鍵性行動都可被看作是某種意義上的“第一槍”,而這些關鍵性行動的領導者、發起者都可以享有這一殊榮。郭國祥、王欣欣在《武昌首義“第一槍”新探》中認為,武昌首義,出現了一個英雄群體,他們在不同的時間段都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如第一策劃者蔣翊武,不僅是起義的直接策劃者,也是首義當晚制定行動計劃的總指揮;第一試爆者孫武,既是共進會的首領,更是身體力行,試爆炸彈,點燃熊熊革命烈火的先驅;第一個向清兵扔炸彈者楊洪勝、第一個和清兵扭打者金兆龍、第一個點火為號者李鵬升、第一個向清兵開槍者程正瀛、第一個吹響起義哨子者熊秉坤,這些人都是革命黨人的精英和先驅,他們不但參與了起義前期的各項準備工作,而且在正式起事過程中各自作出了開創性的歷史貢獻。這些革命先驅,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都發揮了特殊的開路先鋒的作用,毫無疑問都暗合廣義“第一槍”的內在含義。而且,這個群體的無形的“第一槍”比個體的有形的“第一槍”更具歷史意義,也更能反映歷史發展的人民性、客觀性和必然性[21]。
綜上所述,學術界有關武昌首義“第一槍”的研究已經從狹義的單一史實性研究逐漸發展到了多層次理論研究以及系統性的群體研究,總體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具體研究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可以突破的地方,例如,如何從有形和無形、個體和群體、歷史必然性和偶然性、歷史事實和歷史評價相結合等多角度來看待“第一槍”,就還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特別是歷史已經遠去,而當事者留下的各種回憶性史料並非盡善盡美,有的道聽途說,有的侷促一隅、管中窺豹,有的自說自話、自相矛盾,有的“是非顛倒,貪天之功”,要對這樣一些史料抽絲剝繭,還原歷史的本真,揭示這樣一個英雄群體的具體的歷史貢獻,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