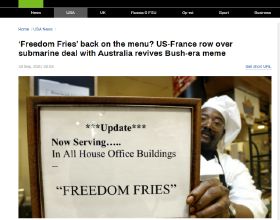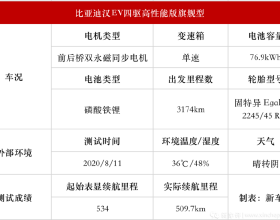從廣義上講,漢匈之間的“和親”其實是包括“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在內的一個寬泛概念,即“和親”、“賂遺”、“互市”三種“羈縻外交”手段的總稱。而狹義的“和親”則特指西漢借公主下嫁與匈奴結成姻親,從而改善兩國外交的聯姻行為。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婚姻是人類歷史上傳統的外交手段之一。原先相互激烈衝突的兩大陣營,為了解決彼此之間的利益糾紛,往往選擇安排雙方的作為籌碼,從而使雙方建立起一個基於婚姻紐帶的利益共同體的糾紛解決機制。
西漢與匈奴的“和親”,究其本質正是符合上述定義的外交聯姻。“和親”作為西漢對匈奴“羈縻外交”手段的一種,始於劉敬對漢高祖劉邦的建議:將長公主下嫁冒頓單于,讓劉邦成為對方岳父,這樣可在外交上佔據高輩分的優勢地位。
筆者推測劉敬提出將“和親”作為一種“羈縻外交”手段,很可能是受了《春秋左傳》中“鄭武公伐胡”故事的啟發:“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鄭武公以此讓對方放鬆警惕,然後出其不意而大破之。
作為一名熟讀儒家經典的飽學之士,劉敬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典故,因此他向劉邦進獻的和親之策應當有“將欲奪之,先固與之”的深層含義。
儘管西漢聲稱以皇家公主下嫁匈奴,但實際上派往匈奴“和親”女子的身份是多變的。最初,劉邦依劉敬之計準備派遣長公主,但受愛女心切的呂后阻撓,最後僅以“家人子”冒充公主和親。
所謂“家人子”就是入宮後未被封為嬪妃的良家女子。漢文帝時,為了增強和親對匈奴的制約作用,西漢與匈奴對高祖時期的舊約做出了重大修訂,將和親女子的身份規格從“家人子”提升為宗室女,但這些出自遠親支脈的宗室女多數是有罪諸侯王之女。
漢元帝時,歸順的呼韓邪單于自請當漢朝女婿,元帝於後宮女子中選拔志願者,最後家人子王昭君應徵。
王昭君出塞之後,漢匈和親依然持續,但西漢和親女子姓名均不載於史冊,可以推斷這些女子的身份並不高貴,所以說,自始至終西漢都沒有一位真正的皇家公主出塞。
當然,匈奴並不在意公主身份真假,因為其看重的不是漢朝美女,而是“和親”背後附帶的財物、關市等經濟利益,所以“為了獲利,也不惜為人子婿”史料記載匈奴曾多次主動請求與西漢“和親”就是明證。
對於西漢來說,由於有了漢匈和親這層特殊關係,漢朝使者可以借出使匈奴之機拜訪“公主”,獲取一些有關匈奴動向的重要情報,這為西漢外交及時應變提供了便利。再者,西漢每年向匈奴輸送的糧食、美酒、絲綢等物也可以說成是孃家人送給出嫁“公主”的“慰問品”,至少在名義上免去了向匈奴稱臣納貢的尷尬。
西漢借“和親”與匈奴結成姻親關係,並陪嫁大量經濟物資,這是希望對其施加籠絡,使其減少對邊境的襲擾;寄希望於和親女子誕下單于繼承人,從而令西漢皇帝可以憑祖父身份對匈奴單于發號施令,則很明顯地表現出控制匈奴的外交意圖。但是,“和親”之策也有明顯漏洞,那就是萬一西漢皇帝先於匈奴單于去世,那麼年長的匈奴單于相對新任西漢皇帝反而會佔據輩分優勢。
況且,漢匈既透過“和親”約為對等的兄弟之國,西漢就必須尊重匈奴風俗,這就給了匈奴對西漢進行外交反擊的法理依據。
劉邦逝世後,冒頓單于向呂后投來含有“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侮辱性語句的國書,乘機試探其對匈奴的外交態度。
由於男丁去世兄弟續娶其妻是匈奴風俗,冒頓單于以“劉邦之弟”身份續娶其遺孀呂后合乎規矩,故呂后雖大怒卻不得不遣使回贈國禮、曲辭答謝。再說,匈奴對所謂“公主”的身份其實心知肚明,故“公主”之子從未被立為單于繼承人。
基於以上理由,後人多以“和親”之策為“屈辱外交”、“綏靖外交”的代名詞,然而他們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劉敬明確指出長公主下嫁是“和親”之策的核心,否則匈奴單于必然“不肯貴近”,也不可能有漢族血統的匈奴太子被立為單于,“羈縻”也就無從談起。
可劉邦礙於呂后疼愛長女的情面讓家人冒充長公主和親,至此劉敬外交設想的前提條件已泡湯。在實際外交政策與最初設想偏離巨大的情況下,效果不理想是在情理之中的。
更何況,公立道德與國家利益不能劃等號,在西漢立國根基尚淺、內憂外患的客觀條件下,公立道德甚至應當服從國家利益。西漢採取“和親”之策爭取戰略緩衝期的做法雖然犧牲了公立道德,卻是契合國家利益的。
總的來說,“和親”作為最早被西漢採用的“羈縻外交”手段,其籠絡作用有餘而控制作用不足。當西漢前期處於外交弱勢地位之時,“和親”並未起到預期的“不戰而漸臣”的控制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漢匈兩國的矛盾,為西漢贏得了一段寶貴的戰略緩衝期。
無論如何,“和親”都在漢匈外交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在緩和兩國關係、增強雙邊交流、促進民族融合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值得後人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