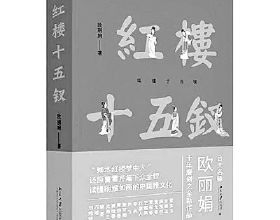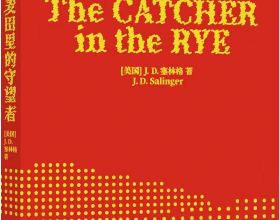文/陶謝
諾貝爾獎開獎季,最引人矚目的當屬文學獎,這倒不是說文學比醫學生理學、化學、物理學更重要,而是因為文學講的是“普通話”,離生活更近。人們可能不關心“身體如何感知溫度和觸覺”,不清楚德國化學家本傑明研究的“對稱有機催化”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們都聽得懂一個作家、詩人在說什麼。
其實若從功利和解決實際問題來說,文學可能沒有理工科直接有效,如今世界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遊的,沒有一樣是文學家直接創造出來的,所以薩特有一句名言:“小孩子都快餓死了,文學還有什麼用?”
薩特這句話是什麼情況下說的,又具體指的什麼?查不到。薩特本人就是哲學家、文學家,終身以此為職業,而且他還是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的最有名的一個人,但是他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因為文學沒有用,而是不想給讀者壓力。在給評委會的信中他寫道:“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他只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他所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其讀者產生一種壓力,我認為這種壓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保爾·薩特還是保爾·薩特——諾貝爾獎獲得者,這決不是一回事......”
有意思的是,諾獎評委會正是因為薩特所堅守的自由精神,才把獎項頒給他,理由是“為了他那富於觀念、自由精神與對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諾獎評委會有一種執拗精神,只按自己的標準行事,想頒給誰就頒給誰,愛領不領。
再回到薩特那句話。人類不是總面臨生死一線的極端情況,一片面包、一瓶水、一丸藥,小孩子活過來,還要面對漫長的人生,他要面對的不止是物質世界,還是一個精神世界。人的意義是什麼?生存——而不是生活——的意義是什麼?人為什麼能走到今天,創造出繁榮的物質世界?又如何讓明天變得更好?說到底,撐起這個世界的,是人類的精神力量,而這正是文學所要闡釋和加持的。作為實業家的諾貝爾,把不直接產出效益的文學列為獎項,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從1901年至今,全世界共有118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羅曼·羅蘭、泰戈爾、海明威、川端康成、索爾仁尼琴、馬爾克斯……這些閃耀的名字,雖說不完美有偏頗有爭議,遺漏了托爾斯泰、魯迅、毛姆、卡夫卡、普魯斯特這樣的文學大師,總體還是被認可的,不然也不會受到這樣熱烈的追捧。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爆出大冷門,不是呼聲最高的村上春樹,也不是熱門的昆德拉,而是頒給了73歲的坦尚尼亞小說家阿卜杜勒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獲獎理由是“因為他對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文化和大陸之間的鴻溝中難民的命運的毫不妥協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古爾納的作品沒有中文版,不僅中文讀者陌生,其他國家讀過他作品的人也不多,屬於小眾作家,他的名字也沒出現在賠率榜裡,這是和往年不一樣的地方。2017年評委會曝出醜聞,內部人員把獲獎名單洩露給博彩公司。為挽回聲譽,瑞典文學院改組評委會,暫停頒獎一年。
今年評委會把目光投向遙遠的非洲大陸,古爾納也是繼1986年奈及利亞索因卡之後35年來獲獎的第一位非洲黑人。據介紹,古爾納早年以難民身份移民英國,雖然是用英語寫作,但他關注的是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的議題,特別是難民題材,非常有現實意義。
諾貝爾文學獎似乎在對一直以來的歐洲審美正規化糾偏,變得嚴謹,也具有國際視野了。遠離商業誘惑,拒絕權力脅迫,重要的是摒棄偏見,才能使這一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大獎更客觀,更有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