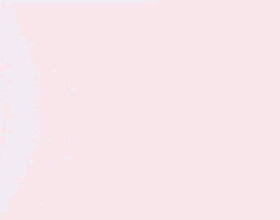作者:王雪瑛
今年是蕭紅誕辰110週年。一直以來,“四大才女”“傳奇愛情”“悲涼早逝”……這些貼在蕭紅身上的標籤,讓不少人更關注、更熟悉的是蕭紅的身世。筆者以對蕭紅的代表作《生死場》《呼蘭河傳》的解讀,賞析蕭紅文學創作的獨特韻致,探究蕭紅文學創作的當代意義。她以“翩若驚鴻,婉若游龍”的筆致開拓了現代文學的敘事空間,她對時代命題的揭示,她對自然之美的書寫,她對人類情感價值的堅守,讓我們感受文學原鄉雋永的魅力。她以純真開闊的悲憫情懷創造的文學世界依然吸引著當代讀者,蕭紅是一個活在當下的作家。
《呼蘭河傳》 蕭紅 武漢出版社
魯迅先生寫於1935年的序言,成為筆者近日重讀蕭紅代表作《生死場》的有力引導:“從《生死場》,看見了抗日前期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
以悲憫書寫黑土地上人民的疼痛
蕭紅出生於一個男尊女卑的地主家庭。封建意識、封建文化猶如無形的鎖鏈束縛著青春的生命,是順從地接受沒有自主的生活,還是在冒險的反抗中走出一條充滿挑戰的新路?在哈爾濱的中學讀書時,蕭紅已經閱讀過魯迅的著作,接受過五四新思想的薰陶,還參加過學生愛國運動。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她選擇勇敢地出走,離開了有著父親冷漠和專制的家,向著白雪皚皚的無邊的大地奔去,從此走上了充滿艱辛的人生旅程。
蕭紅是封建禮教的破壞者,她的出走和反抗被視為家庭的恥辱,她被當作異類受到家族和周圍人的排斥。掙脫身上的枷鎖,面對現實的困境和內心的疼痛,蕭紅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思索,讓她更深切地體會到了那些固守於故鄉土地的農民的悲慘境遇,壓抑他們身心的雙重枷鎖,她握著手中的筆,以一顆憂患而悲憫的心,書寫著黑土地上人民的疼痛。
1933年元旦,蕭紅髮表了第一篇小說《王阿嫂的死》,敘述了失去丈夫的孕婦與孤兒的悲慘命運。她從此開始了在漫漫漂泊中,與困頓交戰的寫作生涯。1934年4月,蕭紅在哈爾濱開始了《生死場》的寫作,此作收筆於1934年9月的青島,出版於1935年12月的上海,與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葉紫的《豐收》一同編入“奴隸叢書”,書前是魯迅先生的序言,書後有胡風先生的讀後記。從此以蕭紅的筆名發表作品。
《生死場》展開了上世紀初北中國鄉村的生存畫卷,敘寫“九一八事變”前後,黑土地上的農民“生”與“死”的故事。他們長年累月地辛苦勞作在沒有希望的土地上,嚴酷的生存條件使他們掙扎在溫飽線上,高遠天空中的流雲,身邊田壟中的高粱,冬日的飛雪,盛夏的驕陽都難以撫慰他們輪迴勞作中荒涼的心田。
蕭紅的小說不依賴懸念和情節,而是以豐富的細節、生動的筆觸全景式地展開了鄉村中的家庭生活,貼近這些人物的種種遭遇和心情,最終呈現了這“忙著生,忙著死”的悲涼境遇。“生死場”的“場”,既是百年前那塊災難深重的黑土地,又是那塊土地上一個個痛苦的靈魂。《生死場》後七章描述了在日寇鐵蹄蹂躪下,東北農民在悲慘的生活境遇中漸漸甦醒的民族意識和反抗情緒。
蕭紅不同於一般女性作家,從敘寫女性的情感故事開始自己的文學寫作,她沒有侷限於傾訴自我內心的疼痛,而是敘寫生死場上農民艱辛矇昧的生存狀態,女性遭受著身心的磨難和煎熬。小說對人性的叩問中,有著對傳統文化心態的反思,對人的生存境遇的探究中,有著對國民劣根性的反思。蕭紅敢於從“生”與“死”這個人生根本問題上來直面和呈現彼時北方農民的生活,敢於關注和揭示時代和社會的重要命題。那一年蕭紅才24歲,還是個文學新人,文壇大家魯迅、胡風對蕭紅創作的有力肯定,使得小說出版後引發了廣泛反響,《生死場》成為蕭紅的代表作,匯入了上個世紀30年代“為人生”的文學主潮,為中國現代文學留下了重要的文字。
呼蘭河的女兒心裡最誠摯的吟唱
1937年10月蕭紅在武漢開始寫作《呼蘭河傳》,而後她隨丁玲去了西安,受丁玲之約,和塞克等人共同創作了表現民眾奮起抗日的話劇《突擊》。1940年1月蕭紅和端木蕻良離開了遭受日寇轟炸的重慶,一起抵達香港。1940年12月20日,蕭紅在離故土千里之遙的香港,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以拼盡心力的寫作完成對故土最深情的回望,這也是呼蘭河的女兒心裡最誠摯的吟唱,吟詠出餘音不絕的藝術魅力。1946年10月茅盾先生以長文抒發自己的讀後感:“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悽婉的歌謠。”
《呼蘭河傳》以宏觀俯瞰的視角,按空間順序勾勒出呼蘭小城的總體格局,以舒緩質樸的語言,以蕭紅童年生活為線索,敘述著以“呼蘭河”為中心場景的的小城故事,展示了20世紀初期“北中國”的鄉土人生和人情百態,有祖父抱著“我”學詩歌,領著“我”學種菜的日子,有養豬的、漏粉的、拉磨的、趕車人的貧困日子,有團圓媳婦、馮歪嘴子、有二伯等人的悲涼故事;有唱秧歌、放河燈、跳大神、野臺子戲的民間盛舉,有呼蘭河的人在人間被風霜雨雪吹打著的平凡日子;有“我”在荒涼的園子裡和寬廣的天地在一起,心裡思索著“我”將來一個人也可以走得很遠…… 《呼蘭河傳》不是為某一個人寫傳,而是為蕭紅生於斯、長於斯的小城寫傳,不僅描摹出鄉民的生存境況和精神狀態,還留下了與呼蘭河同在的人物形象。
坐得筆直,走得風快的小團圓媳婦,在“我”家做了30年,還是一貧如洗的有二伯,以拉磨謀生的馮歪嘴子勇敢地爭得做人的權利,表現出生的堅強和活的勇氣。蕭紅不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她以有二伯、胡家婆婆等人物形象,進入那個時代國民文化心理和人格深層,揭示了“看客”的麻木,封建文化的陋習,同時她以貧窮磨倌馮歪嘴子的人生經歷,寄託了人性中善與愛的希望,呈現了《呼蘭河傳》以珍愛生命為核心的倫理和詩學。
這是一種和自我的生命一起成長的文學書寫,這是一種對故鄉的土地滿懷眷戀和審視的文學創作。北中國的大地是蕭紅從小生活的故土,也是她永遠的精神領地,文學的原鄉,她對故鄉土地和農民的認識,逐漸深入到故土和人心的內裡,看到它的陽光,也看到了它的陰影,她的心在一個明暗相交的世界裡吟唱著不屈的歌謠,“我不能決定怎麼生,怎麼死。但我可以決定怎樣愛,怎樣活。”她以筆書寫著生生死死的生命故事在歲月裡的悲涼和堅強,“向著溫暖與愛的方向,懷著永久的憧憬與追求”,這是蕭紅在與外部的動盪和黑暗抗爭時,對自我的生命價值和人生方向的選擇,這是蕭紅對人類情感價值的頑強堅守,是對人與時代、人與命運的關係的思考,構成她文學創作豐厚的情感和思想的基礎。
北方的嚴寒冰雪不能凍結她的青春熱血,時代的飛沙走石動盪裂變沒有迷惘她的執著追求,人生的風雨交加也沒能阻擋她的傾心書寫,從21歲到31歲的10年間,蕭紅寫下百萬字的作品,文體涉及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和評論。她留下了《生死場》《呼蘭河傳》《馬伯樂》等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力作,無論是魯迅先生對《生死場》精要的力薦,還是茅盾先生對《呼蘭河傳》透徹的理解,都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肯定了蕭紅的文學創作有著直面現實的時代內涵,明麗獨特的藝術韻致。
蕭紅為我們創造了一個豐富的文學世界,她的從北中國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文學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她的文學探索,面向對人性的追問,對人的命運的關注,這是文學永恆的命題;她的文學創作面向人與自然的關係,寄予著人對於自然的敬畏與依戀,這是人類恆久的情感。我們處於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萬物互聯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新冠疫情影響著世界的格局,當下的我們更加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思索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蕭紅以人的生命價值為核心的文學探索觸及了文學的本質,以人與自然的依戀為情結的文學書寫構建了童真與詩意的美學意境。富有生命力的文學作品猶如星月輝映江河,穿越時空依然閃耀著清輝,在讀者的心裡喚起真切的迴響。蕭紅是一個活在當下的作家。(王雪瑛)
來源: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