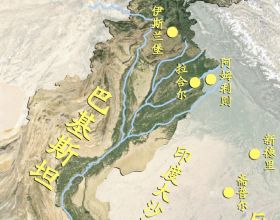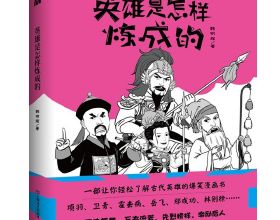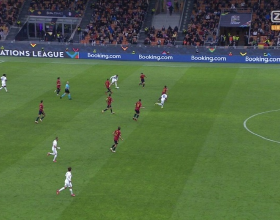2019年,陳彥以《主角》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這一殊榮對他而言可謂實至名歸。與單純的小說作者不同,這位中國最具權威性的長篇小說獎的新晉得主,首先是一位劇作家。長期以來,他堅持戲劇、小說的兩棲寫作,兩副筆墨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在兩個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佳績。
《主角》的修煉之道
檢索陳彥人生和創作的“關鍵詞”,一個“戲”字躍然而出,他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任職編劇25年,還交叉任職過十幾年團長、院長,是個資深而純粹的“戲曲人”。他深知“吃戲飯”的艱難,對戲裡戲外穿梭來往的各種人物極具“同情的瞭解”,對他們的言行舉止、心思情緒有精細的揣摩和精準的表現。他創作的《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等劇作已成為既叫好又叫座的經典,是各個劇團和眾多名家爭相排演的“吃飯戲”。他三次贏得“曹禺戲劇文學獎”和“文華編劇獎”,推出的隨筆集《說秦腔》被譽為內行說戲的大手筆。這些成績背後,屹立著陳彥一個始終不變的理念判斷——“文學是戲劇的靈魂”。因而,以小說的形式直抵戲劇以及戲劇人的靈魂便成為他順理成章的選擇。
多年來,沉浸在秦腔、戲曲、戲劇的藝術氛圍,周旋於舞臺小世界和人生大舞臺,陳彥的全副身心和手中筆墨像陀螺般在臺前幕後高速旋轉,佳作源源不斷地從他的筆端流淌出來。無論是為演出提供“一劇之本”,還是借小說展現百味人生,與“戲”有關的人和事都是他創作素材和靈感的來源。他尤為關注戲曲藝人這個特殊的群體,以及傳統戲曲特別是地方劇種舉步維艱的生存狀態。
回溯陳彥的小說創作歷程,以戲養文、以文演戲、文戲並舉的創作策略產生了正向疊加的效果。《西京故事》首先以舞臺劇的形式面世,巡演二十多個省市,反響熱烈,但因受制於演出時長,不得不割捨了很多“有意味和有價值的東西”。為彌補這一缺憾,作家又用長篇小說的形式將之重述增容,大大提升了題材表現的深廣度,這次改寫成為陳彥長篇小說的“處女作”。繼之的《裝臺》描寫了刁順子帶領的以“裝臺”為業的人們日常謀生的甘苦,出場人物涉及編導演等舞臺演出的各個部門。這些“戲中人”錯綜複雜的關係敘事,使小說的情節推演極其生動形象,堪稱人情世故的大展演。
這兩部長篇小說和劇本的創作,在一定意義上,既是《主角》的“前情敘事”和“背景延展”,也是寫作技巧的反覆試驗和磨鍊。這些因“戲”而生的文字,故事情節迴環交疊,人物形象參差錯落,彼此之間存在盤根錯節的“互文性”,再到《主角》的寫作,內容和形式的積澱產生了一種敘事上的“蝴蝶效應”。
《主角》的新意在於敘事角度和敘事策略的移步換形。與《裝臺》相比,陳彥不再劍走偏鋒,而將焦點聚於舞臺上的主角,並使其與身邊人物呈現複雜的對映和折射關係,形成極具立體感和周延性的全景展示。陳彥常年紮根院團,與藝人群體處成了心念所繫、身難抽離的魚水關係,對這個圈子冷暖盡知,愛恨交織,情感和理智幾經發酵,才釀造出《主角》這泓美酒,才能做到下筆滔滔而無一句模糊敷衍的“水詞兒”。
就其本質而言,《主角》既是主人公憶秦娥的成長史和成名史,也是眾多戲曲藝人的合傳,更可視為陳彥的心靈自白。小說滲透著作者對戲曲藝術及其從業者的深情守望,貫穿著對他們所遇困境的細緻描摹和深度剖析,揭示了戲以人傳、人以戲名、人與戲彼此成全的血肉關係。一言以蔽之,“戲”是“主角”安身立命的人生支點。
儘管有漫長的近乎面面俱到的準備工作做依託,儘管動用了生活的全部積累,《主角》的誕生卻並非一蹴而就的易事。敘事的難度首先在於主角修煉的艱辛歷程,以及造就主角的戲曲生態的混沌複雜。演員從學戲到演戲,從站上舞臺到站到舞臺中間,從偶然的曇花一現到憑藉“一人千面”的藝術表現力穩居主角寶座,幾乎所有人走過的都是一條荊棘叢生、水深火熱的煉獄之旅。不言而喻,戲曲表演是一個成才率極低的行業,《主角》以主人公憶秦娥的命運遭際和藝術追求,為“主角的誕生”這一命題提供了一個全息樣本。
陳彥在“後記”中談道:“能成為舞臺主角者,無非是三種人:一是確有蓋世藝術天分,‘錐處囊中’,鋒利無比,其銳自出者;二是能吃得人下苦,練就‘驚天藝’,方為‘人上人’者;三是尋情鑽眼、拐彎抹角‘登高一呼’、偶露崢嶸者。若三樣全佔,為之天時、地利、人和。”顯而易見,憶秦娥是第二種人,僅憑“一根筋”的苦練,跨越了九曲十八彎的漫漫征程,才抵達舞臺的輝煌。這個將巨大的不可能變為現實的過程,便是陳彥設計曲折情節、營造戲劇衝突的用武之地。他將這一轉變過程中的種種波折和懸念化為不斷加強的敘事動能,不僅使主角命運順勢逆轉,而且充分兼顧各個配角的訴求和作為。於是,小說中的“戲曲生態”便呈現出一種“合力”的結果,作者對人物性格與命運的“安排”更具必然性的說服力。
主角的戲夢人生
《主角》中的“秦腔皇后”憶秦娥,原名易招弟,是深山溝裡隨時面臨輟學的“放羊娃”,絕對的草根出身,她不知藝術為何物,旁人也看不出她有絲毫“藝術天分”。只因舅舅胡三元是縣劇團的“打鼓佬”,為了一個吃商品糧的名額,帶她去考劇團的學員班,並給她改名易青娥,希望她像省城同名的“大名演”一樣成名成家、出人頭地。從此,這個怯弱懵懂的山裡孩子便一跤跌入了坎坷多艱的戲夢人生,一旦踏上那塊眾人矚目的氍毹,她就像安徒生童話裡那個穿著紅舞鞋的小姑娘卡倫一樣,徹底淪陷,身不由己,將青蔥歲月、旖旎才情悉數奉獻給了戲曲舞臺。
易青娥的“主角前史”充滿晦暗痛楚、不堪回首的記憶。舅舅因演出傷人事故而入獄,她受此牽連,幾乎被永久剝奪了學藝的資格和機會,只能在單位食堂打下手,做個“燒火的丫頭”,苦捱時光。多虧一個偶然的機會,“忠孝仁義”四位“存”字輩老藝人發現了她敦厚純良、謙恭耐勞、自尊要強的品格,便主動授藝。從基本功抓起,按照武戲表演的高難要求,對她進行形體和技巧的嚴苛訓練,務使招式合範,形神兼備,進而悉心傳授秦腔傳統戲表演的規矩、尺寸、竅道、絕招。
在眾人因樣板戲消歇不知戲曲表演向何處去而躑躅茫然時,易青娥已被悄然磨礪成一把鋒刃尖銳的鋼錐,單等那個脫穎而出的機緣到來。終於,應觀眾要求,她在農村簡陋的草臺上演出《打焦贊》,飾演燒火的丫頭楊排風。這一“處女秀”純屬意外,上臺不免倉促,但她憑藉暗中錘鍊已久的功力,以驚豔奪人的武打,一舉成名,最終掙脫了“燒火丫頭”的真實身份,成為轟動寧州地區的戲曲新星。其主角魅力、舞臺風采光芒四射,傳佈人口,幾經渲染,簡直到了繞樑三日、令人魂牽夢縈的地步。
自此,易青娥的演藝生涯便如烈火烹油,異常紅火。她很快被調到省秦腔劇團,以“憶秦娥”的藝名風靡大西北。因主演《楊排風》《遊西湖》《白蛇傳》《狐仙劫》等名劇屢獲殊榮,巡演京滬各地、大江南北,甚至唱到了中南海,“秦腔皇后”的美名不脛而走。但盛名之下,嫉妒誹謗、流言謠諑也紛紛襲來,令她難以應對周全。可以說,憶秦娥人生的高光時刻都奉獻給了舞臺。
憶秦娥入行之初便被貼上了“傻”的標籤,眾人笑她不懂世故,丈夫怪她不解風情,面對戲之外的一切“麻煩”,她都顯得束手無策,顧此失彼,心力交瘁。經歷了兩次失敗的婚姻,智障兒子意外身亡,藝術盛期已過,不得不讓臺於自己親手培養的後起之秀養女宋雨,一路踉蹌行來,命運對憶秦娥來說,可謂殘酷得不留餘地。
失去方向感的憶秦娥回到“易招弟”放羊的山村,生活再次將她打回原形,從光彩照人的舞臺“美玉”迴歸為一文不名的山野“頑石”。至此,憶秦娥脫口吟出一闕《憶秦娥·主角》——“易招弟,十一從舅去學戲。去學戲,洞房夜夜,喜劇悲劇。 轉眼半百主角易,秦娥成憶舞臺寂。舞臺寂,方寸行止,正大天地。”這是“主角”對自己悲欣交集的藝術人生的豁然開悟,醍醐灌頂,明心見性。在“急急風”的板鼓聲中,憶秦娥沿著人生的拋物線繼續跑著“圓場”,這源自慣性,也出於藝術之美的召喚,更是個人意志的一往無前。
《主角》以此作結,應該說,實現了王蒙對陳彥屢次強調的“掄圓了寫”的期望。作家懷著巨大的悲憫,將主角引向更加高遠宏闊的“正大天地”,這是對戲曲舞臺上“大團圓”結局的反撥和昇華。小說結構的開放式結尾和人物命運的未完成狀態,喚起讀者對憶秦娥主角人生的持續回味和反思,進而引發對戲曲生態建設和發展走向的探索和想象。
小說愈到後面,愈加明晰了憶秦娥的主角潛質。她的“傻”,她的“木”,造就了她不諳世事,不“開竅”、不“靈醒”、不“玲瓏”的樣子,臺下的憶秦娥完全卸去了主角的光環,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後知後覺、腦筋迷糊的“笨人”。但正是這個天生繪事後素的胚子,才被老藝人視為可堪雕琢的璞玉,加之她愈挫愈奮的上進信念,年復一年心無旁騖、飛蛾撲火般“鑽”在戲裡,方成就了“秦腔皇后”的舞臺傳奇。
前輩藝人捨命相搏,堪為戲曲藝術薪火相傳、綿延不絕的壯烈示範,憶秦娥無法效仿,她將以身殉藝的悲壯轉化為一種心勁兒的搏殺和較量——在日常生活的繁難苦痛對其無休無止的身心圍剿中,始終保持對戲曲藝術的鐘愛與不棄。她以一種迴旋和退守的姿態去悟道“戲”之真諦,就像她所練習的“慢臥魚”技巧,一次“臥魚”的完成,從一分鐘到幾分鐘再到十幾分鍾甚至幾十分鐘,骨肉身架一寸寸銼下去,心氣的清朗竟一點點超拔飛騰起來。在這一升一降中,她體驗著藝術所遵循的“度”的哲學,尋覓著“技”與“藝”美美與共的平衡點,也獲得了心靈的寧靜和愉悅。
唯其如此,憶秦娥才能在滾滾紅塵中把持自我,堅守初心,才能在世態炎涼中寵辱不驚,靜待花開,才能遍訪民間珍稀化石般的老藝人,將幾十本上百本瀕臨失傳的秦腔老戲“背”在自己身上。這種敢於擔當的意識和毅力,這種守正傳承的危機感和行動力,使憶秦娥超越了一般意義上“主角”的職責範圍,成為為戲曲續命的智者和勇者。
《主角》如同一座透明的熔爐,全程展現了“主角是怎樣煉成的”那些至微至著的景觀。在憶秦娥身上,我們見證了煉石成金的艱辛和痛苦,更看到了化蝶涅槃的欣悅和莊嚴。讀者只有忍受著“熔爐”的炙烤,才能觸到《主角》如火如荼、噴湧怒放的煙花,才能感知小說內蘊的澎湃激情。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