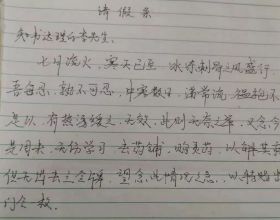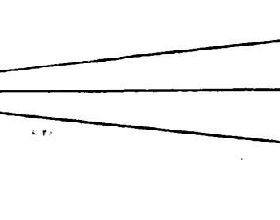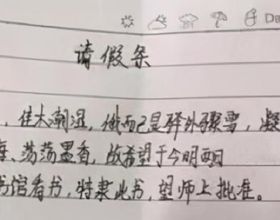最近,中國人民大學戴逸主持的《清史》完成出版了,據說是用白話文來寫的,這與以往的24史的寫法不一樣。於是人們就來議論現在的學者能不能用文言文來寫古代的歷史。說到這個問題時,我想起,前些年,中國人也熱衷於談論國學的事情,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樣,但我只提到一點,國學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它的研究成果都是用文言文寫成的,現在人們談論國學,包括對以往國學成果的研究,又都不是用文言文寫出來的。所以現在所說的國學與原來的國學就有了根本的不同。對這一點不予注意,就似乎把原來的國學與現在所談論的國學混為一談了,讓人不知道其中還有這樣嚴重的不同之處。
這次,借《清史》的撰寫與出版,就使這個問題凸現出來了。所以我今天要專門就原來的國學的成果中使用文言文來撰寫的事情談談自己的看法。
我曾在一本書中專門說到:古代中國的學術成果,在形式上與現代人所寫出來的學術成果有三個根本性的區別:
1、前者是用古代中國語言中的文言撰寫而成的,後者是用現代漢語來寫成的,姑且稱之為白話文。
2、前者的著作和文章的外在形式,與現代學者寫出來的學術著作和文章不同。正因為古代中國學術成果所用語言及撰述形式與現代學術成果不同,故都被稱為“古籍”,而現代的學者寫成的論著都不能稱為古籍。
3、古代中國學術成果的分類與現代中國學術成果的分類不同。如古代學術成果是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的,而現代學者寫成的論著是按哲學文學史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名目來分類,所以古與今的學術研究的成果,在類目上是對不上號的。
這三種不同,可以分別作為專門的問題加以討論,這裡只來說說文言文與白話文在寫學術論著上的不同的問題。
就學術成果的書寫語言來講,中國古代學者使用書面語言——文言撰寫著作與文章,這是不爭的事實,是古代中國學術成果最明顯的特點,是與現代中國學術成果最明顯的區別。
文言是古代中國的書面語言,它與現代中國語言有著根本的不同,這自不用再說了,但文言文字身還有深淺之分,清末民初的學者辜鴻銘曾專門說過這個問題:
文言或書面漢語……也同樣存在著不同種類。傳教士們曾把書面漢語劃分為簡易文理的和繁難文理的兩類。但我認為,這個分類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我看來,合理的分法應當是簡單欠修辭的語文、通行的語文和高度優雅的語文三類。……可以稱它們為普通會話的或日常事務用語、低階古典漢語、高階古典漢語。——見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黃興濤、宋小慶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88-89頁。
簡單地說,文言有簡易和繁難的差別,這是人們都承認的。簡易與繁難之外,又有雅與俗的區別。如古代的賦和駢文所使用的文言,就比一般的散文所使用的文言要繁難和優雅。古代帝王的詔書、大臣的奏章,常常使用駢體式的文言。古代還有一些學術著作也用駢文寫成,如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更多的是用駢文撰寫書籍的序文,此類最多,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佛教著作《出三藏記集》序卷所錄各種佛經的序文,都是非常繁難而又特別優雅的文言。
單從繁難角度講,一些專門領域的著作也很難懂,如古代的天文歷算類的著作,但這種著作往往只是繁難而不夠優雅,能全書用駢文寫成而且兼具繁難而優雅的著作,在古代也不多見。
古代中國在書面語言之外也有口頭語言,一般稱之為“白話”。現代提倡白話文以來,人們往往以為白話就是現代漢語,其實白話也分古代白話和現代白話,現代白話只是現代漢語的一個分支,也不完全等同於現代漢語(現代漢語也有書面語言,但現代書面語言與現代口語都屬於白話,這是與古代的文言文相對而言的)。
古代白話又與現代白話有差別,無論是句式還是用語,都有不少差異。如古代的小說,其中既有文言,也有白話,但不完全是當時的白話,而是一種半文半白的語言。在古代一些專門著作與文章中,一般以書面語言為主,但有時也會夾雜當時的白話,如《世說新語》。在古代的一些詩文中,也會夾雜著當時的白話用語。
雖然古代也有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之分,但總起來說,古代中國學術成果所用的語言主要是書面語言——文言,而與現代中國學術成果主要使用白話文是完全不同的(上個世紀有一些老先生會在特定場合使用文言文來寫論著,但這只是個別情況,不代表整體)。
這一點,是確定原來的國學與現代的中國學術最根本不同的主要標誌。換言之,如果不是使用古代書面語言(文言)撰寫的學術成果,就不能算是國學的著作,最多隻能算是研究原來的國學文獻的現代的國學研究性的成果。
現代學者之中也有人能用文言撰寫論著,但不像古代中國學者純用文言撰寫學術成果,而且其成果背後的學術理念、方法與用語,也與古代學術大為不同,因此他們的學術成果還是屬於現代中國學術,而不屬於原來的國學。此類學者及其成果,在現代中國學術中只佔少數,更多的現代學者是用現代學術的理念、術語、方法和白話研究古代中國留存下來的書籍文獻,再用現代漢語書寫其學術成果,因此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純粹的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