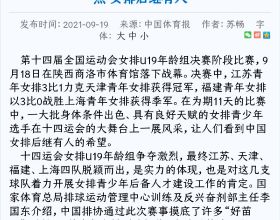(晚清, 西方人在中國 CFP/供圖)
史稷/文
鴉片戰爭中國開埠以後,一些西方人離鄉背井來中國闖蕩,很多人在中國度過大半生。不管他們從事什麼職業,他們都在一個跨文明的地帶踟躕。這個地帶充滿誘惑又荊棘叢生,一旦進入就難以脫身。
尋找文化認同
在華西方人在經歷了文化衝擊之後,或多或少會發生蛻變,產生身份認同的危機,尋找新的文化認同。正如保羅·A·科恩(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一位離開西方到中國傳教的人,一開始可能就不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西方人。在中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後,他肯定變得更不典型。在學習中文和採用某些中國習俗的過程中,他與他的新環境產生互動,一個混合的過程開始了。他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簡單的人,而是一個在中國的西方人。”晚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在日記中流露的焦慮,反應出當時在華歐洲人的典型心態,他們遠離故土,感到命運未卜:“我是一個愛爾蘭人,從我下定決心告別那裡,直到我沒有機會再回來,我始終處於一種迷惑的狀態;我的感覺變得遲鈍——然後麻木,智力也受到影響。但隨後產生的感情——強烈而持久的悔恨之情取代了以前莫名其妙而不可名狀的無視。”
“在華西方人”,特別是那些在中國機構服務的西方人,或被認為是為中國向現代化轉型作出了巨大貢獻的顧問,是尋求彌合兩種文化鴻溝的“第一代國際主義者”,或被認為是侵華帝國主義者。無論譴責殖民主義帶來的災難,還是讚揚西方人為中國現代化程序帶來的貢獻,無論從政治角如何度界定他們的歷史地位,他們都是殖民主義時代跨文化的社會群體之一。這類在華西方人的文化心理在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的著作《僱傭軍與清官》、保羅·A·科恩的著作《發現中國》以及詹姆斯·C·庫裡(James C Cooly)的《威妥瑪在中國》中都有所體現。
19世紀在華歐洲人受到三種社會群體的制約:在華西方人社群、歐洲社會和中國傳統社會。
他們首先是在華西方人社會團體的成員。19世紀歐洲列強主導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歐洲人在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多少帶有殖民主義色彩。他們在中國受到治外法權的保護,以高工資來維持相對上等的生活水平。據中國海關的英國僱員愛德華-鮑拉(Eward Bowra,1841-1874)說,北京的5個歐洲翻譯實習生,有80多個僕人、教師、廚師為他們服務。他驚訝地發現,用17或18個英鎊就能“過上上等人的生活”,而40個便士夠一箇中國苦力生活一週。他感嘆:“這真是一個令人驚歎的廉價國家”。為中國服務的歐洲僱員的工資,比他們的中國同事高得多,無論是在由戈登將軍(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指揮的常勝軍、由馬戛爾尼爵士(Sir 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管理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由法國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 和德克碑 (Paul-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1831-1875)負責的福州海軍船塢,還是由赫德控制的中國海關,都是如此。例如,在海關總署,歐洲初級職員的月薪在17、18英鎊左右,而最高階中國職員的年薪只有70英鎊。清政府之所以給在華機構服務的西方僱員高收入,如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史密斯分析,也許是因為“中國人認為所有野蠻人都是貪婪的,將物質上的吸引力視為制度控制的補償”。
在華西方人的社交生活大都侷限於西方人圈子。基督教儀式、俱樂部活動和小圈子的社交晚會是他們的消遣方式。鮑拉妻子在日記中記錄了典型的在華西方人的社交生活場景:“在過去的14天裡,這裡有一兩次野餐,但對於這種活動來說,天氣太熱了。托馬斯夫人在離這裡大約六英里的花園裡舉行了一次晚宴。……我們踏著月光回家,非常浪漫。兩天後,我們在‘海青’號上做了一次活動,這是一艘屬於海關的蒸汽船,航行了大約40英里。”我們從赫德在中國的生活中也看到英國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眾多的僕人、馬術、下午茶、花園音樂會、教堂的週日禱告等等。無論他們在哪裡定居,他們都引進歐洲生活方式,營造歐洲文化環境,慶祝所有的基督教節日。女士們是娛樂活動的組織者。例如,她們組織的“業餘戲劇表演”,表演是類似“這裡我們說法語”這樣的劇目。
在中國的大多數歐洲人既不願意也沒有興趣融入中國社會。與其說是語言障礙,不如說是殖民主義心態和晚清中國排外主義的雙重掣肘妨礙他們與中國人接觸。亨利·科伯恩(Henry Cockburn)是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的中文秘書,在北京工作了十年,精通中文,但是除了不得不與他的僕人打交道之外,他從沒接待過一箇中國人。西方人也被中國人孤立,他們居住在條約港口,很難獲得在內陸居住甚至旅行的許可。晚清當局謹防外國人滲透到中國內陸。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及其家人在中國進行了一次短暫的旅行,足以讓清朝官員震驚。正如日意格注意到的,允許歐洲人進入內地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將他們置於中國當局的管轄之下。然而這一條件又與條約港口歐洲人堅持的治外法權相牴觸。如亞洲史學家羅德·莫非(Rhoads Murphey,1919-2012)所言:“外國人被擋在帝國的邊緣”,西方人融入中國社會只是天方夜譚。
遠離自己的社會,無法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員,條約港口來自不同國家的歐洲人生活在一個同質的環境中,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似的習俗使他們更加親密。在中國的西方人形成一個人為的世界主義俱樂部,中國人則被排除在這個俱樂部之外。一位自1902年起就在北京工作的報人伍德·赫德(H.G.Wood-head)曾經如此報道漢口的外國人社群聚會:“漢口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競賽和娛樂俱樂部……一個由俄羅斯音樂家組成的管絃樂隊會在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午餐前演奏。每晚和週末及銀行假期的大部分時間,俱樂部是男人、女人和兒童聚會的場所,只有賽馬期間中國人才被允許進入。”
政治和經濟特權以及歐洲的文化氛圍,保證在華歐洲人擁有舒適的生活條件,也強化了他們的優越感。在中國機構服務的歐洲僱員當然不願意離開這種優越的環境,融入中國社會,儘管他們比較瞭解中國社會,並與中國官方保持密切聯絡。
其次,在華歐洲人屬於“某一個”歐洲國家的社會。或許在這一點上,19世紀的歐洲可以被視為一個實體。19世紀歐洲人所理解的“文明世界”是指繼承了基督教傳統和價值觀、已經工業化的西方國家,他們認為歐洲人開創了全人類的進步時代。雖然歐洲人的目標是海外經濟利益,但是普遍認為自己承擔著輸出“文明”和向其他國家傳教的使命。在他們看來,那些在地理和文化上遠離歐洲的國家是脆弱、落後並且僵化不變的。用一位在中國的傳教士的話說:“中國還沒有達到文明的頂峰,而你們(基督徒)站在比他們更高的平臺上”。他們普遍認為,中國是一個停滯不前的國家。赫德對西方人的偏見頗為反感。他批評這些西方人“習慣於將中國視為未開化的國家,將中國人視為半野蠻人:因此他們只會對中國人發號施令,而不是與他們講理。”
此外,19世紀歐洲人當中普遍存在著對非歐洲人的種族歧視的觀念。值得注意的是,對亞洲人種族歧視的觀念,是伴隨著19世紀殖民主義經濟與政治強權而產生的。正如著名印度外交官、學者潘尼迦 (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年)所言,18世紀歐洲人“對中國人的情感通常是尊重,而他們在印度也沒有滋生出種族傲慢的感覺”,而19世紀“膚色優越感的增長”,主要是由於歐洲人在亞洲具有政治強權。
儘管殖民主義將歐洲列強聚集在一起,但正如沒有唯一的歐洲海外利益一樣,也沒有唯一的歐洲價值體系。教育、榮譽觀、公民的普遍志向、宗教態度以及道德標準因國家而異,在中國的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來華之前經歷不同,行為習慣也不同。
以英國為例,儘管有經歷了光榮革命和工業革命,成為莊園主和擁有貴族頭銜仍是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夢想。用一個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話來說:“我們是一個奴性的民族,熱愛貴族和領主制,對土地的敬畏不亞於對貴族的敬畏。”在政治、經濟和知識生活中,越來越舉足輕重的中產階級渴望提高社會地位,得到一個貴族頭銜。如那時的一位歷史學家所言:“繼續上升,在社會階梯光滑臺階上奮力攀登,將出生時的等級提升一步或更多,這已經變成一種責任。”那麼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赫德在中國獲得財富、權力和榮譽之後,還要絞盡腦汁證明自己有一個高貴的祖先,並要買回他所謂的家族產業。他甚至頗費心思地設計他在愛爾蘭北部的家族的徽章和座右銘。馬戛爾尼則“決心在一生中做出業績來贏得一個頭銜。”榮譽感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另一種貴族態度。這就是為什麼戈登將軍在戰勝太平天國叛軍後,拒絕一大筆賞金,卻渴望得到清廷的最高勳章——黃馬甲。較之在華其他歐洲人,獲得貴族身份是在華奮鬥的英國人特有的頑念。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等級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平民出身的英國年輕人在英國海外殖民地找到了跨越階層致富的機會,正如英國曆史學家查理·德拉吉(Charles Drage)提到中國海關僱員愛德華·博拉的職業生涯時所言:“在這裡,一個人的事業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像在墨守成規、虛偽、瀆神拜物的英國,他的事業不受階級和種姓偏狹的束縛和嫉妒的競敵的掣肘。”
總之,在華西方人在試圖塑造他們本國同代人視為成功的人生。
微妙的關係
傳統的中國社會,無疑是影響西方人,特別是西方顧問跨文化經驗的第三種社會形態。晚清的中國社會和其他亞洲傳統社會一樣,因西方的入侵而受到干擾,但是中國傳統的官僚經濟和社會結構並未瓦解,條約港口城市的出現遠沒有改變中國古代城市的面貌和生活模式。赫德的侄女說:“踏進北京的大門,就像回到中世紀。”這也許有點誇張,但這一印象反映出在一個歐洲人眼裡,晚清中國社會與歐洲現代社會之間的反差之大。在19世紀,一個在中國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西方人面對的,是一個結構出乎意料地僵化而複雜的異質社會,無論他是欣賞還是厭惡中國文明,都必須對中國的傳統社會秩序和道德體系做出反應。
如果清代中國對一個普通的西方人來說,不僅是一種外國文化,而且更是一個遙遠的時代,他們可以遠觀或評判中國的官僚行政、經濟制度、習俗和道德,或者僅僅享受一種異國情調。而天朝的西方僱員則必須深諳中國的傳統經濟框架、中國官場、宮廷禮儀以及中國的傳統價值體系,善於處理各種微妙的關係,以完美地演繹他們在中國僱主和西方政權之間的中介角色。
西方的顧問們沒過多久就明白,在中國與官員的關係比法律要重要得多,因此爭相與出入朝廷的官員建立親密關係。英國赫德受到恭親王信任;英國人馬戛爾尼和德國人德璀琳(GustavvonDetring,1842-1913)是李鴻章的密友;而法國人日意格則是左宗棠的門客。馬戛爾尼甚至在儀式上向中國高官行叩頭禮,給大多數外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赫德完全瞭解中國和歐洲稅收制度之間的差異,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地方官員的勢力。他在日記中分析,中國的稅收取決於官員的個人素質而不是法律,他必須面對這種傳統稅收制度,如果沒有地方官員的同意,很難為一項公共事業獲得財政支援,而他提出一個現代化專案時,也絕不能忽視地方政府。
雖然歐洲顧問在中國的現代化程序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卻又依附於紮根於傳統框架中的清朝政府。赫德很現實,體會來自朝廷的指令和意圖,深知他們的工作實際上就是維持清朝的統治:“我們幫助中國保持安靜,維護了王朝的穩定,我希望這是有意義的。”當然,如果說西方顧問依附清朝,是因為這個古老的帝國賦予了他們一切:權力、財富和榮譽。但是不能否認,由於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瞭解,使得他們能更理性而悲觀地觀望清廷。他們雖然深知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但對中國的徹底改革不抱幻想。赫德對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和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參與1889年的改革持懷疑態度,認為“他們改革中國,重塑其機構,簡而言之,讓政府維持下去,這種想法過於美妙。”在馬戛爾尼看來,清朝就像“其他法律有機體一樣,雖然半死不活,但也會在衝擊中倖存下來。因為中國的朝代就像中國的陶器一樣,具有幾乎無法想象的被修補的能力。裂開的花瓶可能被砸得千瘡百孔,但仍然可以透過修修補補來告訴人們其古老,儘管它可能再也不能盛水。”是不是因為他承擔了保護這個“破裂的花瓶”的責任,才策劃了綁架孫中山並把他關在中國駐倫敦公使館的陰謀?因為孫中山是個想顛覆清王朝而不是修補王朝的人。
總之,條約港口的歐洲社群、歐洲社會和晚清的傳統中國社會,構成了晚清在華西方人的文化背景。為大清政府效勞的西方顧問,生活在相同的環境中,或多或少與他們的同胞有著相同的心態。他們與其他在華西方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社會對於大多數在華西方人來說是陌生的,而他們由於參與中國的現代化程序,更要與中國傳統社會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