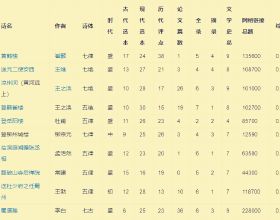天寶十二載(753),開天盛世呈現全盛局面,“是時中國盛強”(《資治通鑑》卷216);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從盛世到亂世的轉換,不過短短兩年。
開天盛世不是一天就能打造,安史之亂亦非一天就能引爆,更不是所謂“紅顏禍水”所致。制度調整的失誤,朝臣黨爭的分裂,玄宗晚年的怠政,種種因素彙集在一起,終於將盛世霓裳羽衣曲變奏為亂世悲情長恨歌。
“文學”與“吏治”的黨爭
從開元初年起,由於用人標準的差異,朝中逐漸形成“文學”“吏治”兩派。“文學”是指透過科舉進士起家,長於文學之士;“吏治”指長於吏幹、善於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姚崇的舉薦者、“吏治”派先驅狄仁傑直言,“文士齷齪”;“文學”派領袖張說則認為,大臣應“以無文為恥”。
玄宗剛即位時,重用“吏治”派姚崇、宋璟等人,幫助自己安定皇位、整理朝政。各項政務走上正軌後,唐朝面臨財政改革和大興文治問題,玄宗擺出了“文學”“吏治”並重的用人格局。開元九年(721)二月初十,玄宗任命“吏治”派宇文融,主持清查全國田畝戶口賦稅的括戶工作,充實國庫。九月十九,玄宗任命張說為兵部尚書並拜相,後升中書令任首輔,讓其改革軍事體制,構建禮儀制度,推行文治。
張說、宇文融剛開始在表面上相安無事。張說曾為赴各地括戶的宇文融寫詩送行,對括戶政策表示支援,“念茲人去本,蓬轉將何依”,哀憐百姓離鄉去土,無所歸依;“外避征戍數,內傷親黨稀”,指出戶籍不附導致朝廷無法有效組織民眾服兵役徭役鞏固邊防。然而囿於黨派之見,張說擔憂宇文融“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
宇文融主持括戶時,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人反對,而總後臺是張說。開元十三年(725),宇文融括戶取得重大成功,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張說奏請封禪泰山,以彰顯文治之功。十二月十二,張說成功主持封禪大典,顯示出其在文采之外傑出的組織能力,但他“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
第二年四月初四,宇文融聯合李林甫彈劾張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玄宗將張說罷相。此後,“吏治”派又多次誣陷張說,“文學”派持續為張說喊冤。玄宗不勝其煩,於開元十五年(727)二月勒令張說退休,貶宇文融為刺史。
不久,玄宗因懷念與張說的私人感情,將其起復為沒有任何實權的左丞相。玄宗亦看重宇文融的理財能力,於開元十七年(729)將其召回朝廷並拜相。宇文融有次在宮宴上作詩表示,“誓將同竭力,相與郊塵涓”,大有以宰相身份融合“文學”“吏治”兩派的手筆。
但不到百天,宇文融因貪贓事發,在流放路上病逝。開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張說去世,被他作為接班人培養的張九齡成為“文學”派新領袖,李林甫開始挑起“吏治”派大梁。
寫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張九齡被罷相
張九齡被玄宗贊為“文場之元帥”,文學詩詞極佳,尤以《望月懷遠》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最為世人稱道。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淵堂弟長平王李叔良曾孫,按輩分是玄宗叔叔。開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張九齡拜相,並於第二年五月升任中書令執掌朝政。同一天,李林甫也以禮部尚書的身份進入宰相班子。“文學”“吏治”之爭,正是在他們手上達到頂峰。
擔任首輔後,張九齡專意提拔“文學”之士的用人原則,屢屢引起玄宗不滿。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玄宗意欲提拔政績卓著的朔方(今寧夏靈武市一帶)節度使牛仙客升任六部尚書。張九齡反對,認為牛仙客“目不知書”;李林甫則提出“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十一月二十三,玄宗採納李林甫意見,雖沒有升牛仙客為尚書,但封爵為隴西郡公。
張九齡因此事心生退意,寫下《歸燕詩》,“海燕雖微眇”,用海燕“微眇”隱寓自己出身微賤,不比李林甫天潢貴胄;“乘春亦暫來”,說自己在聖明時代暫且來朝做官,如燕子春來秋去,不會久留;“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堂日幾回”,比喻自己在相位日夜操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則是告諸李林甫等“鷹隼”,自己無心爭權奪利,切莫再來中傷攻訐,但這只是張九齡一廂情願。
《望賢迎駕圖》,南宋佚名繪。此圖描繪的是安史之亂後,唐肅宗李亨在陝西咸陽望賢驛,迎接由四川歸來的太上皇李隆 基的場面。視覺中國 供圖
李林甫黨羽、戶部侍郎蕭炅的文字水平很差,曾當著張九齡心腹中書侍郎嚴挺之的面,把“伏臘”讀成“伏獵”。嚴挺之表示朝中不能有“伏獵”侍郎容身之處,張九齡遂把蕭炅貶為刺史,而李林甫託以他事誣告嚴挺之倚仗張九齡撐腰干預司法。玄宗大怒,在牛仙客事件僅過四天後將張九齡罷相,擢升李林甫為首輔宰相,牛仙客則任工部尚書並拜相。
在這次人事鬥爭中,張九齡提出“文學”標準,李林甫提出“才識”原則,各執一端,反映了當時官員尤其是“文學”派官員的素質缺陷。
張說、張九齡雖是“文學”出身,但他們久經考驗,擁有突出的經世才能。張說出將入相,對政治軍事都很熟悉;張九齡“文學政事,鹹有所稱”。但他們提拔的文士,起草詔書還算在行,理政能力比較缺乏。此時的唐朝,政事日益繁雜,邊境形勢日益嚴峻,玄宗迫切需要加強對全域性的掌控,提高財政汲取能力,應對周邊民族集體崛起的挑戰。“文學”派根本無力處理這些事務,這是玄宗執意提拔牛仙客、在用人上完全倒向“吏治”派的深刻原因。
被貶後,張九齡寫下十二首《感遇》組詩,明面詠物,實則吐露心境。其一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比喻賢人君子潔身自好,進德修業只是盡人臣本分,非求富貴利達;其四用“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以孤鴻自況,以雙翠鳥喻李林甫、牛仙客,“側見”一詞頗顯二人氣焰熏天,令人側目。
開元二十八年(740)春,張九齡去世,“文學”派徹底失勢。李林甫“條理眾務,增修綱紀”,幫助玄宗繼續構建集權型政治體制,同時大刀闊斧改革經濟、軍事、法律制度,助推開天盛世最終形成。
但“吏治”派推行改革只從一隅一處著眼,不如“文學”派善於從全域性著眼,導致節度使制度等改革走過了頭。而且“吏治”派一切唯玄宗旨意是從,從不敢抗拒李林甫任何指示,不如“文學”派大臣敢於直言極諫。以致玄宗全面起用“吏治”派後,改變了和宰相共商國是的集體決策方式,遇到問題就任命官員組建單獨辦事機構,越過宰相直接對玄宗或李林甫負責,權力完全集中到二人手中。
唐玄宗聽到天空飄來四個字——“聖壽延長”
開元二十五年(737)四月二十一,玄宗為了立壽王李瑁為太子,不顧張九齡強烈反對,在李瑁母妃武惠妃攛掇和李林甫支援下,逼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自殺。一日殺三子後,玄宗有所清醒,聽取高力士建議,為避免李林甫與東宮勾結,以立嫡以長為由排除李瑁,於第二年六月初三立三子李亨為皇太子。
在玄宗之前,睿宗、中宗都活到55歲,高宗56歲,太宗52歲,只有高祖李淵70歲。玄宗認為60歲是李唐皇室的魔咒,所以到天寶初年,56歲的他就開始安排後事,重用李亨內弟韋堅掌握財經大權;任用李亨舊部皇甫惟明、王忠嗣為西北邊防節度使,執掌軍權,意在給太子培養班底,準備交權。
但天寶四載(745)正月初六,玄宗在宮裡祈福時,恍惚聽見天空飄來四個字“聖壽延長”。這本是幻覺,可玄宗偏偏就信了,自認有神仙加持定會萬壽無疆,就不再考慮交班,反而放任李林甫攻擊李亨,以免李亨搶班奪權。李林甫先後製造三起大案,將韋堅、皇甫惟明、王忠嗣全部清洗。
玄宗既留戀權力不想交權,又貪圖享樂倦怠朝政,遂“悉以政事委林甫”。而李林甫欺上瞞下,嫉賢妒能,大量人才尤其是“文學”之士被壓制。
詩人李白在《古風(其十五)》中用“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抨擊君王追求聲色珠寶,聽任賢才零落荒野;《梁甫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把賢才難展抱負的憤懣抒發得淋漓盡致;《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奸臣當道猶如浮雲蔽日,賢良仕進無路,難望長安。
《行路難》前兩首在面對“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世路艱難時,李白尚有“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倔強自信;但到了第三首,已經是完全心生退意,直言虛名無益,“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天寶朝政日趨腐敗,仕路坎坷,李白鬱結之深、憂憤之烈,盡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兩句中,既然“人生在世不稱意”,那麼何妨放下一切,“明朝散發弄扁舟”。
張九齡在《感遇(其四)》中,曾用“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警告李林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李林甫專權多年後,終於迎來了蓄勢待發的楊國忠。元稹《連昌宮詞》有言,“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能進入玄宗視野,來自楊玉環姐妹的推薦。
前朝盤踞李林甫,後宮闖入楊玉環
對於玄宗與玉環的感情,白居易長詩《長恨歌》有深情書寫。楊玉環家境普通,其父親楊玄琰只是七品蜀州司戶參軍,故白居易詩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但其家族和武則天母親楊氏出自同一楊家。因此,“天生麗質難自棄”的她能在開元二十三年(735)嫁給玄宗與武惠妃的愛子李瑁為王妃。
開元晚年,前朝事務由李林甫包攬,無須玄宗操心;但後宮武惠妃病逝後,精神鬆弛的玄宗不免空虛寂寞冷,是為“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開元二十八年(739)十月左右,經由高力士牽線搭橋,楊玉環闖進玄宗生活,“一朝選在君王側”。玄宗將玉環從兒媳變成媳婦,並冊封其為貴妃,掌管後宮,“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宮中“呼為娘子,禮數實同皇后”。
玄宗經常攜楊貴妃赴驪山華清宮泡溫泉,“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華清宮成為盛世大唐最為浪漫的纏綿之處,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其一)》雲:“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但據陳寅恪考證,玄宗貴妃“臨幸溫湯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時節”,無“明皇與貴妃有夏日同在驪山之事實”,故“荔枝來”不一定為真。而華清宮中,最為難堪惆悵的,莫過於失去愛妻的壽王。李商隱的《龍池》言:“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
玄宗和貴妃從華清池回宮後,繼續花樣百出的娛樂,“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有年春日,玄宗貴妃在沉香亭畔觀賞牡丹花開,讓當時在長安供奉翰林的李白寫新詩,是為《清平調詞三首》。
其一: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三: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玄宗曾登臨三鄉驛(今河南省宜陽縣境內),遙望雲霧繚繞的女幾山,感慨人生苦短,欲與貴妃歡樂永遠,遂吸收天竺樂曲《婆羅門曲》音調,譜就《霓裳羽衣曲》。劉禹錫據此作詩道:
“開元天子萬事足,唯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
楊貴妃經常為玄宗跳霓裳羽衣舞,後來“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玄宗貴妃的愛情命運,大唐的興衰榮辱,都與此曲此舞密切相關。李約《過華清宮》有言:“君王遊樂萬機輕,一曲霓裳四海兵。”
玄宗所有寵愛集於貴妃一身,後宮三千佳麗無緣承受雨露,從秀髮宮娥變成白髮宮人。元稹《行宮》有言:“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白居易《上陽白髮人》亦言“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
白居易《長恨歌》詩意圖,清代袁江繪。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視覺中國 供圖
楊國忠亂政,李白杜甫白居易都看到了盛世危局
楊貴妃獨佔宮闈,“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尤以楊國忠為甚。楊國忠本命楊釗,是武則天男寵張易之外甥、楊貴妃從祖兄弟,同時是貴妃二姐虢國夫人的情人。天寶四載(745),楊國忠到長安,透過虢國夫人引線,搭上楊貴妃,被貴妃姐妹引薦給玄宗。
但楊國忠的快速升遷和楊貴妃並無太大關係,他主要因善於理財而被玄宗委以重任。楊國忠躥升的那幾年,正是玄宗在財政問題上思想壓力最大的時期。楊國忠改革財稅徵收辦法,改善漕運物流體系,國庫收入增速空前。天寶八載(749)二月,玄宗在左藏庫看到金銀財寶綾羅綢緞堆積如山,徹底解除了開元以來不斷承受的財政壓力,更加信重楊國忠。天寶十一載(752),楊國忠誣陷李林甫謀反,李林甫一氣之下於當年十一月病死。
玄宗對楊貴妃家族寵幸無比,每年十月赴華清宮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舊唐書·楊貴妃傳》)。天寶十二載(753)上巳節,楊國忠家族集體春遊長安曲江,杜甫作《麗人行》嘲諷道“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天寶晚期,負責劍南軍務的楊國忠為邀邊功,與南詔失和,唐軍屢屢敗北,玄宗“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李白《古風(其三十四)》抨擊道,“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徵”。
楊國忠抓人充軍時,“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資治通鑑》卷216),杜甫《兵車行》雲,“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白居易《新豐折臂翁》亦言,“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雲南戰爭失敗造成的動盪,只是天寶晚期唐朝總體危機的區域性縮影。從武德元年(618)開國,到天寶晚期,唐朝已立國近140年,李白以詩人特有的政治敏感,在《古風(其四十六)》展現出盛世中充斥衰朽的殘酷畫卷。
開篇“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氣魄宏大,囊括唐朝從貞觀之治到開天盛世的赫然國勢;“鬥雞金宮裡,蹴鞠瑤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則從昔日輝煌轉向今日衰朽;“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指出當朝權貴腐朽沒落,將國運斷送;詩人悲憤至極,徒羨“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效仿揚雄閉關寫《太玄》,不問世事。
世事不論詩人問與不問,依然朝著走向深淵發展,而玄宗依然沉浸在開天盛世的餘暉虛幻中。天寶十三載(754)六七月間,玄宗對高力士言道,“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洞曉實情的高力士毫不客氣地反駁,“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資治通鑑》卷217)。
高力士之言,玄宗並非置若罔聞;高力士指出的危局,玄宗亦表示“朕徐思之”。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長期積累,天下已是危如累卵,尤以安祿山尾大不掉為甚。
玄宗一直謎之信任的安祿山,反了
開元時期,胡人安祿山駐防東北,防範奚、契丹,多有戰功,受到玄宗青睞,先後被任命為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手握軍隊達18.35萬人,掌握東北、河北、山西的軍事、財政和人事大權。在“中國(中原)無武備矣”的情況下,出現“祿山精兵,天下莫及”的太阿倒持局面。
其他邊將的民族身份也在悄然改變,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史思明等人是高麗、突厥、突騎施、粟特、契丹等民族出身。後世詩人常據此批評天寶時期胡曲胡舞的流行,元稹《胡旋女》“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白居易《胡旋女》“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
元、白認為,胡風、胡曲、胡舞侵入,導致胡人掌兵,引發安史胡亂。其實主因在於開元天寶長期和平,內地漢人士兵軍事素質下降,漢族將領少了一茬將才,給了胡將從中低階軍官到節度使大將的成長機會。東北地區胡族雜居,安祿山是雜種胡,其父粟特人,其母突厥人,能有效籠絡各個民族的兵士。他利用玄宗賦予的大權,極力擴充套件勢力,掌控軍隊。杜甫《後出塞五首》對此揭露,“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太子李亨和楊國忠屢屢聲言安祿山必反,玄宗卻對他一直謎之信任,擔保其“必無異志”。
安祿山幾次入朝,早已窺破朝廷腐朽無能的真面目。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中的“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即是安祿山探使到長安刺探情報的情景;“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是安祿山對玄宗的逢迎麻痺;而“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便是安祿山準備就緒後的鋌而走險。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初十,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市)以討伐楊國忠為名舉兵造反。太原等地連發警報安祿山造反,玄宗全部不信,直到七天後才確認此賊已反。中原唐軍防守不及,洛陽很快失陷。天寶十五載(756)正月初一,安祿山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李白《古風(其十九)》寫道,“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洛陽陷落,玄宗派在京養病的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到長安門戶潼關建立防線。此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退叛軍對甘肅的進攻,解除長安北部威脅;河北顏真卿舉兵討賊,叛軍後院著火。安祿山考慮放棄洛陽,回軍范陽老巢。
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建議堅守潼關,拖住安祿山主力,然後由郭子儀李光弼從西北向東北直搗范陽,捉住叛軍家屬,再東西夾擊叛軍。可玄宗聽信楊國忠關於叛軍潼關部隊只是老弱殘兵的假情報,強令哥舒翰進攻,致使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初四,潼關失守,哥舒翰被俘。六月十三凌晨,玄宗在禁軍大將陳玄禮護衛下,帶楊貴妃和楊國忠等向四川逃亡。
安祿山佔領長安後,“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杜甫《哀王孫》寫道,“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百姓四處逃竄,杜甫《詠懷二首》寫道,“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雒化為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
馬嵬兵變,此恨綿綿無絕期
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十四中午,玄宗終於走到讓他終生難忘的馬嵬驛。禁軍將士連續趕路又累又餓,把怨恨集中到楊國忠身上。恰巧這時楊國忠被一同出逃的吐蕃使者圍住,騎士張小敬等人大呼“楊國忠與吐蕃同反”,當場把楊國忠父子“梟首,屠割其屍”,接著將玄宗團團圍在驛站中。陳玄禮提出必須誅殺貴妃才能平息事變,玄宗遲遲不做決斷,在高力士的反覆勸說下最終無奈同意。
楊貴妃在佛堂上完最後一炷香後,讓高力士用三尺白綾勒死自己。劉禹錫《馬嵬行》透過目擊證人的口吻,描摹了當時的情景,“軍家誅戚族,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迴轉美目,風日為無暉”。
馬嵬兵變,最冤莫過楊貴妃,她陪伴玄宗十七八個春秋,從來沒有插手朝政,始終把陪伴玄宗作為唯一的樂趣,最終以38歲的無辜生命換取了玄宗的平安,用紅顏禍國的罵名為玄宗承擔了安史之亂的責任。
與貴妃以死報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量朝臣叛降。玄宗逃跑前後,駙馬、張說次子張垍,張說長子張均,宰相陳希烈,河南尹達奚珣等先後投降安祿山,接受偽職,徐夤《馬嵬》詩言:“二百年來事遠聞,從龍誰解盡如雲。張均兄弟皆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
很多詩人對楊貴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李商隱《馬嵬二首》言,“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諷刺玄宗貴為天子,卻連貴妃性命都無法保護,還不如民間莫愁女可以夫妻白頭偕老;於濆《馬嵬驛》亦言,“當時嫁匹夫,不妨得頭白”。
長安收復後,玄宗回京再赴華清宮,溫泉依舊,貴妃不在。羅鄴《駕蜀回》言:“上皇西幸卻歸秦,花木依然滿禁春。唯有貴妃歌舞地,月明空殿鎖香塵。”華清宮的半磚片瓦都會勾起玄宗內心無限傷痛,為排遣痛苦,他把貴妃閨蜜、舞女謝阿蠻請到華清宮。謝阿蠻為玄宗跳了一支《凌波曲》,然後拿出手環告訴玄宗,“此貴妃所賜”。玄宗睹物思人,老淚縱橫,又讓梨園子弟張野狐吹奏《雨霖鈴》。這是玄宗當年在蜀道斜谷路上“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觸景生情譜的曲子,寄託對貴妃的哀思,是為“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張野狐吹《雨霖鈴》剛吹一半,玄宗“四顧淒涼,不覺流涕”,身邊宮女宦官也跟著落淚。張祜有詩《雨霖鈴》曰:“雨霖鈴夜卻歸秦,猶見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玄宗對貴妃的懷念,不僅是對愛情的留戀,更多是對一個時代的不捨。當年太平盛世,能夠與他同歡同樂的,是貴妃的似水柔情。大亂來臨,讓他失去江山的馬嵬兵變,也和貴妃的香消玉殞聯絡在一起。玄宗想起一去不返的盛世開天,自然會想起貴妃,把一腔哀怨都寄託在她的身上。
寶應元年(762)四月初五,玄宗去世,終年78歲,若貴妃還在,這年應是43歲。曾經許下“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誓言的玄宗貴妃,現在終於可以放下一切,去成就“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相守。
當年在馬嵬驛,玄宗失去的不僅是貴妃,還有對太子的控制。馬嵬兵變第二天,太子與玄宗分道揚鑣,兵變最終演變成政變。這之後的局勢,已非玄宗所能控制。而大唐也由此透過重建平叛指揮中心,開啟艱難的平叛程序,最終實現中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