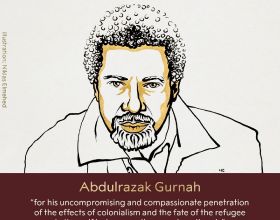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訊 10月7日晚,瑞典學院宣佈,將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坦尚尼亞作家阿卜杜拉扎克·古爾納,其頒獎詞為“毫不妥協並充滿同理心地深入探索著殖民主義的影響,關切著那些夾雜在文化和地緣裂隙間難民的命運”。
古爾納1948年出生於坦尚尼亞的桑給巴爾島,現年73歲。1960年代末,阿卜杜拉扎克·古爾納以難民身份抵達英國,此後定居英國,以英語開始寫作。古爾納的作品暫無中文譯本,不過70後代表作家陳家橋在雜誌上看過這位作家的一個短篇,而他8日下午也從文學寫作的立場分析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邏輯。
古爾納的背景和創作特殊且豐富
對於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坦尚尼亞的小說家,在意外之餘,陳家橋表示這也展現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魅力,“古爾納這次獲獎,我覺得還是非常有意味的。”
只是在《譯林》上讀過古爾納的一個短篇,陳家橋認為,透過一篇小說是不能夠概括一個作家的,“但他能夠獲獎,包括授獎詞,也包括媒體的反映,即便是很有限的反應,我覺得他的獲獎還是恰當的。”
“他的那篇短篇小說《囚籠》,我覺得非常的故事,也非常寫實。包括我看到他寫的最著名的小說《天堂》的介紹,還有一個《海邊》的小說,反映了諾貝爾文學獎幾個新的動態。”陳家橋表示,在後現代這個語境裡面,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新批評主義、女性主義、女權主義,還有移民、流亡、離散幾個大的概念和主題,“實際上古爾納的作品成為這個文學景觀裡面最新的符合潮流的東西。”
具體到古爾納身上,陳家橋認為,非洲和英國這個老牌的殖民主義國家,英語國家、英語文學、英語文化和非洲的基因碰撞,成為作家文字構造的動力和動因,促成了文學的特殊性,“比如奈保爾的作品有加勒比地區、印度文化的基因。我瞭解到古爾納的這個小說,除了有非洲的基因以外,還有穆斯林文化的交融,它裡面有民族的,有文化的,有後現代的,有大陸板塊之間的文化衝突和融合,有多重身份在裡面,所以這個足見他有足夠的豐富性。”
庫切獲獎是標誌性的 古爾納獲獎是延續
陳家橋認為,古爾納的獲獎表達了世界文學的這種新動向,實際反映的就是對這種流散、離散的這樣一種寫作,“就是反映人和他的文化之間,和他的生活環境之間,產生了一種漂移的、離散的、放射性的這樣一種關係。它是有深層文化背景,是一個身份認同出現了危機的情況下的一種寫作。”
陳家橋以英國文壇移民三傑和古爾納為例,指出世界文學的這種新動向,“這幾年獲獎的作家就可以反映這一點。在英國有移民三傑,剛好坦尚尼亞這個小說家古爾納,他也是在英國的移民作家。‘移民三傑’石黑一雄、奈保爾和拉什迪三個是最有名的,其中石黑一雄和奈保爾已經獲過獎,拉什迪一直呼聲很高,但是古爾納並不是特別有名,為什麼他是那個獲獎的,我覺得這裡面還是有一個特殊性,因為他身上有非洲的這個背景。”
非洲獲獎的作家包括南非的庫切,在陳家橋看來,庫切在2003年獲獎是個標誌性的事情,“庫切是一個住在開普敦的白人,他移民到西方社會,後面回到開普敦,他身上這種移民性所體現的這種流散也好,離散也好,這種主題是非常明確的。他的生活和他的文化背景之間所產生的這種撕裂,然後試圖去彌合,構成這種奇異性的新的一種文學圖景。”陳家橋認為,庫切、奈保爾和古爾納的獲獎,有非常值得關注的一脈相承的地方。
【作家陳家橋】
談麥克尤恩和阿多尼斯為啥不獲獎
村上春樹、麥克尤恩和多位中國作家多年來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前總會成為熱門人物,陳家橋對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像麥克尤恩的寫作,實際上也寫得足夠好,包括改編成電影的《贖罪》,包括《無辜者》、《星期六》和《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啊,在中國有很大的受眾,為什麼老是不能獲獎,因為畢竟他就是英國的作家,他就是英語寫作中的翹楚,獲過很多國際大獎,但他就是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覺得這個反映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就想坐在中心看邊緣,我覺得這個是一直是諾貝爾獎的一個特點,我覺得它恰恰也反映了在世界文學的整個批評體系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動向,就是說它不僅站在中心,確立中心話語,它實際上是要站在中心來為全世界發言。”
“所以我覺得,頒給古爾納那種作家,我覺得比頒給麥克尤恩,對世界文學的走向也好,對新的批評環境的整合也好,對鼓勵世界文學的多元化和文化相對主義也好,對新批評格局的觸動和促進也好,我覺得還是有好處的。至於麥克尤恩,他寫得足夠好,但恰恰就是應該,怎麼說呢,就是把一些主流的中心的作家晾在一邊,讓這些邊緣的作家能夠獲獎,這恰恰是一個批評,應該做的。”
至於諾貝爾獎肯定美國詩人格里克,而沒有給阿多尼斯這樣呼聲很高的詩人,“這恰恰就是複雜的批評環境的一個反轉。它既有從中心往外看的這個視角,同時也有對中心裡面的一個一個純粹的語言追求,或者說是詩性寫作的肯定,包括給鮑勃·迪倫,都是這樣的。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諾貝爾文學獎瘋了,比如說給鮑勃·迪倫,比如說像以前給過那個搞哲學的柏格森,包括給英國首相丘吉爾,都是和文學關係不太大的人,但恰恰也反映了文學的這種多樣性,也反映了它試圖從文學涵蓋到歷史、哲學、音樂的野心,文學本身有這樣的一個野心,有這樣的一個趣味上的擴散。”
再為米蘭·昆德拉遺憾一下
“雖然古爾納目前讓中國讀者有印象的就是一個《囚籠》,還有就是媒體上有關於《天堂》等等他的最著名的小說的一些簡介,我還是覺得他獲獎是當之無愧的。剛才說的後現代語境下的各種圖景,包括女性主義,你看這些年給了多少女性作家諾貝爾文學獎,耶利內克、赫塔·米勒、阿列克謝耶維奇……特別是多麗絲·萊辛,多麗絲·萊辛是有非洲生活背景的這麼一個女作家,她《金色筆記》寫得特別好。我覺得諾貝爾獎從來不會不恰當的,頒獎就是恰當的,每一次是頒給誰,這種風向標,預示著整個人類社會在文學這一塊的一個新的動向。
“我覺得我還要強調一點啊,我覺得米蘭·昆德拉沒有獲獎還是有點遺憾。實際上米蘭·昆德拉是個流亡作家,流亡作家就是有很多複雜的原因,不僅是文化的原因,寫作上政治性掛的可能更多,但是諾貝爾獎有一點,我覺得始終是和政治是保持著相對獨立和清醒的關係,無論是政治上過於熱情,還是說在政治上相對來講比較激進,我覺得都不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選項。諾貝爾文學獎對文學的這種處理,是更關注於文學背後的文化差異,文化的新的動向和文化對社會的整合,諾貝爾文學獎正是在這一點上,進一步確立了新的權威。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記者 蔣楠楠
編輯 王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