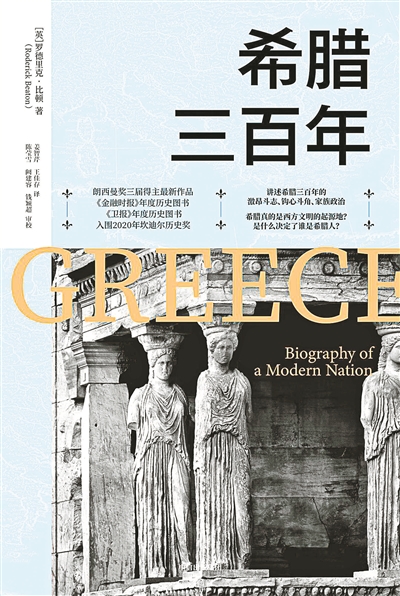每四年一次的奧運會,都會提醒世人把目光投向它的發源地——希臘。雖然現代希臘在近一百多年的現代奧運會上戰績欠佳,但為了尊重它,希臘運動員在每屆奧運會上都率先入場,每次奧運聖火採集也都在其著名的奧林匹亞遺址舉行。有些人或許還知道,聖火乃至現代奧運會本身其實都是“傳統的發明”,直到近代才在“復興”的名義下推出的創新,但鮮為人知的是,其實現代希臘國家本身也是如此。
“我們都是希臘人”
1821年希臘獨立戰爭爆發時,希臘國家已消亡了2000年之久。然而,希臘屬於極少數這樣的國家:世人對其古代史的興趣遠大於現代面貌——另一個也許是埃及,但埃及畢竟屬於中東的文化圈,不像希臘這樣能激起西歐社會的強烈興趣。經歷了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的現代西歐人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奠定“歐洲”或“西方”文化根基的,正是古希臘人,然而在現實中,當時的希臘卻處於土耳其人的“野蠻統治”之下,甚至乍看起來已經與古希臘沒什麼瓜葛了。
這種歷史記憶的甦醒,最終被證明蘊藏著極大的力量。就像晚清時南明記憶的復活,讓許多革命志士奮起排滿,當時的希臘人也在祖先的形象中赫然看到自身處境之不堪。原本對他們來說,那些異教的祖先因為不曾得到基督的恩典,正是需要被遺忘的過去;然而大致從1800年開始,隨著啟蒙思想的傳佈,一種全新的世俗主義開始興起,希臘人逐漸強化了自己與逝去古代文明之間的親緣關係,尤其重要的是自居為古希臘的直系後裔。
乍看起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實際上卻是全新的政治實踐,只不過“創新”是包裹在“復興”和“恢復”的重重面紗之下。對原本傳統已經斷裂的人們來說,要重新接續上,首先就意味著選擇:如果說“現代希臘國家”這個嬰兒的分娩需要“古希臘”這個母親,那麼是哪個古希臘?因為希臘出名的祖先不止一個,除了城邦文明的“古希臘”,還有中世紀的拜占庭文明。在選定了前者之後,仍然有問題:怎樣才能重建這種連續的親近感?這就好比讓現代中國人重新都穿上漢服一樣,在現實中“恢復”意味著要改變現有的種種做法,而接受一種新創的傳統。
但僅僅如此還不足以讓希臘獲得獨立,在現代希臘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希臘對西方文明來說太重要,因而希臘事務從來不僅僅是希臘人自己的事。在對歷史的回望中,古希臘普遍被視為西方文明的根基,因而“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尤其是其他歐洲國家,欠下了希臘巨大的文化債務”這一觀念,不僅是深深植根於西方人心目中,甚至也進入了希臘集體意識之中。這不僅導致人們將古代希臘理想化,也使得現代希臘獨立運動在一開始就得到了西歐各國公眾的極大關注和自發支援——英國詩人雪萊用一句“我們都是希臘人”喊出了所有人的心聲。
誰是希臘人?
雖然這最終為希臘帶來了艱難的獨立,但卻也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種種問題。對現代希臘國家來說,古希臘不僅是自己獨佔的“名牌”和資源,也是合法性的來源。正如《希臘的現代程序》一書中早已指出的:“古代希臘之所以成為新國家的建立神話的主要部分,是因為啟蒙後的歐洲暗含著的標準就是:古代希臘在認定新國家正統地位時起決定性作用。”
這勢必就要忽視很多歷史的斷裂,而刻意強調連續性,有時造成一些極具諷刺性意味的現象,尤其是“民主”雖公認是古希臘人的發明,但現代希臘的代議制民主,其實卻是從西方引入的。新國家給人的印象,彷彿從古希臘的輝煌之後,中間就一筆帶過,無縫對接到了現代希臘,因此和現代國家對公民的定義不同,新國家“享有主權的人”被命名為“希臘人”以及“希臘人的後裔”。然而在現實中,這個國家的人口卻並不是統一的血脈傳承下來的群體,而有著混雜的語言群體和宗教社群(特別是穆斯林和猶太人),那麼問題來了:“誰是希臘人?”
如何彌合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自此一直纏繞著現代希臘社會。這不僅導向清除那些“雜質”的異文化群體的行動、摧毀近古的居民建築來儘可能地“恢復”古希臘遺址的景觀,而且在內部也引發了經久不衰的紛爭:一些人念念不忘獨立革命中那種絕對自由的滋味,主張迴歸傳統;另一些人則試圖在務實和融合的基礎上推進現代化建設。現實是:雖然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現代希臘呱呱墜地,並宣稱是古希臘的後裔,但它在成長過程中卻勢必會形成屬於自己的獨特個性。
不堪重負的“使命”
正如本書所言,直至20世紀末,希臘歷史學家幾乎都一廂情願地認為,他們的國家是一個特例,特別古老,與任何國家都不一樣。這在賦予它特殊認同的同時,也給它帶來相當棘手的問題和特殊的現代化道路:它要變成一個西化的現代國家,但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卻是回到過去,“要由古人領導現代的人奔向現代化”,換言之,“通往未來的道路看起來是要復興一個已經消失的過去”。就像它的首都雅典,不僅要變成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城市,而且還是在“再現早已喪失的古代榮耀”這一名義之下推進。
然而,無論現代希臘如何努力,它都絕無可能達到古希臘在世界格局中曾佔據的那種地位。1844年,希臘政治家科萊特斯在向議會發言時,曾闡述祖國所應有的世界地位:“從地理位置上看,希臘是歐洲的中心,東方在它的右邊,西方在它的左邊。透過衰落和覆亡,希臘註定啟蒙了西方;但是,希臘要透過再生,來為東方啟蒙。這兩個使命中的第一個,是我們的祖先完成的;第二個使命,要由我們來完成。”
最終,現實證明,希臘的“偉大理想”一廂情願給自己賦予的使命是不堪重負的,有時蛻變成對外的擴張主義,既沒有充分考慮到鄰國的感受,也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反彈。由此帶來的震盪使希臘政壇陷入分裂,不同派別的人對於如何看待希臘人的使命,在一百多年裡都無法彌合分歧:一些人相信最重要的是解放所有希臘人,另一方則認為保護希臘這個政權國家才是最重要的。這種紛爭,直到冷戰後期才隨著希臘政治的成熟逐漸平息。
在這過程中,希臘與西方的關係也在不斷變化:起初,它其實一直是“東方”的一部分,但近代又被視為西方文明的根本,自認每個西方人都對希臘欠下了恩情,這種矛盾的若即若離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它才終於越來越積極地融入歐洲一體化,生活方式開始變得更像西方了。弔詭的一點是,儘管對希臘人來說,生活變得更舒適了,但它在西方遊客眼裡的魅力卻下降了,因為它變得太“歐洲化”了。希臘的這種“普通國家化”意味著它終於逐漸變得和其他國家無異了:在後冷戰時代,它的外交政策也越來越多建立在成熟國家的自我利益之上,而不再是跨邊界的共同文化傳統之上了。
在近三百年的時間裡,“傳統”既是孕育現代希臘國家的母體,又是它的重負,但無論如何,時至今日都仍是它最重要的資源。當然,現代人仍會不斷選擇哪些“傳統”才值得保留和強調,就像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開幕式上,在重現極具衝擊力的古希臘輝煌的同時,也把此後被羅馬和奧斯曼帝國征服的歷史完全摒棄了。在這裡,“傳統”實際上服務於當下的需要,是“古為今用”;反過來說,它也正因此而被現代人不斷加以重新詮釋,開創新的局面,並由此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