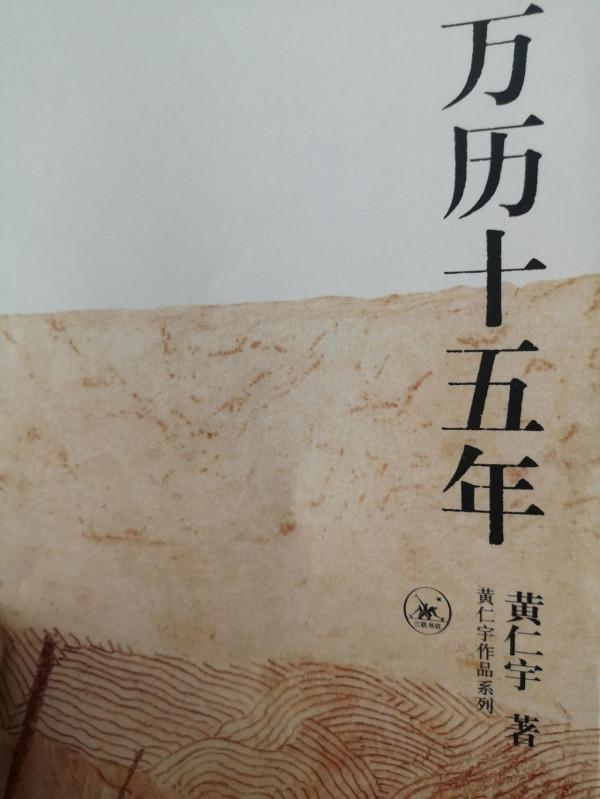【晨語~萬曆:權力的無奈】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長達28年不上早朝。自從1585年以後,萬曆除了僅僅於1588年對自己的定陵再度視察過一次以外,三十多年,他沒有走出過紫禁城一步,創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紀錄!
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擢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摺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惰。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麼趣味?
萬曆皇帝缺乏他叔祖(正德皇帝)的勇氣、積極性和尋找快樂的情趣。他從小開始就沒有一天體會到自由的意義,也不是憑藉自己的能力而獲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難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確的主張了。他讀過有關他叔祖的記錄,深知文臣集團只要意見一致,就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堅強的毅力,這個孤立無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個胸襟開闊足以容物、並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損傷,他就設法報復。報復的目的不是在於恢復皇帝的權威而純系發洩。發洩的物件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無辜的第三者。積多年之經驗,他發現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極抵抗,即老子所謂的“無為”。
由於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皇帝沒有能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了活著的祖宗。張居正不讓他習字,申時行不讓他練兵,那麼他貴為天子並且在年輕時取得了祖宗的身分,對事實又有什麼補益?
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象,由於大量這種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後被稱為神宗顯皇帝,而幾百年之後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是命運的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