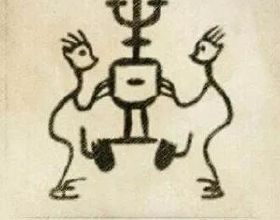看到王文娟過世的訊息,忍不住想起了孫道臨先生,想起今年是孫道臨先生誕辰一百週年,也想起我和孫道臨先生一段交往的往事。
在北京的北長街西側,有前宅衚衕和後宅衚衕。這是清朝才有的兩條衚衕,本來是一處官宦人家的大宅門,前宅後宅各開了一扇大門,門前人來人往,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有了路,漸漸形成了兩條衚衕。前宅衚衕在南,後宅衚衕在北,東臨故宮,西鄰中南海,北鄰北海,都近在咫尺,真正屬於皇城眼皮子底下,從古至今都非常幽靜,與一些喧囂的網紅衚衕和雜亂的破舊衚衕,不可同日而語。相比較而言,前宅衚衕短些,卻也寬些,且院落多軒豁典雅,多名人居住,比如當時的法學家何基鴻。
三十一年前,1990年夏天,如果不是孫道臨先生約我到那裡見面,見寡識陋的我,根本不知道京城裡還有這樣一條短小精悍典雅別緻的衚衕。如果不是由於有了孫道臨先生,衚衕再如何典雅別緻,和我關聯不大。有了孫道臨先生,這條衚衕便於我有了難忘的回憶,回憶中的一切,才有生氣和生命,如同陽光透過衚衕中的老梨樹枝葉灑下的光斑閃爍,始終跳躍在三十一年夏天的那個中午時分。
我去的時候,一眼看見,孫道臨先生已經早在前宅衚衕東口,即北長街那兒等候著我了。記憶是那樣的清晰,一切恍如昨天:他穿著一條短褲,遠遠地就向我招著手,好像我們早就認識。我的心裡打起一個熱浪頭。
要說我也見過一些大小藝術家,但像他這樣的藝術家,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的儒雅和平易,也許很多人可以做到,但他的真誠,一直到老的那種通體透明的真誠,卻並非是所有人能夠達到的境界。
前宅衚衕裡,有上海駐京辦事處,他來北京住在那裡。中午,他請我在上海辦事處的餐廳吃午飯,那裡是正宗的上海本幫菜,口味純正。除了吃飯,我們談的是一個話題,那就是母親。他說他在年初的一個晚上看新的一期《文匯月刊》,那上面有我寫的《母親》,他看了一夜,感動地流出了眼淚,當時就萌生了一定要把它拍成一部電影(其實那只是一篇兩萬多字的散文),經過了半年多的努力,他終於說服了上海電影製片廠,決定投拍,讓我來完成劇本的改編工作。他這次來北京,主要就是來找我商談此事,居然那樣的信任,沒有什麼交談,更沒有見過面,就把編劇的活兒交給了我。
他對我說,讀完我的《母親》,他想起自己小時候在北京西什庫皇城根度過的童年,想起自己的母親。他也想起了在那些艱苦和殘酷的歲月裡,他所感受到的如母親一樣普通人給予他的難忘的真情。
那天,他主要是聽我講述了我的母親的故事,和我對母親無可挽回的閃失和愧疚。他就那樣靜靜地聽著,不打斷我,竟然聽著聽著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淚。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七十歲人的眼睛居然沒有渾濁,還是那樣清澈,清澈得淚花如露珠一般澄清透明。
忽然,他驀地站了起來,有些激動地對我說:我為什麼非要拍這部電影?我不只是想拍拍母愛,而是要還一筆人情債,要讓現在的人們感到真情對於這個世界是多麼的重要!
我們一老一少淚眼婆娑相對,映著北京八月的陽光的時候,我感受到藝術家的一顆良心,在物慾橫流中難得的真情,和對這個喧囂塵世的詰問。那天回家,對著母親的遺像,我悄悄地對母親說:一個北大哲學系畢業、蜚聲海外的藝術家,拍攝一個沒有文化平凡一生的母親,並不是每一個母親都能夠享受得到的。媽媽,您的在天之靈可以得到莫大的安慰了。
1995年2月,我新出了兩本書寄他,裡面有那篇《母親》。他寫信對我說:“再次讀了你寫的關於《母親》的文章,仍然止不住流淚。也許是年紀大了些,反而‘脆弱’了吧。總記得十七八歲時是要理智得多,竟不知哪個時候的自己是好些的。”
2007年12月,孫道臨先生逝世。偶去北海,再走北長街,路過前宅衚衕東口,忽然覺得孫道臨先生正站在那裡,遠遠地向我招著手。(肖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