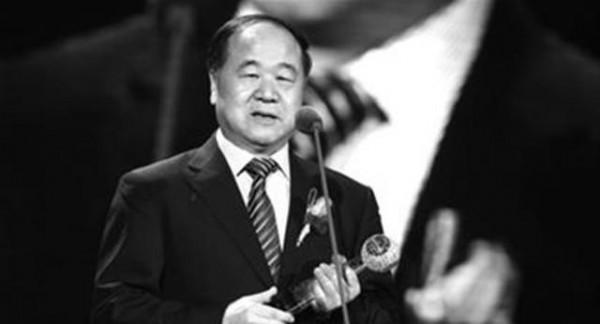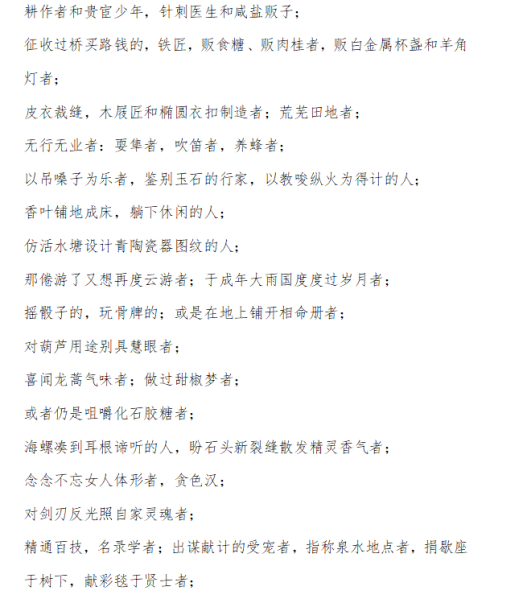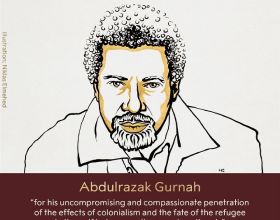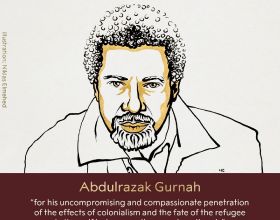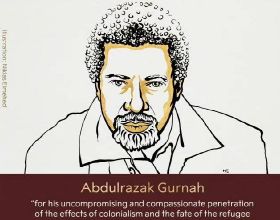距莫言榮膺諾貝爾文學獎已九載有餘。
雖說國內很多作家對諾獎的評判標準不置可否,然而不得不承認,多數國人對這項歷史悠久,飽負盛名的獎項情感還是相當複雜的。
從魯迅謝絕瑞典人邀約到老舍自殺無緣參評,從沈從文殺入決選遺憾落選到北島三次入圍最終惜敗一籌...
即使是12年莫言拔得頭籌,但作為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三千年詩文傳承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文學界的這點認可是遠不能讓我們國人滿意的。
再這說來,莫言的獲獎也不無尷尬之處:從寫作手法上來看,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昭然若揭,深受外國作家影響。
在頒獎詞中,瑞典學院更是直接闡明瞭莫言作品與福克納、馬爾克斯之間的淵源,“中國古老文學與口頭傳統”的話術云云反倒更像是安慰之詞。
因此,對於中國文學本身來說,這塊獎牌的純度並不算高,中西方的觀念芥蒂,語言藝術中的翻譯隔閡仍舊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然而縱觀歷史,從百年諾獎歷史來看,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碰撞遠不止莫言這一次。
中國文學與諾獎的初遇發生在1938年。
美籍作家賽珍珠憑藉1931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大地》摘得諾獎桂冠。
賽珍珠雖出生於美國弗吉尼亞,但在她年僅4個月大的時候,她的傳教士父母就將她帶到了中國大陸。
自此,賽珍珠開啟了自己長達40年的中國人生。
她親切的將鎮江稱為“中國故鄉”,而漢語作為她最早學會的語言也順理成章的稱為她的母語之一。
賽珍珠一生出版著作80餘種,其間包括小說,傳記,兒童文學,政論等等,中國大地上的民生是她的主要作品母題,除此之外,她還曾將《水滸傳》翻譯成英文,為中國傳統文學走向世界舞臺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諾貝爾委員會在頒獎給《大地》時解釋道:“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描述,描述真切,取材豐富。”
由此可見,賽珍珠雖長了一副白人皮囊,但其作品中的中國元素,無論是故事人物還是思想感情,甚至她的三觀處世都是佔據主導地位的。
中國文學第二次得到諾獎青睞是在1960年。
這次故事的主角依舊不是黑頭髮黃面板,而是法國詩人聖—瓊·佩斯。
聖—瓊·佩斯出生於法屬西印度群島,官路亨通而聰敏的他在政壇如魚得水,很快就進入了法國外交部。
1916年,聖—瓊·佩斯來到中國使領館工作並先後擔任北京使館秘書和上海領事館領事。
在華期間,聖—瓊·佩斯步履不停,遊歷完東北後又深入西北,穿越沙漠,並創作出長達10章有餘的長詩《阿納巴斯》。
正是這首歌頌人類無盡創造力與探索精神的長詩,使得聖—瓊·佩斯於1960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當然,我們不會只因為聖—瓊·佩斯來過中國就荒唐的把他納入中國詩人之列。
之所以將其詩集歸為中國的文學,故事還要從北京海淀西北郊區一個叫管家嶺的小山村說起。
在這裡,聖—瓊·佩斯寫信給自己的母親傾訴了一個村落的消亡。
在這裡聖—瓊·佩斯告訴自己的朋友貝熙業醫生(法國白求恩):“在我的腳下,代替整個人類的是一個低矮的山谷,一條被流沙淤塞的河道,是指向西方的蒙古和新疆的遼闊土地。”
而這裡,是當年居民稱之為“外國地兒”,也是聖—瓊·佩斯居住寫作的地方。
不得不提的是,這方水土不僅為聖—瓊·佩斯提供了居住,構思,寫作的物理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聖—瓊·佩斯還源源不斷的從這方土壤中汲取養分,吸收元素,這使他作品的內容與藝術也深深紮根於此。
這也使得他的作品彷彿一張活靈活現的北方京城鄉村風俗畫卷!
距離莫言最近的一次諾獎邂逅想必大家都早已耳聞。
故事的主角是法籍華人作家—高行健。
高行健出生於江西贛州,1987年前往德國從事繪畫創作,次年轉往法國巴黎居住。
從我本人主觀上來評判,高行健是個很有才情的作家,但他獲得諾獎是有一定政治因素摻雜其中的,這裡由於一些敏感因素我不多做贅述。
對於高行健,諾獎的評價是:“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高行健的《靈山》讀起來還是有一些隔膜感的,反倒是那位法國詩人聖—瓊·佩斯能讓人讀完倍感親切。
或許是因為,聖—瓊·佩斯才是真真切切的寫出了中國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