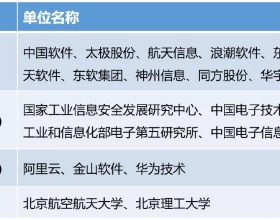章太炎(1869—1936年),字枚叔,後易名炳麟,號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醫學等等,著述頗豐,代表作主要有《儒術新論》《國故論衡》《齊物論釋》等。他的思想經歷和學術著述中飽含著許多具有啟發意義的治學理念、治學品格和治學方法。
以歷史引起愛國心
在治學理念上章太炎主張以歷史引起愛國心,他強調,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引起愛國心,非歷史不可”,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不斷繁衍發展,就在於其是一個具有歷史意識的民族,就在於其能夠在自身所擁有的數千年豐富的生產、交往與組織經驗中始終保持自身的獨特性質,這決定了其在存亡危機時刻能夠成為具有強烈的自我覺醒意識的民族,而對中華民族流動與變遷過程的記錄,也正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書寫傳統。他指出,治學雖有取捨,但卻以儲存民族特性最為重要,而要儲存民族特性、發揚愛國志趣,就必須要儲存自身的歷史,學習自身的歷史。
堅持“以史切要”。章太炎十分重視在史論結合的雙重維度上闡發歷史研究的內在思想主旨和以史切要的政治主題。就史學而言,他基於實證性和批判性的筆法探求歷史背後的事理,從而創立了以史解經的“新史學”;就史論而言,他以反思性評述對社會行為所作出的歷史性闡釋,蘊含著構建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歷史連續性敘事的深刻立意,呈現出來的是有關民族特性的精神表達。他反覆強調歷史作為切要之學具有重要意義,是維繫民族特性的核心要素。這一愛國之思,始終貫穿於其史學和史論的互應之間,貫徹至其整個學術生涯之中。
倡導“以史救文”。章太炎重提“六經皆史”,他所提的“史”是“史學”而非“史料”。他認為今文經學的根本危機在於“史”的系統地失信,對“文”的危機的拯救可以透過否定抽象化的“文”和絕對化的“信”,將經統一於史中來實現。這一“以史救文”的道路,不僅為傳統經學研究重新注入了新的生機活力,而且在“中國文化應往何處去”的重要關口,為中國的學術和文化轉型提供了一個新的重要思路。
以百姓心為心
在治學品格上章太炎主張“以百姓心為心”。他說:“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這一真俗兩行之路,始終貫穿著他對“真諦”與“俗諦”、“真情”與“俗情”相互貫通與融合的思考。在這一思考中,他不斷向著“俗諦”和“俗情”傾斜,並且提出了真俗本來不二的觀點,這不僅使他的治學之路具有了一種曲徑獨行的別樣色彩,而且也使他的治學思想具有一種心懷百姓、愛國憂民的內在品格。
章太炎一生都在致力於追求“合致用與求是二者冶於一爐”的治學目標。在1932年發表的《論今日切要之學》中,章太炎疾呼:“合致用與求是二者冶於一爐,才是今日切要之學。”他主張“學在求是”“用在親民”,因致力於“求真之是”所以更加深刻地領悟“用在親民”,因致力於“用在親民”所以更加努力“求真之是”,這成為章太炎治學品格的集中體現。他強調“大獨必群,不群非獨”,因為他真正領會到了“群”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謀取一己之私利,而是為了維繫一個大的共同體,讓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安頓;真正領會到了只有從“小群”中毅然獨立出來,才能投入到拯救“大群”的事業中去,才使得“大獨”具有了極強的實踐品格,這一實踐的最終目的則是為了造福於“大群”,以在肩負起救國圖存重任的同時,使廣大平民的利益免遭侵犯。
追求實事求是之學
章太炎在治學方法上主張語必徵實、說必盡理,反對“臆造新解”。文史學家龐俊在《章先生學術述略》中曾指出:“綜其治學方法,則有六事:一曰審名實,二曰重左證,三曰戒妄牽,四曰守凡例,五曰斷情感,六曰汰華辭。其謹嚴如此,是之謂實事求是之學。”章太炎在《自述學術次第》中對乾嘉之學的衰微感嘆道:“斯四術者,所包閎遠,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實事求是之學,不能以空言淆亂者。”從文中來看,他所提到的“四術”皆為傳統意義上的經學,從他對宏觀經學的界定“六經皆史”而言,這一方法的適用範圍明顯可以擴大到他的整個治學過程。
怎樣做到實事求是?關於這一點,章太炎雖然沒有專門作出闡釋,但卻將其內涵表述為“稽古之道,略如寫真,修短黑白,期於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則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也就是在研究中應該達到對“是”等於“實事”的客觀考證。具體而言,主要包括“疑其難證”和“忠恕”之法。“疑其難證”指在沒有足夠的以文字可考的史料為證據的基礎上“疑古”。“忠恕”之法指以物為物,以己推人,“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周以察物,舉其徵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舉一隅而以三隅反,恕之事也”,“忠恕”之法是實現“實事”與“是”相等同的關鍵。章太炎在具體的史學研究過程中對上述方法實踐運用,不僅將六經還原為了古史,而且還引入了邏輯的方法,使其超出了傳統經學的研究範圍,從而實現了史學研究中歷史與邏輯的相互統一。他在面對不同的時代任務時對這一治學方法又各有側重,將二者之間的學術旨趣具體地呈現於不同的現實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