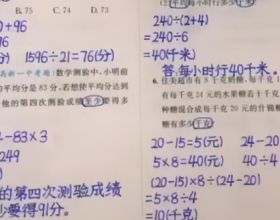春詞~元稹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蔭藏。
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崔鶯鶯和張生的故事是從戲臺上看到的,印象深刻的是戲裡那個小紅娘,活潑靈動,唱腔婉轉動聽。小時候對於戲曲裡的小生唱腔最為反感,掐聲掐調的,難聽,因為這個原因吧,對於張生沒啥好印象!
包括現實生活中的張生。
住在一個村子裡的鄉親,多多少少都有些親戚關係。這個張生是跟我家拐著八個彎的表叔,就像二舅姥姥的表妹的大姐夫家的外甥……就是那種能串起表親加姻親加本家的關係,也許八竿子都打不著。
張生是村子裡的另類,傳奇另類。
記得有個文章裡說過,在中國農村,每個村子都一個或者幾個傻子,瘋瘋癲癲的活動在村口,不請自來的流動在村子裡的紅白事兒場合,幹一些沒人願意幹的活兒,好像一個地方的保護神,稱作“守村人”,只要有他們在,村子就不會消失。
可張生不是傻子,是個瘋子。他也不會出現在人多的地方,更別提紅白喜事的場合了,他好像是生活在平行世界中,與現實格格不入。
張生可以說是村子裡不多的高學歷者之一,七八十年代,高中生都少的可憐,更別提大學生了,張生是農業大學畢業生。
老人們說,他是上學上傻了,書呆子,甚至有一段時間裡,成為了部分家長拿來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上那麼多學幹啥?跟張生似的,上大學有啥用?農業大學!不還是個農民啊!到頭來成個書呆子,不中用的瘋子。還不如早早出來下地幹活掙錢尼!”
我們小孩子都躲著他,他也躲著人群,說實話,張生不像個農村人,真像個秀才,長的可像戲臺上的張生了,白淨的臉龐,身材很好,略瘦,每天都是微笑著嘴角,眼神迷離,不會直視別人,快步走著固定的路線,早上從家走到村西國營單位磚窯,傍晚再從磚窯回來。
他有父母哥嫂,但是不一起住,也不一起吃飯,特別是水,他自己的小破屋子裡有一個大瓦罐,裝的是雨水,如果沒有了,他會去村裡大河坑裡打水,即便那河坑裡的水渾濁不堪,甚至有垃圾。吃的東西是家裡人給送,他當下不吃,總是隔天才吃,也不怕壞了餿了。但是他很乾淨,衣服、臉蛋、手都洗的白淨。
有壞小子耍廢,把張生裝水的大瓦罐打碎了,他也不惱,還是抿著嘴角,收拾好了碎片,過不了幾天,就從磚窯那軲轆回來一個新瓦罐,原因是他以前在磚窯做過會計。
我一直納悶,好好的一個大學生怎麼會變成這樣?直到多年後的一個仲夏日,生叔叔的瘋魔緣由才浮出水面。記得那是生叔叔30多歲光景的時候吧,他家突然來了一個女人,穿衣打扮一看就不是我們村子裡的人,像是出嫁在外面大城市,衣著鮮亮回家省親的年輕姑奶奶。張生的父母跳著腳罵她狐狸精,害人精!張生的嫂子用豬圈漚糞的爛麥秸扔她一身,女人不還手也不回言。
小時候村子裡會經常有吵架的現場直播,那時候沒有電視、手機此等高科技娛樂產品,看打架的,如同看彩色武打懸疑故事片,是人人必到的。
圍觀的人很多,七大姑八大姨們指手畫腳的幫腔兒,用最惡毒的語言譴責著女人。片刻後,生叔叔張嘴說了一句,讓她走!聲音不太大,但是是普通話,和我們的土話的腔調很不一樣,當時覺得真好聽!從來沒有聽見過生叔叔說話的我都驚呆了!
女人滿臉淚痕的凝視著生叔叔,人們停止了戰鬥,女人放下帶來的東西,怯怯的離開了。
張生的老母親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大盤四座的癱在地上,一邊數落著,一邊搶天哭地的嚎了一大番兒,事情便過去了。
經過這場插曲,這個村裡人都知道的秘密,我第一次清晰的捋順了出來。
生叔叔的奶奶喜歡“西廂記”,生了第二孫子以後,看著長得秀才似的白淨臉龐,便起了這個小名~張生。生叔叔的母親不止一次的埋怨過奶奶,也許壞就壞在這個小名上了吧!
張生上學很厲害,一路到了大學畢業,那個年代可是個保證鐵飯碗的硬槓槓啊!畢業後,張生分配去了國營磚廠做會計,和戲本子的劇情一樣,和廠裡的一個姑娘好上了,對了,就是那個衣著鮮亮的省親姑奶奶!
姑娘家一百個願意,高攀了生叔叔這個吃公家飯的高材生,好事眼看就要終成眷屬了。可萬萬沒有想到,命運像個調皮搗蛋的孩子,有時候毀人不倦的沒商量。
國營磚廠的直屬上級給了一個名額,是調入市工商局的指標,這可是相當金貴的,祖墳冒青煙的節奏,純粹就是離開雞窩,飛向梧桐樹變鳳凰的高光機會。無疑,這個符合指標的只有生叔叔。
姑娘這下忐忑不安了,本來就是高攀,現在對方又是要調入市裡的行政單位,幹部級別,姑娘實在是怕生叔叔飛了,無論張生如何發誓保證都不放心。
一哭二鬧三上吊之後,估計是舉全家之力想出來的一個惡毒的念頭吧,被計劃出來了,姑娘說,你要是真心的,用行動來表示吧!把指標讓給我,你有學歷有資本,再爭取下一次。這樣我們倆個不都能夠脫胎換骨,成為人上人了嗎?還能夠雙宿雙飛,舉案齊眉。
我都懷疑,姑娘為了說服生叔叔,達到目的,單去學了這幾個詞兒吧?
愛情至上的書呆子,真成了“西廂記”裡張生,被愛情衝昏頭腦是不計後果的,生叔叔申請了指標,等批下來的時候,換作那一欄寫著親屬關係的姑娘的名字了!我不理解那時候居然還有這樣的操作方式。
姑娘如願以償的成了金鳳凰,可這個金鳳凰飛走了,卻一去不復返,從此再也沒有飛回來。
生叔叔覺得,愛她就給她最好的,包括所有。在生叔叔滿心歡喜的等待中,姑娘結婚的訊息傳來了,嫁給了領導的兒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家人搬到了城裡,姑娘的兩個弟弟也脫離農村,從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狀態,直起腰做了國營工廠的臨時工,在那個年代也是相當不錯的。
生叔叔還在磚廠做會計,沒有什麼過多的反應,倒是他的父母,把姑娘家已經空無一物的屋子,統統打砸了一遍,算是出了一口氣。
終於有一天,滂潑大雨中,生叔叔喝醉了酒,從磚窯走到了家,發了一晚上的高燒,第二天,便魔魔怔怔的變了一個人,任誰問什麼也不出聲,醫生神婆都束手無策。他不信任任何人,不吃別人給的東西,不喝別人給的水,人們都說準是怕毒死他吧。
從此以後,好好兒的一個秀才變成了瘋子。村裡人都說這是相思病,只有那個姑娘能夠救他。生叔叔的父母、親戚託人去找姑娘,得到只是斬釘截鐵的回絕。
年復一年,村裡便每天有一個白淨的瘋子,微笑著嘴角,輕聲嘟囔著誰也聽不見,更聽不懂的話,來往於磚窯和村裡,直到很久以後,磚窯搬遷了,他還是固定的路線每天走著……
雖然不知道姑娘是不是心裡怎麼想的,我覺得她但凡有點兒良知,這輩子也不會心安吧?踩著別人得到的東西不燙手嗎?一家人極度自私的決定,毀了生叔叔的一輩子!姑娘家舉家搬離是明智之舉,否則在村裡,不但沒有立錐之地,更甚者正義的老百姓們會用吐沫淹死他們。
那次,姑娘唯一的一次來看望生叔叔以後,生叔叔的情況好了一些,有時候能夠在村口坐下來,歇一會兒,看看中老年婦女們扯閒篇兒,看看孩子跳皮筋,看看男人們喝酒抽菸,但就是不說話,聽二嬸子說,姑娘走的第二天一大早兒,生叔叔拿著姑娘帶來的衣服吃的,在河坑邊上,一把火燒了,燒的黑渣渣都扔到了河坑裡,一點兒痕跡都沒留。
生叔叔就這樣溜達著,微笑著,白淨著過了一天又一天,50多歲的時候,在一個白雪飄飛的冬天,完成了守村人的使命。不,他守著的不是村子,他守著的是他那一份乾淨真摯的感情,雖然所託非人……
說他傻也好,說他瘋也好,說他相思病也好,張生從戲裡走出來,又回到了戲裡,用一輩子寫了一場屬於他自己的人生大戲,顯然遇人不淑是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