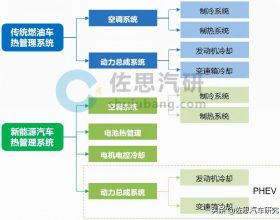第二章 走向冷水河畔
(接第一章)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紅衛兵運動暫時停下來了。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高考升學已經停止了,到1968年為止中學畢業和即將畢業的學生無法進入高中和大學,又無法被安排工作。此外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依然在延續。一個又一個大批判運動還在進行著。早請示晚彙報如同教徒早晚功課,祈禱誦經一樣雷打不動。不同派別的群眾組織還在互相毆鬥。學校已經完全停課,學生大部浪蕩街頭,成群打架的事情,經常發生。學生自然形成不同的團伙,黑社會的雛形已經隱約可見。更有甚著,呼朋喚友,一聲呼叫:“走,打架去”!於是隨聲而起,甚至對手是誰,問也不問。積累六屆一千七百多萬中學生前途迷茫,變成了社會的動盪因素。如不解決,後果不堪設想。
中央領導機構也意識到需要尋找一個有效的辦法將這批年輕人安置下來,以免情況失去控制。於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偉大領袖的一聲號令下,轟轟烈烈的展開了。我也就在這個時候,離開了我生長成人的西安,西安東關,東關古新巷而來到漢中,南鄭,冷水河畔。
我本來應該,也完全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可是,人生的道路,卻被人為的拉向了另外一個岔道。我雖然彷徨,雖然逆反,雖然失望,雖然痛苦,但是行動上卻還是主動的順從,從而完全改變了自己的一生。卡爾•馬克思的父親,亨利•馬克思說過:“人生的道路是漫長的,但關鍵的時刻卻只有幾步,尤其是年輕的時候”。我體會的太深太深。
1968年末的一天下午,西安火車站廣場人頭攢動,哭聲如潮。西安最大的一批下鄉知青就要出發了。父母拉著兒女在哭泣,同學相擁而流淚。我的心哇涼哇涼,此一去,何日得以回還?此一去,前途多麼迷茫,此一去,一生居於他鄉。我本來還壓抑著自己的情緒,不想外露。可在火車開動的那一刻,同學長安突然抱住了我,嚎啕大哭起來。我的情緒一下子爆發出來,哭聲和淚水,伴我離開西安,久久不能平靜。
當火車停在寶雞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車窗外樓房窗戶燈光閃閃,一個個溫馨的家庭享受著快樂和幸福。父母的關愛,兒女的歡樂,夫妻的溫存,孩童的活潑調皮,如同就在身邊。那讀書聲,談笑聲,孩子的唱歌聲,聲聲如在耳畔。而我們,卻要走向……。我心中充滿苦楚。今晚我的家,我的孃親,會怎麼渡過呢?我走了,留給她們的只有孤獨,只有失望,只有擔心,只有悲傷。這完全不同的場景,使我充滿惆悵。我默默在心裡湧出一首臭詩:“車外燈火通明,天倫之樂無窮,明知南轅北轍,何日調頭向東?”
自那時候起,我的身份就是“知青”了。我也深知,從今往後就是“冷水河的農夫”了。
冷水河出米倉山北麓,沿河三十多里一馬平川,分為四個公社(相當於現在的鄉)。一路像撒豆子一樣撒下了我們的同學。我們一群是籮筐最底下的“豆子”,被撒到了最東邊,最遠離縣城的光輝公社。
生產隊來鎮上接我們的是大隊革委會的女副主任。大概四十歲左右,胖胖的身材,滿臉笑容,挺和善的。可能從沒見過省城來的男人,她羞答答的招呼著我們。讓同來的社員用雞公車裝上了我們的行李。雞公車看來挺簡單的,上面是平置的A字型木架,下面是木質獨輪。推起來臀部左右扭動,以調節平衡。據說這就是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
給我們安排的住房,是一個改嫁他村的“風流寡婦”的空房。後來聽說這寡婦嫁到這裡時二十剛剛出頭。在鎮上上學時,喜歡上了我們村的一個孤兒。那男孩學習非常聰明,咣咣戲(南鄭地方戲)唱得還不錯。就是父母早逝,家境十分困難,沒有經濟來源。在學校也比較孤獨,比較自卑,還經常受到同學欺負。可和他一起讀書的“風流寡婦(當時還是純情少女)”偏偏就喜歡上了他,女孩是二十里外一個村子地主家的姑娘,長得十分漂亮。那倆眼睛特別水靈,一對酒窩,一張小嘴,一顰一笑無不令人動心。姑娘雖然出身不好,處處受人歧視,但是膽子不小,算個敢作敢當的女漢子。是她處處護著他,使他少受許多欺負。生活上,物質上也時時接濟男孩。
他們是在中學畢業後結的婚。文革期間,結婚也必須革命化,加上一個是“狗崽子(文革期間血統論非常囂張,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的辱稱)”,一個是沒人看得起的孤兒,所以婚禮十分簡單。婚禮當晚,新娘子的美貌就引來一些村皮無賴的騷擾。他們欺負新郎的懦弱,對新娘子動手動腳。性子剛烈的新娘子奮起抗爭,導致鬧房不歡而散。沒想到第二天,新娘子作風不好,破鞋,新婚沒有見血,外面還有相好的傳言,已經滿村傳開。那時候,農村沒有電,沒有電視電影,沒有其他文化娛樂。所以,傳閒話,說髒話,床笫之事成了社員的取樂手段。遇有閒話,越傳越多,越傳越精彩,也越傳越下流。這樣新娘子的“風流韻事”似乎也就鐵板釘釘了。甚至無賴們打賭,看誰能先把這女人睡了。
六七年,在全國範圍出現了以“文攻武衛”為藉口的大規模武鬥,我們村也不能例外。新郎官本來文靜,但是,還是被別有用心的傢伙逼去武鬥了。第一次上陣,我們村就敗了下來。村皮無賴本來就沒有戰鬥力,但是,逃跑倒是不慢。結果,新郎官“戰死沙場”。有人說是被自己村裡人打死的,後來也沒有查出個結果。反正,新娘子以後的境況是可想而知了。
新郎官安葬後第三個深夜,新娘子的屋裡,就傳出慘叫求救的聲音和村裡勢力最大的無賴的得意笑聲。村裡鄰居懼於無賴,不屑於新娘子的聲譽,竟無人出手援助。新娘子的尊嚴,名譽,身子從此毀於一旦。後來,新娘子生了一個孩子,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無賴,倒有點像大隊革委會的一個頭頭。於是“公共汽車”的綽號,就成了新娘子的官稱。
風流寡婦(我還是叫她風流寡婦吧,至少比“公共汽車”文明一些。)後來無奈帶著孩子改嫁到外村一個死了妻子,因為地主成分一直找不到媳婦的男人家裡,也總算門當戶對,同病相憐了。
我們來時,村上就以安排學生的名義侵佔了她家的房子。
房子不大,窗子很小,門扇很厚,山牆上端漏著一塊。冬天的風完全可以直吹進來。腰子形的灶臺和住房一起,屋裡房頂,牆壁被炊煙燻得黑黢黢的。床鋪是木頭做個矩形的框,下沿裝五條兩寸寬的木撐。放上竹子做的笆子,再放滿稻草。我可是第一次睡草窩的床了。
我們在同一生產隊下鄉的是同班的四個關係很好的男生,沒有女同學,沒有給自己準備好將來做媳婦的後備力量。四個小光棍,睡在風流寡婦的屋裡,那寡婦的影子,那寡婦的氣息,那寡婦的風流韻事好像就在身邊。雖然我們始終沒有看見過風流寡婦,但心裡總有一點怪怪的感覺。
冬天,農村沒什麼活可幹,每天早上,晚上到大隊部跟著接我們來的白姓女副主任,拿著紅小書,面對領袖畫像請示彙報。內容完全跟她唸叨,像懺悔,像祈禱,像祝頌。其他時間,我們就去周圍瞎逛。
村子旁邊不遠,就是冷水河。河面在這裡已經有一里多寬了。冬天河水不多,很多沙灘外露,有不少野鴨,白鷺在覓食。河心有一個很長的島,那是個林場。那裡也被撒了幾顆“豆子”,我們學校的幾個同學。其中高中的同學,明顯具有遠見卓識,還帶來幾個女生,後來竟然還做了他們的媳婦。
西邊和東邊各有一個鎮子。我們經常步行去那裡閒逛。喝碗熱乎乎的豆漿稀飯,吃碗香噴噴的麵皮。西邊鎮子原本不大,鎮南面是進出米倉山的山口,所以鎮子就叫“山口子”。這裡也撒了許多“豆子”,其中一個,後來竟成為我終生最好的朋友。山口邊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神廟,叫“娘娘山,娘娘廟”。說是漢王的娘娘在此住過,想必是呂后娘娘了。
那廟在文革初期已經被破了“四舊”。不過失去屋頂的大殿,牆壁上還有不知何年何月留下的壁畫。記得好像是八仙過海的故事。我一個同學,比我高兩屆。是個高度近視,好像有一千多度。本來不該下鄉插隊,可是家庭出身不好。他爸是黃埔後期畢業,沒跟林彪,沒跟徐向前,沒跟劉志丹,偏偏跟了戴老闆。文革時弄了個“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帶著。我同學不下鄉插隊更沒出路,於是和同學們一起來到冷水河畔。
有一次我們爬上娘娘山娘娘廟去玩,大家去欣賞牆上的壁畫。那牆壁挺大,距離近了沒法看到壁畫全貌,所以都儘量拉開距離。只有我這高度近視的同學,臉都快貼到牆上了。我們笑他是瞎子摸象,他說:“我可是窺一斑而知全豹啊”。幾年以後,我們都紛紛招工離開了農村,可是“窺一斑而知全豹”卻遲遲沒人接收。除過他的身體條件外,家庭出身是最致命的弱點。他還調侃的說:我這都是“先(人)兒的害”。
東邊也走十來裡,就是城固縣的上元觀鎮了。那可是個遠近聞名的大鎮店。我們去的時候,四個城門還在,東西南北四條街道,滿是木排門面的商鋪。商店,飯館很多,還有銀行,郵局,書店。但是所有的門臉都塗上了鮮紅的油漆,招牌也統一是“毛澤東思想宣傳站”。我們為了區別店鋪的型別,就分別稱之為“毛澤東思想百貨宣傳站”; “毛澤東思想副食宣傳站”; “毛澤東思想生產資料宣傳站”等等。說是一天中午,“毛澤東思想圖書宣傳站”來了一位顧客,對營業員說:“同志,買張主席像。”營業員立刻拍著桌子喊:“你反動,主席像也敢說‘買’?得說‘請’!”,於是讓顧客站到高凳子上批鬥。顧客誠心誠意的認了錯,在“靈魂深處革了自己的命”,營業員才饒過了他,給他捧來主席的畫像。那顧客顯然是心存故意,拿起就走。營業員追上問:“錢呢?”“請主席還要錢?”“笑話,買東西能不要錢?”“啊!大家聽到了吧?她說主席像是‘東西’!她是反革命。”於是,營業員自己爬上高凳子,痛哭流涕的低頭認起罪來了。
上元觀不同於其他鎮店,這裡是抗戰時期西北聯大所在地,所以至今文化氛圍仍然濃厚。這兒還有一個特產“上元觀紅豆腐(豆腐乳)”。弄個熱饅頭一夾,那味道“特色扎咧”!
有一天,我們來這裡瞎逛,居然碰到了我們的同學“烏龜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