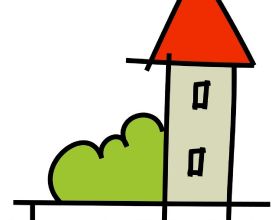我的遠房傻姨,今年五十出頭,第一次見她是過年禮節性的串親戚家的時候。
一大桌子親戚圍做在一個圓形方桌上吃飯,傻姨不錯眼珠的看我,她不認識我,也是第一次見我,就和我第一次見她一樣的好奇,驚訝。
上桌前大家齊齊找凳子挨坐在一起,傻姨早已經坐在那裡了。我搬了一馬紮想坐在小姨身邊,而她抓起我的手示意讓我緊挨著她坐下,雖然我萬般無奈,可還是滿臉笑意做到她的身邊。
也許多年來其他人習慣了那種味道,好像除了我每個人都可以無視那種味道的存在。其他親戚們們都吃的津津有味,聊的歡天喜地。只有我坐在那裡踟躕不前,僅僅吃了幾口青菜,再好的美味佳餚都難以下嚥。
那天坐車回家的路上,我問婆婆過年前就沒有給傻姨洗回澡?她身上的發出的氣味弄的滿屋都烏煙瘴氣?你們難道都嗅覺失靈了,聞不到啊!
婆婆說“今年洗沒洗咱不知道,二十多年都習慣了。”
這親戚串的,肚子都餓癟啦!婆婆笑!公公也笑!
傻姨!其實一點也不傻,懂得吃好的,喝好的!懂得兜裡裝滿瓜子邊磕邊嚼邊遛彎。
她今年五十出頭,卻邋里邋遢,如果勤洗澡勤換衣服,也是位漂亮的中年婦女。
衣服穿在身上從不捨得脫下,上面的灰塵與油質相互摻雜都結成了疤,一揭整塊整塊的往下掉。一年到頭不洗澡,遠遠靠近就可聞到一股濃濃的刺鼻的味道,年輕愛乾淨的小媳婦們都離得遠遠的,只有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肯和她說話聊天。
她,傻嗎?我不以為然。
也許天生腦子裡就缺一根弦,那根弦從投胎的時候就忘記輸入。
她,命很好。
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兩個兒子對她孝順有加。
前年傻姨的老公撒手人寰,我叫他舅舅吧!留下傻姨一個人孤零零的在那間小屋裡居住。
傻姨與舅舅居住的小屋裡,因為長年累月在裡面生火做飯以及取暖。牆面被煙熏火燎變的黑黑,青天白日的都覺得裡面烏漆墨黑的。床上的被褥也是油質斑斑,桌上擺滿摞滿雜七雜八的家庭物件,地上零零散散的都是扔的生活垃圾以及青菜。
傻姨很懶,連自己吃飯都想吃現成的。舅舅也是,有一個邋里邋遢的妻子,他自然而然也好不到哪裡去。
據說舅舅在世時對傻姨那是萬般寵愛,捧在手裡怕摔了,含在嘴裡怕化了!舅舅一個月掙個千兒八百的足夠兩人解決溫飽了。
傻姨能遇到舅舅也算是她的福了!
傻姨姊妹眾多,經常給傻姨買衣物,過年過節時常給她零花錢。這麼多妹妹當中就屬她六妹過得寬裕,也是給零花錢買衣物最多的一個。
自己的老父老母去世很早,家裡就剩下一個說傻不傻說憨不太憨叫人時常掛心的老姐姐了。
這是她們姐妹經常掛在嘴邊的話語。
好日子就持續到舅舅去世一年後。
傻姨最近好像越來越傻了。一桶油擱置了一年多,連油桶蓋都沒有拆開,這麼長時間了連一頓飯都沒有做。
表嫂說“那一年農忙季節,傻姨往家裡偷偷拿大街上鄰居曬的糧食,她還死不承認。”斷斷續續持續了好多回,以至於兩個兒子挨個給人家賠禮道歉。
兒媳們很生氣,又無可奈何。
最近又發生一件讓我聽了都發狂的事情,也許是寂寞也許是傻得被衝昏頭腦。
這回是真傻了!要不正常人幹不出這種丟人現眼,是人聽了都無比憤怒的傻事。
村裡有許多老光棍,傻的離譜的傻姨經常偷偷摸摸的去。兩人關門閉戶在屋裡打鬧,在屋裡調戲,這些話語都被在老光棍家屋後乘涼的老頭老太太們聽的一清二楚。
正好那些人都是些愛扯東家長西家短的人,而後這件事被傳的滿城風雨、人盡皆知。終於有一次這件事傳到表嫂的耳朵裡,以前表嫂偶爾也聽到過關於自己婆婆的一些風言風語。有一老太太把原話背給表嫂聽了!聽著聽著都讓她都覺得有點觸目驚心、羞愧難當。
原本和和睦睦的一家人被傻姨的這一舉動攪的天翻地覆,再也回不到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