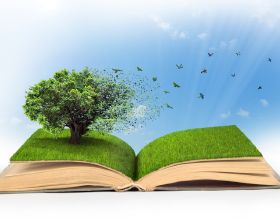天微亮,扎巴和南吉就起床吃早茶了。扎巴要去山下林中撿早菌子,一夜間,它們又會冒出許多來。南吉還在隱隱擔心昨天遇見的那些棚子,就讓扎巴帶上一隻獵犬防身。牧人在茂林深山被老熊、豺狼突襲是常有的事情。
母親代替扎巴擠牛奶,她提著奶桶晃晃悠悠地走進圍欄,像多年前的自己忽然歸來那般自在。母親坐在拴牛樁前頭抵奶牛的肚皮,雙手去牽引奶牛身下的奶頭,試了幾次,奶汁都沒有牽引出來,母親便對著奶牛輕輕地說話撫慰,讓奶牛放鬆,也讓自己的手指鬆軟起來。接著一股股雪白的奶汁就注入了奶桶。我用熱水為青措和小洛嘉洗臉,在他們臉上點了洗面奶細緻地打圈、清洗,抹上青檸面霜。他們洗淨的小臉蛋如六七月間的野桃兒,粉白。青措為了展示自己粉撲撲的小臉蛋,飛奔向屋外,爬上圍欄朝母親喊:“家婆!家婆!”母親只抬頭看了一眼,並不答應,是怕驚嚇了正在擠奶的犏母牛。
正午收工,門外響起了獵犬的叫囂聲,孩子們一齊奔向門外,他們在驚訝地大呼小叫。我們也隨之出門去看,只見扎巴肩上壓著一個黑乎乎的獵物朝小木屋走來。走到近前,他將獵物放在草地上說:“森林公主回來了。”原來是一頭笨重的野豬,脖頸上有幾道深深的齒痕,背部有被抓傷的痕跡。獵犬隨在邊上狼狽不堪,頭部嘴唇也有傷痕,它湊近野豬嗅聞,眼神中透出驚嚇且畏畏縮縮。扎巴朝獵犬吼了一聲,它知趣地躲開了。
南吉見狀便忙著在爐灶上燒開水,扎巴從柴房裡找出幾塊木板拼接在木屋外的草地上,將野豬挪移到木板上躺著。每個人都為這頭野豬忙活著,像過年一樣。水燒開了,扎巴用銅瓢舀起開水對著野豬從頭到腳淋上一遍又一遍,不時去拔幾根豬毛,能夠輕易拔下來了就翻轉來淋另一面。淋妥當了,扎巴拿出菜刀在石頭上正反磨礪幾下後為野豬剃毛,寧卡和吉美也拿出菜刀來幫著刮腿部和頭部的毛髮。野豬的頭沒有太多皺褶,刮來容易。毛被剔除乾淨了,扎巴用一根皮繩捆住野豬的一雙後腿與南吉合力將野豬倒掛在屋簷下,又淋了一遍熱水沖刷殘留的毛髮。扎巴取出別在腰上的褲刀,在野豬的一隻腿上割開一道小口,拿了一根鋼筋順著皮層一直捅到後大腿,然後鉚足了勁吹氣,邊吹邊打,野豬就鼓脹起來了。接著,扎巴用褲刀對準野豬的肚皮從上至下比畫了一刀,皮下的肥肉晶亮亮地次第綻開了。
野豬被割成了一對一對的吊子,放入大盆裡灑上花椒粉和鹽醃製,腸肚掛在柴房裡晾曬。切了半盆五花肉片,灑上椒鹽放在爐灶上燒烤,肉冒著滋溜溜的聲響。肉烤熟時,南吉從屋外端進來一盆洗淨的嫩綠生菜,說是:“五花肉烤好了就用這葉子包裹著吃,像韓劇裡那樣。”我問:“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南吉手指向圍欄背後的一方園子,它用塑膠薄膜蓋著,這是多麼神奇的事情,在這極高山之巔能長出這麼好的矮山蔬菜。
孩子們吃著生菜裹肉,雍貝若有所思地吃著烤肉,後來,他向扎巴打聽森林裡的遇見。
扎巴說,起初,菌子都躲著我,快走到山腳的時候才遇見了一朵松茸,剛剛冒出來有拇指大小,蓋了木葉讓它繼續生長,還在邊上的一棵樹上捆了一把青草來做記號。繼續尋找,看見不遠處的一棵杜鵑樹上長著一朵猴頭菌,那樣子真是像一隻縮頭縮腦的猴子,剛伸手要去摘的時候,身邊的獵犬朝著一處茂密的青槓林狂叫起來,接著朝那密林中飛撲過去。獵狗的嗅覺和眼力都超常靈活,遠遠就能看得見,並能曉得野物的存在。我慌忙爬到就近的一棵樹杈上藏身,只見青槓林中一頭肥壯的野豬領著幾頭豬崽走出棚子來尋食了,它們走得小心,始終不離散。這樣一旦被攻擊,它們就靠數量抵抗,相互救援,群體也能自衛的。看到這陣勢,我第一反應是喚回獵犬,誰知那畜生早已按捺不住猛撲上去,豬崽們立即緊緊靠攏在一起,形成一圈兒,它們的母親迎面保護與獵犬對抗。看到這樣的場面,我心都有些緊縮了,我捲曲舌頭急急地喚回獵犬準備掉頭回去。可是野豬和獵犬已經撕咬成團,獵犬的頸背被野豬咬住不放,後來,獵犬掙脫了,反撲野豬從它的頸脖下口,那對尖利的犬牙深深地扎入了野豬的命脈。野豬當場倒地,熱血突突地噴出。小豬崽們驚叫著四處逃竄,最小那隻躲進了棚子裡。獵犬或許是起了惻隱之心,放棄了對那些小豬崽的追捕。我跳下樹去看撕咬過的現場,獵犬傷痕累累,野豬已經斃命,便撿起野豬回來了。
雍貝聽完,緩緩放下手中那塊即將遞進嘴巴里的烤肉,隱秘地放到了腳邊,名字叫木子的小貓像一陣風樣叼走了那塊肉躲在爐灶邊吃起來。雍貝皺起眉頭不再說話,他看著爐口跳動的火苗,眸子晶瑩。扎巴拉開身邊的木桌抽屜,取出一本《野生動物保護宣傳手冊》,裡面夾著一張蓋有印章的紙頁。扎巴將它交給雍貝說:“野豬不是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但是我們也曉得不能隨便捕殺,只是這幾年牧場上的野豬繁殖過快,對草山和河谷的莊稼都造成了嚴重破壞。今年年初,我們格日切牧場就從林業部門申請到了獵捕兩頭野豬的指標,一直沒有遇見也就沒有刻意去捕殺。”
雍貝“鑑定”完畢,把手冊歸還扎巴,扎巴從雍貝的表情變化捕捉到了自己成功的表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