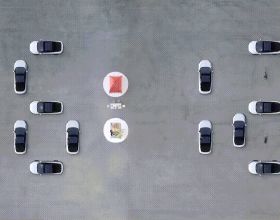我叫李善水,是位姑娘,揹著一隻碩大的藍色書包,提著叮噹作響的鋁製飯盒,在暮色中一瘸一拐,緩慢前行。
我的名字是姥爺取的,姥爺坐在院子裡,我搬了木頭做成的小板凳坐在他跟前,他念:“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憂。”唸完了他總會過一會才同我講話,那表情像是意猶未盡,我總覺得他像電視劇裡的老夫子,右手拿書,左手背在背上,腦袋轉著圈,聲音高昂,尾音悠長,樂此不疲。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這樣的姥爺,雖然他時常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但總會給我講很多有趣的故事。在我生病那幾年。
記憶中從生病到做完一整套檢查,這期間相隔十來年,也很慶幸從那場持續十來年的病痛中活下來,活過了08年的汶川地震,又活過了近兩年的新冠疫情,對人的生命也是在無數的瞬間,生出敬畏之心來,太過於莫測和堅韌,像村子邊上永遠不知疲倦流動的河水。
小的時候生活在川中地區的村莊裡,那時候九幾年,醫學,交通,人的思想都不像現在這般,生病了第一時間去醫院,以前人生病了都是找鄉里的閬中給看,抓一包草藥,拿回去熬成又苦又臭的棕褐色湯水,一日三餐,準時下肚。
從最開始的腳踝到後來的膝蓋,再到身體大大大小小的關節,我成了個半植物人,學也沒法上。這病也奇怪,說來就來,也沒個招呼,像沒有禮貌的客人,氣沖沖地往人家屋裡鑽,攆都攆不走,讓人內心莫名惱火。
我們一大家子人,加上我一共六個,為了我的病焦頭爛額,就連平時最喜欺負我的哥哥也開始對我愛護有加,不是逗我笑就是找來好吃的放我懷裡。
母親更是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瘦下去,她每天為我穿整好衣服,將我抱在院子裡的躺椅上,放好了,她要出門,去地裡幹活,但她總是回過頭來看我,看上好幾遍,才慢慢在我眼前消失。
我沒有表情,我的臉被病痛折磨成了一張冷漠的面具,只有眼睛是紅的,因為我常在夜裡哭,白日裡我不敢哭,哭是一種懦弱,是投降放棄,我那時候對生命還保持著一份執著,毫無來由的執著,也沒想過人若是死了呢。
第四年,那時候我和我們一大家子的人又捱過了艱苦的一年,我還是被放在院子裡的躺椅上,聽耳邊的風,看遠處的山川,近處的草木和頭頂的雲層,還有比雲更高的廣袤的天空。
我已經哭的很少了,興許是日復一日的便習慣了身體的僵硬和不知什麼時候會突然襲來的疼痛。
可是母親卻時常落淚,有時揹著我,有時就在我面前,我微微閉起雙眼,假裝不見。但是眼淚是有溫度的,她每月給我剪一次腳指甲,就把我瘦得只剩下骨頭的腳丫子放到她的掌心,她低著頭,自顧自地念叨:“怎麼就這麼瘦呢?是怎麼回事呢?”說話的時候她也從來不看我,有時候溫熱的眼淚從她的眼眶裡掉到我的腳背上,她輕輕地用大拇指拭去。因為常年勞作的原因,母親的手十分粗糙,尤其是冬天,手上裂開的黑色口子,像肆意生長開來的細密藤蔓,硌著面板上有輕微的疼痛感,我竟莫名地喜歡,那種觸感,是有生命在呼吸的,能調動人的神經,又不至於將人擊潰。
開春的時候,我的整個身體已經支撐不起腦袋的重量了。這副樣子的時間裡,記憶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大姑回來看姥爺奶奶。
午飯過後,那日春天的太陽剛剛好,不刺眼,也不灼熱,是連家裡的貓都會喜歡得伸懶腰的溫度,淡黃色的,像水一樣透明,又像瀑布一樣往下傾瀉。
家裡人端了小板凳,高板凳,藤椅,他們錯落有致地圍成了一個圈,臉頰微微泛紅,是生命應該有的樣子,唯獨我面色蒼白坐在中間,腦袋歪在椅子上,我只覺渾身不適。
大姑在我身邊站立了一會,我沒有理會她,我內心異常煩悶,想擺脫她的目光,但她不依不撓往我跟前湊,又伸出她細滑的和母親很不一樣的大手來牽我的手,我的兩隻手,從肩膀到指尖應該是一截被折斷後丟棄在地上的樹枝,沒有溫度,也沒有什麼重量,她一下就拉了起來,並且試圖把我從椅子上牽起來,讓我像個正常人那樣站立在地面上。
我焦急地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話讓她停止,我的家人他們都沒有說話,只是看著,他們知道我那樣被牽一下是不會死掉的,或許他們早就想讓我挪動一下,這幾年我像被釘在椅子上一樣的姿勢,讓他們也很絕望吧,我也知道我不會就此死掉,只是內心產生從未有過的危機感,像要被人甩出去,笨重的身體落在地上,無人理睬。
有一股恨意從心窩子裡生出來,往上衝,在我的眉宇間,眼中,和顫抖的嘴唇間,她徹底激怒了我,而最終讓我崩潰的是我的無能為力,我無法反抗她,儘管我語氣極盡嚴厲,也並沒有起到絲毫作用,最終我被氣地哭出了聲。
母親趕緊從我小時候坐的木頭板凳上起身,把我的雙手從大姑手裡接過來,她慢慢將我放回到椅子上,依著原先的姿勢,我仍舊在不停地抽泣。只是我的掌心貼在母親粗糙溫熱的掌心中間,剛才的氣憤和恐懼都被漸漸撫平下去。
大姑這時才覺有些尷尬,看我眼淚直流,埋下頭從兜裡翻了一張20元的紙幣放到我的懷裡,好聲好氣向我道歉,所有人都打著哈哈地笑,就連我耳聾的奶奶也走上前來把大姑放在懷裡的20元紙幣又塞到我的手心裡,她像講悄悄話那樣小聲地招呼我把錢收起來,買薄荷糖和夏天的葡萄。
他們所有人都把我當成了一個鬧脾氣,天真有趣的孩子,忘記了我是一個病人。
再往後走的日子,天氣就更溫暖了,但我還是老樣子,吊著一口氣,不死不活地折磨著我們那一家人。
我有一天聽姥爺在廚房同母親講話,姥爺說:“善水怕是救不活了,你看她脖子都歪了。”
我們祖上是做醫生的,就是姥爺的父親,我的曾祖父,在解放前有很好的名聲,那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沒有開始,曾祖父家靠著治病救人積累了一些錢財,後來農民的生活越發艱難,曾祖父開始免費給人治病,遇見確實艱難的家庭順帶的還送一些米糧,曾祖母為此經常吵鬧,後來也便斷了後一代人學醫的念頭,總覺得做醫生是個虧本的買賣,做不得。
當時姥爺的話傳到我耳朵的時候我內心是平靜的,經過幾年的煎熬,我對生命似乎沒有什麼奢求,生死也就那樣。那年我已經12歲,身體幾乎沒有發育,但思想是蒼老的,蒼老到接近死亡。
我覺得很奇怪,我一直沒有死,又活了一年,每天喝棕色的湯藥,苦臭得厲害,一天三次,但我的身體像被人下了詛咒,一點反應也沒有。
母親開始信奉鬼神,有一天她揹著我走十幾公里的路去一位仙姑家,同行的還有一位大嬸,是介紹人,她將仙姑介紹給了母親。
仙姑家也在村子裡,家裡還養了好幾只大紅公雞,用竹條編制的網格圍起來,看見我們的時候異常活躍,仙姑很客氣地邀請我們進到堂屋去,堂屋裡香火氣息很重,供奉的是南海觀世音菩薩,座下是三尺三的紅布,淨瓶一隻,瓶中一株清幽的綠色植物,一對蠟燭,兩團火苗。
母親把我放在一把老舊的木椅上,她自己轉頭接過仙姑遞過來的小凳子,她們很快就進入了話題,母親把我的事情,一一告知出去,從生病到現在,白天如何,夜裡如何,吃飯如何,上廁所又是如何,交代得清清楚楚。
後來仙姑開始作法,她雙腿跪地,身前放一隻空碗,從兜裡掏出打火機點燃一撮錢紙,火苗一小團在她眼前晃,她嘴裡小聲唸叨什麼,嘴唇張合速度很快,錢紙即將燃盡的時候,她放進碗裡,火苗熄下去,鋪了一層淺灰色的灰在碗底。接著她昏倒在地上,按照她先前的安排,有人將她抬到床上去,她平躺著,眼睛微閉。按照仙姑的說法,此刻她屬於靈魂離體,前往南海。
我和母親坐在離床沿大概1.5米遠的地方,在約定好的時間,按照約定好的方式,母親開始同她對話。
母親問:“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我們善水為什麼會得這個病?”說話的時候,仙姑交代要雙手掌心貼合,置於胸前,需得虔誠菩薩才能與之顯靈對話。
仙姑閉眼答到:“她前世的母親為了找她,沒有投胎轉世,現在纏上了她。”
母親繼續問:“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仙姑答:“辦法有,這個孩子額頭正中有兩顆痣,這兩顆痣是神明保佑,去不得,以後長大了也不能去,二從你們家出發往縣城方向走6公里,有戶人家的瓦房上有一株新生長出來的“綠蔭草”,你回去摘下來煮水給她吃。”
話說完仙姑在床上抽搐一陣,緊接著又恢復成正常人。
一副對剛才之事毫無知曉的樣子,她一直說她只是作為一個載體讓我們和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有一場對話,為我們答疑解惑。
那天回家,母親由於一路揹我,我看她手臂疼了好幾天,父親和姥爺是不信鬼神的,自然沒有人陪她同去,我想那時候的母親一定是絕望至極了的吧,只有她一個人做著那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不過耐不住母親的倔強,父親按照仙姑給的指令,果然在一戶人家的瓦房頂找來了一株生長的很茂盛的燈籠草,我們那個地方拿這種草是喂兔子吃的。
第二天我便喝下煮好的水,和著把草也吃了下去,那滋味我至今還能想來嘔吐一番,簡直無法言語,相比我每日三餐的棕色湯藥的味道,有過之而無不及。
只是從那次回來以後,我發現母親好像捉住了一絲希望,她好像真的信了仙姑的話,認為我不會死掉,只是這樣的希望隨著日子的消逝又很快就化成泡影,時間就是這樣,真假,好壞,在這場巨大的洪流之中都將無所遁影。
母親始終沒有放棄,我一邊繼續喝藥,一邊任由母親去折騰,我的身體,生命本就是她賜予我的。
熱心村民常給她講一些偏方,用童子尿燒開了給我泡腳,一團濃密的白色煙霧從我面前升騰而起,臭哄哄的。母親這次站到一邊,命令父親來照顧我,父親同母親是有些區別的,母親情緒容易激動,是個感性的人,平時裡是很愛說話的,只是極少同我講話,興許是怕說的不好傷了我的心,人在病中總是比常人更脆弱些。
父親及瘦,個子比姥爺矮了大半個腦袋。聽說父親小時候也生過一場大病,再加之長身體的時候正好碰上文革,那時候姥爺三個兄弟誰都不願意背這地主的名聲,按理是當時當家的大老爺去承當的,姥爺是二哥,骨子裡是個仗義的人,便把這名號安排在了自己頭上,為此父親和我的姑姑們也沒有少受文革的苦。平素裡肚子是吃不飽的,我們家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只有尊老愛幼,在我們家裡年齡最大的奶奶和年齡最小的我是最受一家人保護的,文革的時候更是想方設法顧著小的,父親下面還有個妹妹。後來我常聽奶奶笑話父親,每次吃完飯他都會把全家人的飯碗集起來,挨個的舔一遍。父親總是笑,然後又意味深長地說:“那時候餓啊,從來吃不飽。”
父親當時是有一個哥哥的,生下來身子弱,沒過多久便去世了,只匆匆看了一眼人世。當時有算命先生同姥爺講,那孩子是有大作為的人,命格不凡。我們那樣的家庭承擔不起,勸他節哀。這算命先生安慰人的方式也真是別具一格。
想來這人的命運也是千奇百怪,誰也不知道會怎樣。就像我吧。
再後來又被帶到村子邊上的沱江河畔去,有人說我是有一個魂魄被河裡的水鬼給勾走了,當然這是隻有母親願意相信,因為我七歲那年跟著母親趕集,曾經不小心在沱江河碼頭掉了下去,被人撈起來的。
母親傍晚去沱江河邊燒紙錢,帶個黃色油漆的小鐵盆,一邊點燃紙,一邊喚我的名字“李善水,快回來啊,李善水,快回來啊,李善水,快回來啊。”喚上三遍,在收攏下來的黑色帳子裡,聲音綿長。她將燒紙錢用的小鐵盆放在背風的山包包下面,再走回家。夜裡睡覺的時候她也時常那樣喚我。
再後來母親又聽來偏方,找各種草藥給我泡澡。
用老薑搗碎了,放在鍋裡炒熱,倒入藥酒,藥酒裡面泡的兩條長蛇,和一些活血化瘀的藥材,記憶中蛇膽是被我和著白酒下到了肚子裡,那時候臨近的村民,若是逮著蛇了,父親便會給我帶回一顆蛇膽,我吃了不少。為著如此,我直到如今也對蛇這樣的動物有些忌憚,總覺得萬物有靈,生活在食物鏈之中的暫且不說,但是蛇這樣的屬於野生動物的,是不應該在人的吃食之中的。
母親用勺子攪拌老薑碎末,熱敷在我的關節處,用白紗布裹很多圈,很緊密。
熱敷了大概15分鐘,取下來的時候兩隻膝蓋血紅,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膝蓋竟然有了些知覺,我可以稍微伸曲一下,沒有覺得疼痛。
我的病應該是從那一刻開始轉變的。突然之間於無盡的黑暗之中投下一條光柱,是生命的攀爬繩索。
生病以後的幾年裡,我從未見過一家人臉上露出來那樣真實的笑容。
我覺得那些日子,我站在生死線上,被兩邊反覆拉扯,而這一次我決定朝著生的方向跟他們走。
在精神恢復了以後,我開始吃食多一點,母親很開心,變著法的做我喜歡吃的菜,父親每次上街去都會給我買一堆水果。姥爺在傍晚的時候同我講他們以前的故事,講了很多文革時期的人和事,他那時候已經不給我講三國演義裡面的英雄故事了。我覺得這樣挺好,離我們更近的真切生活對我的影響是更大的,這重新燃起了我內心對於生命的執著。奶奶雖然耳朵聽不見聲音,但她每天在家,大部分時間就搬了凳子坐在我旁邊,給我腿上蓋一條毯子,端熱水給我喝,夏天的時候搖一把蒲扇給我吹風驅蚊。哥哥已經去縣城裡打工了,初中畢業,在親戚家安排的裁縫店裡,他好像是在我生命的那幾年,突然長大的,從一個調皮搗蛋,搶別人玩具的小男孩變成了一個有責任擔當會照顧人的大男生。
我後來還繼續做其他的治療,用老薑碎末子熱敷只是讓我的病情緩解了一些,讓我們的生活重新燃起了一絲希望,但還是不夠的。我繼續治療是開始做針灸,拔火罐,塗藥酒,喝藥酒,喝藥,這些填充了我整個生活線。
我開始慢慢能行走了,病雖然好了起來,身體氣色也比從前大好,但我內心卻充滿了自卑和虧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