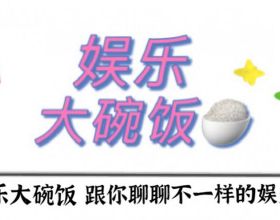朱成林先生
朱成林先生的作品
在比較西方現代美術的發展趨勢和當代中國油畫發展的現狀時,可以看到油畫在藝術語言更新上的潛勢表現在發掘藝術家感性特徵的一面。然而,時至今日,儘管從西方舶來的油畫在中國已經有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史,中國油畫也在各種風格取向、圖式創造上紛紛湧現出一批批優秀的藝術家,但就其整體而言,在色彩語言上真正有所建樹的藝術家還是比較少的。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特別關注朱成林先生的油畫作品,他的作品在任何一個展覽場合出現,都會讓人刮目相看。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國西北青海成長起來的畫家,對於邊陲的風情有獨特的感受。在炫目的景觀下面,有艱辛生活構成的獨特畫面;也有畫家讓客觀自然回到自己的內心時筆觸表達的昇華。這裡的中西之辨和古今之別,在朱成林先生的疑惑和辛勞中獲得了一種獨特的解決。
我始終以為朱成林先生是一位具有獨特藝術個性和創作活力的藝術家。前不久我觀看了朱成林先生的一個畫展,朱成林先生早期的油畫作品,不管處理得繁複還是簡潔,其個性特徵都非常鮮明。在用色、用線、組織畫面結構等方面,朱成林的油畫與西方的表現主義也有區別,他並不是完全依賴色彩的刺激,而是已經開始運用色彩強烈對比,製造一種視覺和心理效果,著重突出畫面的整體氣氛,營造出一種既和諧、響亮、歡快、明朗,又抒情、寧靜、溫文爾雅、詩意盎然的氛圍。這個時期朱成林先生在其藝術創作裡,就已經開始了對錶現形式美感這一問題的思考,這個時期他對形體奇妙的誇張變形、略帶中國畫意味的線的運用以及對灰色系列的情有獨鍾的運用,都給觀者留下了深刻的視覺印象。有不少畫家將寫意畫的逸筆草草與油畫的直接畫法結合起來,力圖改造出一種體現書寫性的油畫語言,儘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似乎犧牲了油畫語言的厚重性,有簡單粗率之嫌。俄羅斯美術大師瓦西里·康定斯基說:“色彩和形式的和諧,從嚴格意義上說必須以觸及人類靈魂的原則為惟一基礎,藝術的目的和內容是浪漫主義的。”而朱成林先生的油畫作品中的色彩飽滿、響亮,與富有韻律感的點線配合在一起,不但讓人感覺到藝術家本人愉悅的心情,更讓人品味到詩的意境。這一點與寫意畫的逸筆草草與油畫結合的畫家作品完全不同,卻與瓦西里·康定斯基色彩與情感的論述完全一致。我觀他早年作品,他創造了一批帶有鮮明青海地域特徵的少數民族人物形象,我發現他更關注對人物個性特徵的塑造,他描繪的藏族同胞,臉部刻畫非常豐富,色彩、塊面組合得很自由,明確地將特定的物件和身份凸現出來的同時,卻控制著自己沒有向完全誇張、抽象的方向演變,他也剋制著不去過分主觀地表現自己的激情,而是介於主、客觀之間的自由描繪,這大概是中國的表現性油畫的一大特色。
色彩作為獨立的造型語言得到真正的解放可以說是從印象主義開始的。印象主義畫家們為了表現瞬間的光色印象開始使用分色技術並加以短小的筆觸,在畫面上造成五彩斑斕的光色效果。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朱成林先生的作品來看,畫家開始厭惡沒有個性的甜膩調子。他鐘情於印象派之後的富有表現風格的作品。從他畫的一大批用筆率真、色彩純樸的寫生作品可以看到藝術一定要“進去”,要表現物件和自己內在的心理和感受。1996年法國之行歸來,朱成林的作品展出時震驚了青海畫界,也讓我久久地思索,到底什麼是中國人的油畫?到底什麼才是中國人的民族油畫?到底什麼才屬於油畫?法國之行成就了朱成林老師嗎?他的《巴黎街頭》《埃菲爾鐵塔》等,這些作品儘管取材異域,卻都是帶著一種類似鄉土的感情意識去表現,朱成林的畫風幡然一變,集印象派、表現主義和抽象主義之大成,自出機杼,創造出了一幅幅耳目一新的作品。
畫家從寫實逐步走向抽象,它除了畫面結構、色彩、造型發生變化之外,更出奇的方式就是筆觸,其實更準確地說就是它們結合在一起了,這種筆觸的豐富、千變萬化與色彩的層層疊加是朱先生個人成熟的風格,其面貌是一個很重要的引數,或者是一個指標。這時候他希望完全和別人不一樣,跟國內油畫家不一樣,跟外國油畫家也不一樣。如果說他完全有自己成熟的油畫語言面貌,我覺得不同於印象派筆觸首先就是一個叛逆性的標誌,其次就是色彩的地域性特徵。怎麼講,我覺得朱先生在創作過程中,基本上說是從情感上來的。但畫家始終還是站在令他著迷的青海本土語言上升華。這個時候我在想畫家形成這種面貌一定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嘗試,比如挑戰色彩的極限超過自己原來固有的這種色域的領域,他還從西方更多大師成就裡去吸收營養,或者看到了青海本土地域吸引他的東西,某些精神的觸動才使他做出了這個走向大師級品格畫家的嘗試。這樣推理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今天的朱成林先生的油畫面貌。
多年生活在乾淨、空曠、博大的青海,青海的地域特徵形成了畫家的自信和野性,這也應該是朱成林先生對青海地域藝術美的理解逐步深化的一個過程。對青海的一草一木看得越久,朱成林先生就越著迷。在青海不長草的山上,朱成林看到了別的畫家沒有看到的東西。正如他所說:“光線照在山上,有一種綢緞一樣的美。青海的美,讓我的內心發生了非同尋常的變化。”正是他與青海之間的那種無比的相愛,冥冥中必然會成就朱成林先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畫家。從取材於家鄉的《紅樺林》《雨後深山》《暖冬》《紅土山坡》來看,都是朱成林先生鄉土情結的反映。如果我把他這些作品作為“原材料”做再度創造的時候,就如老牛反芻,在重新咀嚼中體味出全新的內涵,所謂“全新”,就是在他過去的作品中不曾有過的新的品質。這種不經意的對已有作品的“反芻”,就是構成他多年來表現青海的一個特色的元素,也成為他的一種新的創作方法。先生為人低調,少言寡語,以一種極單純的方式生活,以一種極平易的態度待人,從不多事,從不炫耀,從不張揚,更不會想到找找關係炒作自己。但他的藝術卻耀眼奪目,光華燦爛。朱成林先生的個性色彩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標誌是對灰色系的大膽使用。灰色具有明度較低但也最沉穩、視覺效果最和諧但也最易安靜的特點。然而,朱成林先生慣用大面積灰色作主色調,明度較低卻層次豐厚,清雅靜謐而又溫厚潤澤。這個時期朱成林先生藝術的突出特點是純化了色彩這一油畫造型語言。正如他所說:“青藏高原的色彩是堅挺的,神秘的,高遠而通透的,它給人更多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如果說朱成林先生八十年代末的作品還善於汲取西方現代藝術諸流派中的色彩精髓,諸如印象派的色塊表現以及梵高、馬蒂斯等的色彩表現主義在他的作品中有鮮明的印記的話,法國考察歸來後的作品則放棄了印象派以來熱衷於顏色對比而改用層次多變、複雜微妙的調和複色組織畫面的色彩結構,同時以微妙的互補色使各種複色保持低明度、單純響亮、和諧歡快的效果。而且在特定的環境下,他把色彩與情感結合得更加緊密,並形成一種熱情而又溫潤的韻致,給人舒暢怡悅的美感。
杜夫海納(Mikel Dufrenne)曾經指出,繪畫不在畫家的眼前,而在畫家的手裡。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透過塞尚的疑惑發現,畫家總是希望能夠揭示事物背後的某種東西,儘管對於那種東西究竟是什麼會有不同的理解。杜夫海納和梅洛·龐蒂的說法,為我們解讀朱成林先生的繪畫提供了詞彙和理論支撐。與疑惑相應的另一個詞彙,就是杜夫海納反覆強調的“手”或者身體。人們通常將中西方繪畫傳統的不同表述為心與眼的不同。借用鄭板橋的術語來說,中國繪畫側重描寫“胸中之竹”,西方繪畫側重描寫“眼中之竹”。
朱成林先生很從容地從事他的油畫探索,他在創作中是一個非常自由的人,沒有拘泥於任何西方流派的約束。他沒有在中西兩種繪畫傳統之間做簡單的嫁接,而是希望透過一種艱苦的勞動,來化解它們二者之間的矛盾,也讓令他著迷的青海重新賦予了現代美學的繪畫形式。近年來,朱成林先生卻把日漸複雜深奧的技術,重新淬火,反其道行之,力求達到簡約、樸淡、精粹。正是朱先生用一生的渾然修煉讓他的藝術真正地達到了無求無慾而又隨心所欲,淡化一切規矩而又自成規矩,形成充滿生氣,充滿生命活力,屬於他自己的視覺印象。朱成林先生近年來似乎遠離了大家的視線,甚至有人說他是個隱身畫家。他的藝術不僅表現在作品上,而且首先表現在心靈裡,如果說金錢和權勢容易獲得人們的青睞,異化一個人的本來面目和自身價值,那麼他無疑是徹底保持其藝術家本色的一位畫家。這句話用在朱成林身上再也恰當不過,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一位“具有偉大心靈的”畫家,一位“徹底保持其藝術家本色”的畫家。然而,朱成林先生跟很多同齡人一樣,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經歷了屬於他的人生。可能正是因為他屬於青海的經歷,因為他所接觸的人,也因為他的天性,最終形成了他的油畫藝術和油畫語言。
作者:李積霖 稿件來源:青海日報 宣告:以上內容版權為《青海日報》所屬媒體平臺所有,未經許可禁止轉載,違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