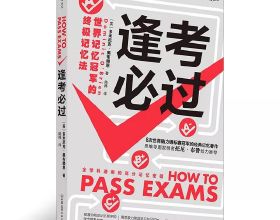來源:讀特

《我們季候的詩歌:史蒂文斯詩文集》 [美]華萊士·史蒂文斯 著 陳東飈 張棗 譯 陳東東 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7月版
一直以來,華萊士·史蒂文斯在國內都有許多讀者,包括許多當代詩人,都非常熱愛這位美國詩人。對他詩歌的翻譯一直沒有停止,曾有人統計過,他的詩歌《罈子軼事》,已經存在12個譯本,未來恐怕還會有更多的譯本出現。這本《我們季候的詩歌》,在我看來是一個史蒂文斯詩作的理想譯本。
這本書的珍貴之處在於,它是我們時代兩位重要的漢語詩人和一位傑出的翻譯家攜手合作的——詩人張棗已經離世十二年,他生前的譯詩不多,據說史蒂文斯就佔了他譯詩總量的三分之一還要多,是他比較用心也用力去翻譯的一位詩人,而且是在他生前唯一出版的譯詩集。詩人陳東東與張棗之間維繫數十年的友情,他與陳東飈的默契,所有這些都賦予了這本書一種特別的意義,一個溫暖的記憶。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陳東飈就涉及史蒂文斯的翻譯,從《最高虛構筆記》到《罈子軼事》《史蒂文斯詩全集》以及這兩年又對《我們季候的詩歌》的重新修訂,可以說陳東飈與史蒂文斯打了幾十年交道,他非常瞭解史蒂文斯。在翻譯方面,張棗與陳東飈兩人的譯詩觀念不太一樣,這本書中能感受到張棗的個人美學觀念和陳東飈一貫的翻譯理念碰撞下帶給我們不一樣的史蒂文斯。
本書的書名,用的是史蒂文斯一首詩的題目——《我們季候的詩歌》,有意思的是,它也是一度在英美學界引起爭論的一個話題。據說,20世紀70年代開始,英美學界就“Whose Era”發起論爭,休·肯納(Hugh Kenner)認為20世紀英美文學屬於“龐德時代”,布魯姆就反對說應是“史蒂文斯時代”,理由正是史蒂文斯所寫既符合“我們氣候的需要”又恰切地再現了“我們的氣候”。(引自李海英《偉大的塵世之詩:華萊士·史蒂文斯詩歌研究》)布魯姆的這個說法恰好與我想談的一個關於想象力的話題有點關係。我想結合一下詩歌《罈子軼事》(陳東飈譯)來稍微談一下這首詩。
我把一個罈子置於田納西,
它是圓的,在一座山上。
它使得零亂的荒野
環繞那山。
荒野向它湧起,
又攤伏於四圍,不再荒野。
罈子在地面上是圓的
高大,如空氣中一個門戶。
它統治每一處。
罈子灰而赤裸。
它不曾釋放飛鳥或樹叢,
不像田納西別的事物。
史蒂文斯在《徐緩篇》裡多次提到想象力。他提到兩個命題:“1、上帝即想象。2、被想象之物即想象者”,然後推匯出想象者是上帝。他也說過,“人即想象力,想象力即人”——其實,他還想說,人即上帝。人即上帝即想象力。反之亦然。在史蒂文斯的詩緒中,他把想象力的地位放到最高處,就像被放置在田納西山上的那隻罈子。《罈子軼事》首先是關於想象力、關於虛構的詩,也可以說,就是關於詩的詩。布魯姆說史蒂文斯的寫作恰切地再現了“我們的氣候”,這個氣候是什麼樣的一個氣候?在一個詩人開始寫作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他所身處的時代,他所身處的氣候?他要如何把握這個氣候,特別是一個人的寫作跨度是半個世紀,如何在寫作的最初就寫下幾十年後依然有效的詩篇?答案無疑是想象力。正像上帝是一種想象物的同時它也是想象者本身。以罈子作為象徵的詩歌,它統領著一個詩人的身心,它被放置在最高的位置上然而並無實際的用途,它不曾釋放飛鳥或樹叢——《徐緩篇》裡,史蒂文斯做出更具體的說明“一首詩未必釋放一種意義,正如世上大多數事物並不釋放意義”——但藉由想象,它“再現了我們的氣候”“使得凌亂的荒野環繞那山”——作為詩人,我希望自己的寫作也能再現我們所身處的氣候,它取決於我們的想象,也經由我們的想象實現它自身。
(原題《放置在最高處的想象力》)
(作者:梁小曼)
本文來自【讀特】,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臺提供資訊釋出傳播服務。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