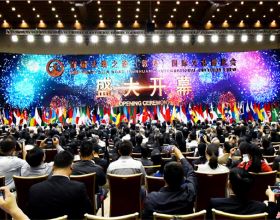隨著帝制的崩塌,北京文化受到的衝擊非常直接。原有政治勢力逐漸分崩離析,固有的文化體系也隨之而產生裂變。精英文化被稀釋,昔日以皇權文化為主體的完備的、系統的、成熟的北京文化,逐漸被民間化、市井化。貴族文化與平民文化直接接觸,宮廷藝術走向民間,“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新文化崛起,不同的文化型別都有特定的擁躉與市場,在各自的發展軌跡中並行競進,塑造出非常豐富的文化景觀與時代氛圍。
北京自元代起正式確立全國政治中心地位。歷經明清兩代,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地緣優勢為城市文化發展帶來多種優質資源,眾多國家級的文化機構紛紛建立,透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大量文化精英集中於此,構建了國家開展重大文化工程的人才基礎,多種因素的集合使北京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無可置疑的國家文化中心。
進入 20 世紀之後,清末新政開始推行,一批新式文化教育機構開始在北京建立,這種現代性因素的出現為暮氣沉沉的北京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1912 年後,北京仍然保留了首都的身份,政治地位仍然是文化地位的重要保障,傳統的慣性力量也使北京維持著強大的文化氣場,憑藉發達的高等教育體系,北京仍然是對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影響最大的城市。即使在 1928 年國都南遷之後,北京在中國的文化版圖中仍然是最具文化底蘊與學術品質的地方。
1912 年到 1949 年間,北京社會風氣日漸開放,近代西方新的文化觀念更大程度上被北京居民所接受。大批新式知識分子從南方湧入北京,一批現代大學在此建立,許多有影響力的新聞傳播機構紛紛進駐,以學生為代表的新興群體開始形成併發出自己的聲音,市民在政治意識、倫理道德觀念等方面都發生了相應的轉變,這些因素的疊加,使古老封閉的“帝都”催生出一系列嶄新的文化氣象。
19 世紀末期,與上海、廣東等開埠較早的國內城市相比,北京不僅在現代化程度方面明顯遜色,而且在政治風氣上也非常保守,一批政商要人與新式知識分子大都在遠離這座帝都的地方進行著他們各自的事業。尤其是上海,自晚清以來逐漸成為西學傳播中心, 戊戌以及庚子之後,這裡形成了全國最為發達的文化事業,涉及出版、教育等多個領域,眾多新式知識分子在此聚集,上海的文化地位持續上升。但在中國政治、文化一體化的格局中,北京的優勢地位一直不可忽視。從最初的創辦報刊、啟蒙民眾到後來的政黨辦報、影響輿論,北京對全國的引領作用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比擬。
蔣夢麟左 1,蔡元培左 2,胡適左 3,李大釗左 4 .1920 年 3 月在西山合影
長期以來,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的雙重地位決定了北京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消費城市。明清以來,“國都”身份對北京文化面貌的塑造產生了重要影響。這裡聚集了大批不事生產的人口,人口的職業結構決定了城市的消費性質,旗人的悠閒、官員的富有、士大夫的趣味、商賈的集中,也為北京娛樂業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小說家倪錫英就在 1936 年描述北平 “可說完全是代表著東方色彩的平和生活。那裡,生活的環境是十分的偉大而又舒緩。不若上海以及其他大都市的生活那麼樣的急促,壓迫著人們一步不能放鬆地只能向前,再也喘不過氣來。又不若內地各埠那麼的鄙塞簡陋,使人感受著各種的不滿足”。①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也認為北京是藝術和悠閒之都。後來,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對這種情形做了非常精到的描述:“在滿清的末幾十年,旗人的生活好象除了吃漢人所供給的米,與花漢人供獻的銀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都會唱二簧, 單絃,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 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或畫點山水,或作些詩詞——至不濟還會謅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兒詞。他們的消遣變成了生活的藝術。他們沒有力氣保衛疆土和穩定政權,可是他們會使雞鳥魚蟲都與文化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他們聽到了革命的槍聲便全把頭藏在被窩裡,可是他們的生活藝術是值得寫出多少部有價值與趣味的書來的。”
娛樂方式是我們觀察北京文化面貌的一個重要視窗。清代以來,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發展逐漸走向頂峰,京城社會文化消費市場異常發達,市民的娛樂文化豐富多彩,娛樂的物質載體——各種型別的娛樂場所遍佈內外二城。20 世紀初的北京,仍然聚集眾多新舊權貴、富商巨紳、軍閥政客,商界隨著軍政人物繁忙的交際活動起舞,社會經濟活躍興盛,各類消費行為熱絡,呈現出“動”的、繁榮的北京景象。雖然 20 世紀 20 年代進入軍閥混戰的階段, 戰事時而波及民生,卻未影響權貴富戶與政要人物的笙歌享樂。
優質的教育資源一直是北京作為文化中心的重要標誌,作為國都的特殊地位使其在高等教育方面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早在科舉時代,各省舉子紛紛雲集於南城各會館,演化為京城獨一無二的文化景觀。科舉廢除之後,各地學子仍然慕名而來,此地高校匯聚、學術機構眾多、大牌學人云集,是無可置疑的現代中國教育界、學術界的首席重鎮。
現代北京一直是國家高等教育中心。國立大學(包括高等專科學校)最為集中,到 20 世紀 20 年代初,已經由一所發展至九所。除了北京大學之外, 還有北京高等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北京美術學校、北京女子大學。此外還有私立高校如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中法大學、新華大學、華北大學、鬱文大學等。據 1926 年調查,北京共有大學 29 所,其中國立者10 所,私立者 16 所,教會及外國人所立者 3 所。
1912 年的清華學堂
大學這種現代新式教育機構的出現,不僅吸引了科舉制度廢除之後失去進身階梯的大批青年舉子的關注,更招徠了眾多飽有才學的新舊文人前往任教, 教授群體以及青年學生群體的形成是北京文化更新的重要推進力量, 大學成為各種思想流派競相爭奪的活躍領域。憑藉特殊的政治地位與長期的文化積累,高校資源非常豐厚的北京聚集起全國眾多頂尖學人。如果說在明清時期,與江南相比,帝都北京對學人而言並不具有絕對的吸引力,但到了1912 年前後,雖然南方許多新式知識分子對北京這座城市仍然沒有好感,但這並不能阻擋他們奔向北京的腳步。
1917 年的北京發生了兩件日後影響中國現代文化格局與發展趨勢的文化事件,其一是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其二是陳獨秀攜《新青年》北上發展,這兩件事情密切相關。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後,循“思想自由”之方針,採“相容幷包”之主義,進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聚集起了社會轉型時期各類“新”“舊”知識精英,包括陳獨秀、黃節、周作人、李石曾、梁漱溟、胡適、劉半農、王星拱、劉叔雅、劉師培、章士釗、李大釗、高一涵、程演生、吳梅、葉瀚、楊昌濟、何炳松、李辛白等。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成為《新青年》雜誌的作者。同時,依託於“最高學府”的聲名,《新青年》發出的各種思想與主張也加速對外傳播,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與輿論背景。隨著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的形成,新文化運動逐漸開展起來。不過,真正使“新文化運動”在全國蔓延開來的則是五四運動。
北京大學紅樓
五四之後的北京,成為新思想、新文化的會集地,同時,五四精神中的崇尚科學理性、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精髓也重塑了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和靈魂,讓他們以現代的眼光重新審視傳統中國和自身。因此,五四以後的北京處於最傳統與最現代的文化衝突之中,既相互抵制又相互滲透。它不像上海那樣完全浸淫於西方文明帶來的巨大的現代感之中而失掉自我,也不像中國內地的廣大農村那樣對外來文化完全拒斥而固步自封,而是形成了一種傳統與現代交織、相容、對峙的文化氛圍。
1927—1937 年間的北平通常被稱為“文化古城”。這一時期,北平原有的政治、軍事功能持續弱化,城市經濟陷入低迷,只有文化功能得到凸顯。憑藉多元的高等教育體系、深厚的學術思想資源和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北平在一種比較安寧的狀態中孕育了獨特而濃郁的文化氛圍。這裡聚集著多所國內一流高校與國家級學術機構,依託這些機構,大批高階知識分子維持著體面的學院派生活,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文化消費群體,並在文學、藝術與學術領域創造了一批流傳後世的精品。這些成果不僅與北平的地域特徵密切相關,也是構成現代中國文化發展整體面貌的一塊重要拼圖。
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力圖把政黨、軍隊、學校等領域置於三民主義的規範之下,三民主義逐漸被構建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是由於南京當局對北平的政治控制力較弱,導致三民主義在北平的影響有限,市場空間不大。遠離了喧囂的政治中心,為北平的文化與學術提供了比較自由的生存空間。雖已淪落為“故都”,但北平仍然維持了很高的學術水準, 這裡匯聚了幾所國內頂尖高校以及一些國家級學術機構,吸收容納了大批曾遊學海外的精英學人。他們在輸入英美學術文化的同時,也帶回了自由主義思潮,為北平“自由主義重鎮”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由於政治氣氛淡薄, 官方管制相對寬鬆,依託於穩定的學院體制,生活條件比較優越,這一時期北平的文化氛圍對秉持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而言非常適宜。同時,大量具有相同學術趣味與政治取向的知識群體的定期聚集,也維繫和強化了此地原有的文化環境。
作家林語堂在《京華煙雲》中用寫實的筆調,展現了近代北京城市生活的多元性:
滿洲人來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歐洲的白種人來了,以優勢的武力洗劫過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現代穿西服的留學生,現代捲曲頭髮的女人來了,帶著新式樣,帶著新的消遣娛樂,老北京也不在乎;現代十層高的大飯店和北京的平房並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壯麗的現代醫院和幾百年的中國老藥鋪兼存並列,現代的女學生和赤背的老拳術師同住一個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和尚、道士、太監,都來承受老北京的陽光,老北京對他們一律歡迎。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北平成為淪陷區,文化人大批南下避難,眾多高校與文化、學術機構南遷,北平與當時文化活動比較活躍的重慶、昆明、桂林、延安等城市基本處於隔絕狀態,與上海、南京等淪陷區的文化活動也接觸有限。日偽政府利用中日地域接近、文化相似等特點,鼓吹兩國“同文同種”的理論,透過構建嚴密的管制體系,在文藝、教育、媒體等領域實施一系列政策與措施,力圖將北平的文化生態納入到日化的軌道中,形成了相對封閉的文化環境,北平的文化事業遭到空前浩劫,曾經的“文化中心”只剩軀殼。
現代北京,新舊文化並存,中西文化並立,傳統與現代既有直接交鋒, 也有彼此吸收與借鑑,型別繁多,這主要是由這座城市居民的階層結構決定的。作為曾經的“帝都”,既有滿清貴胄遺老,也有大批政要與時代精英, 這裡從來不缺乏達官顯貴,同時駐紮著數量可觀的各國外交官群體。作為高校林立之地,眾多國內頂尖學人在此聚集,還有大批新式知識分子以及青年學生,已經形成了頗具聲勢的群體。除此之外,土生土長的北京本地土著佔據著底層社會的大多數。各種文化樣式都有自己專屬的舞臺,都有自身特定的目標觀眾,沒有哪一種文化樣式可以獨自佔據主體地位。
(來源:北京社科普及讀物《北京歷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