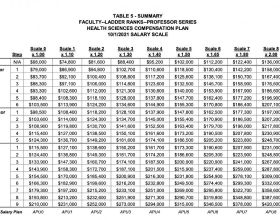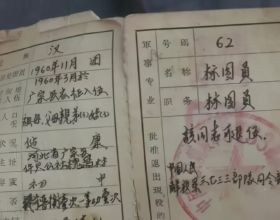1、美國學校裡的教育戰爭
2021年5月的最後一個週五晚上,美國佛蒙特州埃塞克斯郡的一座大樓裡,一群沒有戴口罩的(白人)家長們正在參加一個集會。與他們一同參與這個集會的還有佛蒙特州共和黨主席德布·彼拉多(Deb Billado)及保守派博主蓋伊·佩奇(Guy Page)。發言的是埃塞克斯郡韋斯特福德學區理事會新當選成員利茲·卡迪(Liz Cady),她以公開批評“黑命貴運動”、學區的教育平權政策和批判性種族理論而聞名。“大多數美國人以及我在佛蒙特遇到的大多數人並不關心你的膚色。他們關心的是你的品質!……公立學校應該遠離意識形態和層出不窮的理論,它們應當致力於給所有學生提供卓越的教育。批判性種族理論不管有多麼華麗的辭藻,都不應當出現在我們的公立學校裡。”她的發言得到了家長們的熱烈掌聲。
就在街對面的一座教堂裡,另外一場同樣以種族問題為中心議題的集會也正在進行。集會召集人民主黨州議員塔尼亞·維霍夫斯基(Tanya Vyhovsky)以及另一群(膚色各異的)家長和學生戴著口罩,保持著社交距離。其中一個學生說他們試圖在課堂裡討論種族問題,但遭到了其他學生的反對和忽視,甚至連他們抱以厚望的老師也對這個話題避而不談。與會的另一位學生認為學校裡所教授的歷史是徹頭徹尾的“教條灌輸”,白人教師和學生對種族問題態度冷漠是因為他們傾向於保護自己的社會權力,所以對種族問題視而不見。
這樣針鋒相對的集會像是一場“對臺戲”。起初是在學術界,後來擴散到新聞界,現在連公立學校裡,這樣的對立陣營也越來越常見。過去的幾個月中,在共和黨主導的一些州,如亞利桑那、新罕布什爾、俄克拉荷馬等,已經或正在透過法案,試圖禁止在公立學校教授批判性種族理論。批判性種族理論是否可以在學校被教授,已然成了一場“教育戰爭”,埃塞克斯是這場戰爭中無數的戰場之一,前文描述的集會是這場戰爭的某一場戰鬥。戰爭的導火索則是《紐約時報》推出的“1619專案課程”。
2、“1619專案課程”之爭
2019年,《紐約時報》啟動了名為“1619專案”的專題報道,其中以妮古爾·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發表的故事集最為著名。該故事集中一篇標題拗口的文章——《我們的民主的奠基理念在寫下的時候是錯誤的,是美國黑人的鬥爭使它們成為真理》——獲得了2020年普利策評論獎。文章批評了美國學校教授歷史的方式,認為美國的學校在教授歷史時,把自由和平等建構為這個國家的立國之本,但事實上當時還有成千上萬的黑人奴隸沒有獲得自由。文章進一步認為美國的歷史不應從1776年《獨立宣言》的發表開始計算,而應當從1619年第一批黑奴被販賣到北美大陸時開始計算。
400年前的一個夏天,一艘載著20餘名非裔奴隸的貨船抵達英屬殖民地弗吉尼亞的港口,雖然那時美國作為國家還沒有被建立,但後來的美國得以建立的一個重要基礎——奴隸制,已經開始了。“1619專案”致力於重塑美國曆史,將奴隸制的影響和非洲裔美國人對美國的貢獻置於歷史敘事的中心地位。該專案一經推出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批評者們(尤其是共和黨人)認為“1619專案”試圖否定或混淆美國賴以建國的根本原則,誤讀了美國曆史,是一項“宣傳”專案,其目的是分裂這個國家,是一種修正主義敘事。時任美國總統對“1619專案”發起了猛烈攻擊,聲稱左派“用欺騙、虛假資訊和謊言扭曲、歪曲、褻瀆了美國曆史,企圖告訴我們的孩子我們國家是建立在壓迫的原則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由的原則之上的”。網際網路上的反對者們把支援“1619專案”的人稱為“恨國黨(America-hating Left)”。
儘管存在重大爭議,《紐約時報》還是決定在美國的公立學校推進“1619專案”並與普利策中心合作開發“1619專案課程”,由後者開發教案、閱讀材料、課程活動並召集專案合夥人,旨在推動“1619專案”在美國的公立學校落地。芝加哥、馬薩諸塞、紐瓦克、新澤西、紐約及華盛頓特區等民主黨主導的地區陸續開設了相關課程。截至2020年5月,全美已經有超過4500多個課堂使用了該中心開發的課程資源,這一數字仍然在增長中。
與此同時,反對者們對“1619專案”也沒有停留在口誅筆伐,至少有5個州——愛荷華、南達科塔、密蘇里、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的右翼立法者提交了禁止學校教授“1619專案課程”的法案。愛達荷州、俄克拉荷馬州已經通過了類似的法案,明確禁止使用包括“1619專案課程”在內的眾多與種族主義相關的課程資源。其他一些試圖阻止公立學校引入“1619專案課程”的建議包括:揭示“1619專案課程”背後不可告人的目的;對資助“1619專案課程”的第三方機構進行審查;在州層面標準化測試中加強對“1619專案課程”內容的審查;要求教育部每年向國會彙報哪些學區部分或全部採納了“1619專案課程”;在聯邦政府撥款時只撥給那些沒有采用“1619專案課程”的學區。可以預見的是,圍繞“1619專案課程”的爭議和敵對行動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記憶體在於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
3、批判性種族理論之爭
儘管圍繞“1619專案課程”的辯論與歷史有關,但美國學校裡的教育戰爭卻不僅僅關乎文化和歷史,更關乎現實。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的學校一直在進行改革,但這些基於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改革——諸如基於標準的課程運動、加強問責、推動私人公司的影響、《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力爭上游》計劃等——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有色人種在教育上的比較劣勢。相反,白人與有色人種之間在教育機會和學業成就之間的差距越來越明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社會中種族歧視依然根深蒂固。
美國學界喜歡從性別和階層的角度對教育中的不平等現象進行理論化建構,至於教育中的種族差異,美國學界過去採納的是“劣等種族正規化(inferiority paradigm)”——有色人種在生理和基因上不如白人。這一正規化的一些基本假設是:人種間的智商有差異;白人中產階級(男性)被作為標準用來與其他族群進行比較;運用統一的方法與工具測量族群差異;儘管族群之間存在著社會階層、性別、文化背景、英語熟練程度等變數差異,這些因素都是外部因素,可以忽略不計。在這一正規化的影響下,一些研究指出,針對有色人種的補償性教育政策註定會失敗,因為目標群體的智商本來就低,在解決社會問題、制定教育政策、實施教育政策及解釋教育政策效果時應當考慮到人種之間的生理性差異。這一正規化由於對有色人種赤裸裸的歧視受到了廣泛的批評。隨著身份政治在美國社會中蔓延,談論膚色容易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人們對膚色的關注慢慢變得謹慎,如何在學校情境中談論種族問題也變得越來越棘手,於是“種族色盲主義(racial color blindedness)”逐漸流行。
種族色盲主義者認為在做決定、制定政策、採取行動時不應當考慮種族差異。當人們對種族問題毫不關注時,種族歧視也就不存在了。教育中的種族色盲主義體現在制定標準化的課程要求,對所有人種一視同仁,淡化種族差異,在此基礎上突出平等。例如,一種觀點認為,當不考慮家庭結構、父母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等因素的話,種族這個單一因素並不能使一個孩子的學業成就更好或者更差。黑人與白人成年後的收入差異不是由膚色決定的,而是由家庭結構、教育成就和工作性質決定的。
問題是,黑人與白人在家庭結構、教育成就和工作上的差距恰恰是種族歧視的結果。種族歧視,尤其是無處不在的系統性、結構性和制度性種族歧視,才是有色人種在學業成就上遭遇到的最大障礙。所謂系統性種族歧視是指那些原本根植於社會、政府和法律中的歧視性規則、實踐和習慣,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表面上看來是“公平的”,但實際上這些歧視性規則、實踐和習慣的殘餘影響滲透在整個社會系統的方方面面。例如,儘管美國公立學校裡的有色人種已經超過了半數,但公立學校裡80%以上的教師卻是白人(2018年資料);黑人為主社群的房價要低於白人為主社群的房價,其學區也相對較差;由於衛生條件不同,有色人種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要高於白人……
所謂結構性種族歧視是指由公共政策、機構實踐、文化表徵及其他社會規範所構成的體系,這些要素相互影響和作用,使得種族間不平等無處不在。結構性歧視不是某個人或者某個機構有意識的行為,它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的基本特徵。例如,相對於白人兒童而言,黑人兒童更有可能被診斷為有學習障礙而被送到特殊教育機構,因缺少關心和發展而沾染不良習性,然後他們會被開除,成年之後走上犯罪的道路。
制度性種族歧視則是指在社會和政府機構中潛在的系統性不平等資源分配。比如,一個黑人學生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利息往往高於跟他同班的白人同學,因此他不得不工作更長的時間以償還貸款;這使得他能夠花在學習上的時間更少,因而學業成就更加落後。制度性、結構性和系統性種族歧視就像一個龐大的蜘蛛網。制度性歧視是蛛絲,結構性歧視是這張網的一部分,它們一起構成了系統性歧視這張大網,將有色人種牢牢地困在網的中央。
與之相反,白人由於歷史或者現實的原因在高質量教育、體面的工作、高收入、擁有住房、退休福利和社會福利等方面享有相對優勢,這種相對優勢被稱之為“白人特權”——一種歷史積累的、潛移默化的白人特權。例如,白人不需要擔心佩戴什麼樣的口罩,甚至不用擔心是否要佩戴口罩,因為白人社群的感染率沒有黑人社群高;白人不需要整天擔心警察會突然叫停他們的車輛,用槍指著他們的腦袋;白人不會擔心隨時被別人當作小偷或乞丐。所謂白人特權並不是說白人沒有這些問題而黑人成天碰到這樣的問題,而是指黑人經常僅僅由於膚色不同而遇到這樣的問題。白人一旦被有色人種提醒種族問題的存在,就會出現劇烈的情緒波動,這一現象被稱之為“白人的脆弱”。
將種族視為一種社會建構而非簡單的生理差異,將種族歧視視為社會、政治、法律和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而不只是個人偏見的產物,這是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核心觀點,也是“1619專案課程”的理論支撐,這才是“1619專案課程”遭到抵制的深層原因。教育中的批判性種族理論主要探究教育中的政策與實踐如何導致頑固的不平等狀況並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些研究的物件包括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學校、非洲裔及拉丁裔美國人學區的撥款不足、對黑人學生過度的懲戒、有色人種在爭取優勢專案時遭遇的系統性障礙、為高中入學設定有傾向性的選拔條件、強化種族主義的課程資源等。
美國學校裡的教育戰爭(或意識形態戰爭)由來已久,批判性種族理論只不過是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的又一次戰鬥而已。例如,自20世紀30年代起,保守主義者試圖將鼓勵學生思考經濟不平等根源的教材逐出校園,聲稱這些教材給學生灌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20世紀90年代,美國公立學校的人口構成越來越多樣化,保守主義者與進步主義者圍繞傳統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展開了“經典名著戰爭”,保守主義者認為依據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增加來自其他文化的經典著作會壓制教育的真正動機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歷史科目,保守主義者於1994年試圖制定國家課程標準,禁止歷史教科書中涉及北美印第安人被隔離或受到暴力對待的內容。這次圍繞“1619專案課程”的爭論中,保守主義者認為該專案課程刻意抹黑美國的歷史,是針對白人的莫須有罪名,並將最終分裂這個國家。
4、教育戰爭是社會割裂的縮影
當然,學校裡的教育戰爭,或者說是文化戰爭只是社會割裂的縮影。讓戰爭的雙方感到憂慮的實際上是社會權力關係的變化,這才是戰爭的底層“語法”,學校的課程只是表層的“詞彙”而已。
12年前,當安德魯·哈特曼開始撰寫《美國的文化戰爭史》時,他用的是過去時態,認為有關如何定義美國的價值觀爭論已經結束。該書於2015年出版後,他的觀點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援。但不久之後,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人們很快就發現美國社會中的文化戰爭只是暫時沉寂了而已。特朗普被稱為當今美國“最卓越”的文化戰士,他給奄奄一息的美國文化戰爭帶來了“氧氣”,讓文化戰爭之火再次熊熊燃燒,其火勢甚至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即使拜登上臺也無法撲滅。美國社會的政治極化使得黨派的領導者們不得不從黨派利益出發,被動捲入深不見底的利益爭鬥;日益政治化的媒體也開始拋棄原本的平衡原則,明目張膽地參與政治,不惜利用虛假資訊達到自身的政治目的。
美國人期待一個把美國的整體利益而非黨派利益放在首位的領導者來結束這場文化戰爭,但拜登上臺之後的表現無疑是令人失望的。人們終於意識到,美國的文化戰爭或許永遠也不會終止,那些原本認為文化戰爭已經結束的人們紛紛糾正自己先前的說法,連不承認美國存在文化戰爭的一些人也開始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作者:周小勇,系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