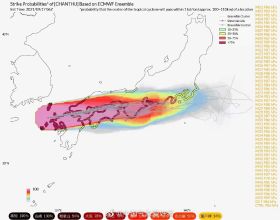耿諄(右一)
2012年8月27日下午,一名老人因病離世。他的後人將他火化。在老人的骨灰裡,他們驚奇地發現大小二十多塊有別於骨頭、疑似彈片的硬塊。
原來,老人是一名老兵,曾經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浴血奮戰過。許多像他這樣年紀的老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他們的身上,仍然留著當初為祖國奮鬥的印記。
但是這位老人還有一段更為不一般的經歷。他的名字叫做耿諄,在戰場上被日本俘虜之後,漂洋過海,竟在那個彈丸小國的土地上,發起了一場“暴動”,證明了中國男兒的錚錚鐵骨。
再度睜開眼時,他來到了陌生的國度
耿諄出生於1915年11月,是河南襄城人。他年輕時讀過幾年私塾,小時候家中開茶店,後來因為鬧土匪,茶店被人洗劫一空並燒燬。後來耿諄在街頭販賣舊書,同時也因此可以閱讀大量的書籍,學到了不少東西。
1932年,耿諄進入軍隊當兵。1937年8月,他已經被提拔為中尉。1944年時,耿諄已經是一名上尉連長,奉命防守洛陽。幾年的軍旅生涯中,耿諄永遠衝在戰場上的第一線,落下了許多的傷痛。他本以為自己說不定哪一天就死在戰場上,卻不想,最後竟成了一介俘虜。
那時,日本軍隊重兵攻打洛陽。而耿諄的部隊正好佈防在日本軍隊的進攻路線上。那時他們的連隊中僅有三挺捷克式輕機槍,一些漢陽造、三八式步槍,以及一些大砍刀。而日本軍隊則是重火器和5輛坦克。過分懸殊的兵力讓戰場的局面變得極為不利。
戰鬥到激烈處,耿諄的後背、左腳和耳廓等多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渾身鮮血淋漓。但是他依然浴血奮戰在前線。最後,耿諄所領導的70餘名官兵都戰死在戰場上。而耿諄因為一發炮彈近距炸響而昏死過去。
再度睜開眼時,耿諄已經成為了日本軍隊的俘虜。1944年7月,耿諄被日本兵押上一條海船,船上還有三百多名中國人。他們一同被押送到日本做勞工。汽笛響起時,人們看著翻滾的海水和漸漸遠去的大陸,心知自己再難返回故土,不禁都失聲痛哭起來。
當時日本對外發動戰爭,導致國內勞動力缺失,因此從各地都俘虜不少人運往日本國內充當勞工。日本軍隊雖然沒有殺害俘虜,卻待他們非常苛刻。
在船上時,日本為躲避美軍的襲擊,在大海上繞行了七天七夜。他們又擔心勞工們可能暴動,就把人全部關進船艙。因為害怕海水進艙,還用油布蒙上。再加上當時是盛夏,船艙十分悶熱,沒幾天就有人死了。
耿諄無法坐視同胞的死亡,主動與日本軍隊進行交涉。日本軍隊妥協了一部分條件,並將耿諄任命為勞工大隊長。
耿諄把同胞們分為9隊,還特意分出老人班和小孩班,讓他們得到應有的照顧。為了鼓勵大家,他說道:“弟兄們,千萬要保住自己的身子,只要堅持,相信還會有活著回來的那一天!”
到達日本後,耿諄一行人被押送至日本花岡作業所挖礦,那裡共計勞工達980多人。耿諄依舊被大家推選為勞工大隊長,帶領大家在陌生的國度等待回國的那一天。可惜的是,日本殘酷的勞工條件,讓這批人中的不少人都永遠留在了異國領土上。
最開始的時候,勞工們還能多少得到一點糧食充飢。沒有多久,他們就只分配到一點像是橡子麵做的小窩頭和蘋果渣。這種橡子麵不能發酵,做出來的東西黑黑的一團,極難下嚥。不少人就因此活活被餓死了。有的人甚至因為飢餓,去偷吃死老鼠。
勞工們吃食方面被如此苛待,乾的活卻不允許有一分一毫的偷懶。甚至遇到下雪,日本軍隊也要逼迫他們在水溝裡繼續幹活。除此之外,監押勞工的日本監工,更是常常以凌虐勞工為樂,動輒為一點小事將勞工打得皮開肉綻,血流不止。
勞工們甚至連生病了都不敢休息。有一名勞工薛同道病了,連路都走不動。誰又知道薛同道那時才23歲,曾是一名八路軍,身體棒得很,現在他卻可憐悽慘至此。
耿諄不忍心,勸他說:“別出工了,去病號房歇著吧。”薛同道只說:“大隊長,還是讓我上工吧,病號房裡口糧減半,更活不了人啊。”
當天,在回來的路上,薛同道就支撐不住,昏了過去。等他醒來時,看到一個朝鮮老媽媽看著他,偷偷遞了一個小米團給他。可是剛等他接過小米團,日本監工就衝了過來,一巴掌打掉米團,還一腳踹在他的臉上。
這樣還不算完,回到駐地後,日本監工們圍著薛同道毆打他,什麼木棍、鐵尺、皮靴,統統都招呼到這個骨瘦如柴,脆弱不堪的年輕人身上。一旁看到的勞工為薛同道的悲慘遭遇紅了眼,有些人不忍心地掉轉過頭。
有一個人忽然悄悄告訴耿諄說:“大隊長,你看他拿的是什麼?是用公牛生殖器編制的‘牛陽鞭’!”
這句話一下子點燃了耿諄本就苦苦壓抑在內心的怒火。他曾多次為了勞工的悲慘境遇去同日本軍隊交涉,要求對方改善他們的條件。
可是他每次都無功而返,勞工的境況反而更加悲慘。此刻他已經不想再忍耐下去,士可殺不可辱,何況即便繼續忍耐,也未必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於是,他暗中下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瘦骨嶙峋的仁義之師,與震驚世界的花岡暴動
日本軍隊苛刻的勞工條件,讓原先980多人的勞工驟然只剩下七百多名。死去的勞工都被火化放在一間小木屋中,耿諄希望未來有一天能夠帶著大家一起返回故土。可是面對越來越多的骨灰盒,耿諄的內心充滿了痛楚。
勞工工作所中,並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壞人。有人偷偷向耿諄傳遞訊息,說蘇聯會路過日本的北海道附近。已經做好決定的耿諄覺得機會來了,準備帶領勞工們發起暴動,並且逃往北海道,聯絡蘇聯軍隊,想盡辦法回到中國。
他先是找到一些骨幹說:“怎麼著都是一死,拼了吧,不活啦!”他剛一說完,其他人就立刻表示同意。接著,耿諄又假借抽菸借火的機會,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把所有人都擰成一股繩。
700多人的勞工,有人是國民黨軍官,有人是共產黨軍人,還有人是無辜的農民……他們來自五湖四海,難免會有摩擦,會有矛盾。可是這些人,一聽到耿諄的計劃,就毫不猶豫地同意,眼中閃爍著怒火,想要在這異國他鄉怒吼一聲。
耿諄很快就和幾位勞動骨幹定下計劃。他們會先殺死日本監工,然後趁機出逃,往北海道的方向走,看看能不能遇到蘇聯軍隊,或幸運地碰上船隻。
可是,即便有船,茫茫大海之上,他們一行人未必可以順利抵達中國。更何況,一路上肯定辛苦萬分,說不定就會被日本軍隊攔截在半路。如今他們都被餓得瘦骨嶙峋,病痛不堪,根本沒有多少的戰鬥力。
死亡,幾乎是顯而易見的結果。因此耿諄告訴每一個人,都給自己準備好用於自盡的東西。而耿諄,則是磨好了一把尖刀。他已經下定決心,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反抗日本軍隊的暴行。
1945年6月27晚上,是他們約定好要發起暴動的日子。可是當天晚上,耿諄宣佈要改變暴動的時間。原來並非耿諄突然心生害怕想要拖延時間,而是他知道今晚值班的人,是“老頭太君”和“小孩太君”。
這兩個人,雖然是日本人,卻對勞工們十分同情。“老頭太君”單獨帶工時,總是讓吃不飽的勞工少幹一點活。若是有人摔倒,他則會讓對方去休息。而“小孩太君”則是管理糧食,常常會盡量多給勞工分一點口糧。
若是他們今晚發起暴動,一來黑夜裡難以分辨,難免誤傷兩個同情中國勞工的監工。二來,勞工發生暴動,日本軍隊肯定會追究當天監工的責任。因此,耿諄就決定將發起暴動的時間推遲三天。
推遲三天,對於耿諄他們來說,有著極大的風險。700多人的隊伍,誰也不能保證風聲絕對不會洩露出去。可是他們卻仍然這麼做了,並且毫不猶豫。
除此之外,在發起暴動時,耿諄更是讓本就勝算渺茫的大家帶上病號一起逃跑。他還一再叮囑大家說:“暴動後不許進民宅,日本老百姓無罪,不能傷害他們,尤其是不能傷害婦女和兒童,不能讓人家說我們中國人是土匪。咱死,也要死個清白!”
暴動開始後,勞工潛伏至日本職員宿舍,他們準備先破壞電話線,避免日本人聯絡外界。但是卻被意外發現。爭鬥中,幾名監工和漢奸都被打死,其他日本職員逃了開來。沒有多久,警報聲響起。
耿諄不得已更改了原先的計劃,立即帶著勞工們匆匆往山上逃跑。
險死還生,重見天日會返回祖國
花岡暴動引起日本官方的注意。日本監工福田金五郎和清水正夫引來一批龐大的隊伍,包括當地的警察和地區的憲兵以及民間團體等人員,共計2萬多人,對700多人的暴動的勞工進行圍剿。
勞工們本就受到苛待,瘦弱不堪,又被數目龐大的敵人圍剿,只能依靠鐵鎬作最後的鬥爭。有的想要搬起石頭砸敵人,體力不支,一下子昏倒在地。許多人連自殺的力氣都沒有,最終都被敵方俘虜。
而耿諄準備好的尖刀,也在混亂中遺失。他只好解下自己的裹腳布,一頭拴在樹根,一頭套在腳上,中間一個活結勒住自己的脖子。腳一蹬,活套就越勒越緊。
眼看耿諄就要在異國他鄉結束生命,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敵人抓到了他,讓他再度成為一個俘虜。
面對被俘虜的中國勞工,日本軍隊毫不留情。他們強迫眾人跪在花岡町警察署前面的廣場上,任意打罵,連著三天三夜都不給一丁點吃喝。
日曬雨淋之下,又加上勞工們本就瘦弱不堪,很快就有人支撐不住,兩眼一黑,然後再也沒有醒過來。有資料統計,三天時間內,中國勞工就有113人死亡。
無法坐視如此悲慘的事情一直持續下去,耿諄和部分主要策劃者主動站出來承擔責任。在這期間,日本軍隊也一直嚴刑拷問耿諄,懷疑他是中國派來策劃暴動,試圖顛覆日本。面對這種汙衊耿諄並不承認,直言是無法忍受日本軍隊對勞工的苛待才發起暴動。
受盡折磨的耿諄後來被押至秋田監獄,一個月後,他又被押至裁判所。無論在哪裡,他都受到了折磨。法庭上法官最後判定耿諄為“戰時騷擾殺人”,要判處他死刑。其他人則是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年、15年不等,最輕者為7到5年徒刑。
面對這樣的結局,耿諄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他雖然並不認同日方的判決,也沒有想要上訴的想法。他心想,自己或許就要死在這異國他鄉了吧。
那時他們並不知道,日本已經戰敗投降。而耿諄接連轉換法庭,最後由軍事法庭改由普通刑事審判也正是這個原因。
在監牢的時候,有一個日本青年,暗中給耿諄遞了紙條。第一次是寫著“日本戰敗”,第二次寫著“世界和平”幾個字。後來耿諄打聽到,對方原來是曾經刺殺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未果的反戰派勇士,小長光。
沒有多久,耿諄的境況就得到了改善。而當初作惡多端的監工們,則是被列為戰犯押上日本的橫濱軍事法庭。耿諄因為身體虛弱不堪,不得已要先回國療傷。
等到1947年9月,他再度踏上日本的國土,作為證人,在日本橫濱軍事法庭上,飽含血淚地吐出身為勞工時,受到的壓迫和日本監工的殘暴。
誰能想到,曾經在日本監工的壓迫下,瘦弱不堪,氣息奄奄,甚至已經被判處死刑的耿諄,會成為原告,在法庭上控訴他們的罪證?
最後,法庭判處花岡作業所所長河野無期徒刑;判處花岡作業所中山寮寮長伊勢、監工福和清水絞刑。
同時,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被判為犯罪的勞工案件。
一紙訴狀,多年堅持,他只想為數百名死難同胞討回公道
耿諄後來就回到中國,在老家務農為生。他本以為這輩子就這樣子平平淡淡地繼續過下去,只是會常常想念埋骨異國的同胞而已。
沒有想到,日本秋田縣的老百姓,卻記得這樣一群鐵骨錚錚的中國人。在異國他鄉英勇地反抗壓迫,並不曾傷害到他們一分一毫。1953年7月,他們就自發地把部分中國勞工的遺骨蒐集起來,送回中國,安放在天津。
轉眼到了1985年,當時耿諄已經是71歲。他偶然在《參考訊息》上看到一條新聞:二戰期間日本秋田“花岡事件”倖存者劉志渠等4人,現向鹿島建設提出賠償要求。耿諄仍然記得劉志渠,當初還是他把劉志渠安排在勞工病號房中當看護。
面對這樣的訊息,他不禁想到,時隔多年,難道還可以追究日本人的責任,為過去的數百名死難的勞工討個說法嗎?他立即就寫了一封信,寄給戰後在日本定居的劉志渠。
而劉志渠收到信後,立刻就帶著日本作家石飛仁到中國河南省許昌市襄城縣拜訪耿諄。劉志渠說:“鹿島建設如此殘酷地迫害我們,我們有權向他們討還血債,向他們索要賠償。”
而同行的日本作家石飛仁,對於花岡暴動就非常感興趣。他對於其中受苦難的中國勞工抱有極大的同情,更對耿諄十分感興趣。
他就因此撰寫過一部再現花岡暴動的書,名字叫做《花岡蜂起——中國人強制聯行》。此次見到耿諄之後,回到日本的他立即發表一篇《耿諄健在》的文章,在日本引起轟動。
在日本,像石飛仁一樣關注中國勞工事件的還有一個由教師、律師、醫生和部分旅日華僑組成的名叫“中國人強制聯行思考會”的社會團體。他們專門調查和研究戰爭時期中國人被俘虜至日本強制勞動和遭受迫害的內幕。“花岡事件”也一直是他們調查和研究的重點。
耿諄晚年時參加的六十週年活動
這個社會團體,還在大館市的十瀨野公園裡,豎起一座高5米、寬1米的“中國殉難烈士慰靈碑”,在每年的6月舉行於紀念碑前舉行“靈慰祭”活動,來紀念“花岡事件”中的勞工們。
1987年6月,耿諄就受到這個社會團體的邀請,再度踏上日本國土,祭奠花岡死難的勞工。而當年的“小孩太君”也特意跑來拜訪耿諄,感謝當年耿諄為了保護他而推遲暴動的時間。
之後他還怕日本右翼分子會襲擊耿諄,時時緊跟在對方的身邊,保護耿諄。還有一些有同情和支援他的日本朋友說:“中國勞工若想打官司,我們可以提供包括資金在內的各種幫助。”
在那裡,耿諄還見到了日本參議院田英夫。在“花岡事件”42週年紀念會上,大館市市長、參議院議員、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等人都到場獻花致哀。許多旅日僑胞和中國駐日使館代表也前來憑弔烈士。
回國後,耿諄就聯合其他倖存勞工和部分死難者的家屬,成立了“中國勞工花岡事件受難者聯誼會”。1988年12月,他就以“聯誼會”的名義,正式向日本鹿島建設提出三項要求:
一、必須鄭重地向中國勞工謝罪;
二、在中國的南京、日本的大館各建一座紀念館,讓後人永遠牢記這樁慘案,永遠不再發動戰爭;
三、鹿島建設必須付以經濟賠償,花岡作業所986名中國勞工,每人五百萬日元。
中國政府在1972年與日本政府簽訂了《聯合宣告》中,宣佈放棄了國家間的戰爭賠償。但是並不代表中日雙方之間的民事間戰爭索賠也一併“放棄”,耿諄認為他們這些慘遭迫害的中國勞工,有權向鹿島建設追討血債。
但是鹿島建設態度強硬,拒絕後兩項要求,耿諄為此氣憤不已。1995年12月20日,耿諄和倖存者們一同在日本東京地方法庭,一紙訴狀,再度將鹿島建設推上了被告席。但遺憾的是,一審被日本法官圓部秀穗粗暴地中止審理,最終耿諄被判敗訴。
耿諄面對此情此景,對著日本眾多媒體抗議道:“這是日本司法方面的黑暗,是日本軍國主義死不認錯的再次體現。”
1998年5月,志願為中國勞工打官司的日本律師團團長新美隆,帶著日本律師團前往北京拜訪以耿諄為首的中國勞工,詢問他們是否還有繼續打官司。耿諄回答說自己絕不會變更自己的決定,一定要讓鹿島建設為中國勞工們鄭重道歉。
他甚至還宣告說:官司若是我們幾個先打贏了,賠償的錢我們一分也不拿,花岡慘案中986名勞工中只要有一人沒有拿到這筆錢,我們就永遠不動它。
其他幾名在座的勞工代表也立即表示贊同。許多老人都已經年邁不堪,一身病痛,可他們的身上仍然閃耀著奪目的光芒。
之後的幾年,耿諄就一直為這場官司不斷奔波,甚至他已經老到連走路都需要人攙扶,可是他卻始終不肯放棄。到2000年11月29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宣判,以耿諄為代表的中國勞工同日本鹿島建設為“花岡事件”訴訟案和解。
但在和解書的《聯合宣告》中,鹿島建設雖然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並進行道歉。但是鹿島建設卻將所有“花岡事件”受害者986人支付的5億日元的補償款,將透過中國紅十字會作為“花岡和平友好基金”進行管理,並設立一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運營委員會”。
日本鹿島建設將這筆補償金,說是“捐出”而非“賠償”,讓耿諄無法接受,拒絕領取這筆費用。他憤怒地說道:
“這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中國勞工不稀罕他們‘捐出’,只要他們認罪和帶有認罪性質的賠償。日本鹿島建設在其關鍵‘說法’上耍花槍,說明他們過去兇狠殘暴,現在仍是頑固不化、死不悔改。所以我決不妥協!”
到了2006年的時候,有人曾經去採訪已經91歲的耿諄。他身患疾病,急需金錢治病,卻仍然不肯領取那筆鹿島建設“捐出”的費用。直至2012年8月27日,這個97歲的老人永遠地離開了人世,也未曾違背過自己的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