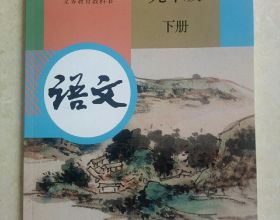懷念秋哥
我的表兄曾秋明,我們曾系兄弟姐妹都稱他“秋哥”,可直到解放後,我都七歲了,才知道”:他不是我的親哥!
2015年,在抗戰勝利七十年到來之時,他已滿八十歲,他的生日也正是八月15日。那天在病房中安享了他參與付出的先進坦克99A參加閱兵的訊息。兩個月後,在疾病的折磨中去世。我的哥,覆蓋著軍旗,身著軍裝,永遠離開了我們的世界!
他一生曲折得難以想象!但他無愧他光榮革命父母的希望,在革命教育下成長,將一生獻給了國家。
秋哥長期被病痛折磨,近幾月尤為甚至。儘管我們對他離去也可說早就有了思想準備,但還是無法接受這一事實。禁不住淚如泉湧失聲痛哭。一連幾天都無法解脫。現在一晃六年過去,我仍擺脫不了對他的懷念。你看了下面我回憶的他的文字,就能理解我們的那份深情。
我的童年與我秋哥一直在一起生活,我們是一生中彼此最瞭解、最知心的兄弟。從我記事以來,我就和他一起生活、讀書、娛樂、嬉鬧……他去世一個月前,我專程到北京趕到他的醫院,一連數日守在他的病榻床頭,我們一起最後回憶了遙遠的過去:
(一)白色恐怖下,父母差點被迫“丟棄”他
秋哥的母親是我的姑母曾子平,她原名曾穎明,是我父親的大姐。我的祖父就是武漢老通城(當時名“通成”)餐館的創始人曾厚誠。姑母幼時在武漢“聖約瑟女子中學”[1]完成中學學習期間,見識了武漢第一次大革命前後的浪潮和血腥,初步有了投身革命的理想。1929年考入復旦大學,就在這所有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等老師的校園,又親身經歷“一二八”戰火的教育,在勇敢支前活動的鍛鍊中更堅定了愛國信念。她開始一步步向往共產主義理念,走上革命道路。
1934年春,姑母在上海復旦大學文學院新聞系畢業後,進入“《申報》附設流通圖書館”,跟隨李公樸先生,與高士其、艾思奇等共事。後與韓籍抗日青年程葉秋成家。1935年秋哥在上海誕生,他的名字是父母名字各取最後一字(曾穎明,程葉秋)命名的,卻取用了母親的姓。
1936年底,在蔣政權“攘外必須安內”的下,秋哥的父母面臨過多次危險,被迫數次搬家轉移。後組織上欲將他們轉移去根據地,作為父母,眼看就不能照顧剛滿一歲的他,竟被迫忍痛在《申報》上刊登了一則啟事,大意是:
現有合法夫妻×××、×××,欲將孩子交人領養。子性別為男,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生,出生證件齊全。已經斷奶,身體健康。有意領養者請於一個月內來“量材婦女補習學校”聯絡,過時如無人領養將送至育嬰堂。
相信這個“一個月”的期限,乃是大姑對上天的最後祈禱和哀求,是他們在絕望中等待最後的變數。或許,她知道,因為她公開身份是《申報》僱員的原因,家人都會很注意讀《申報》的。
我不信神,但這次一定是神仙顯靈了!在武漢的祖父、二姑和我父親同時讀到了報紙上的啟事。我的父親與二姑當時是武漢大學的學生,二人慌忙請假從學校下山來,過江前就迫不及待地先發去了電報,勸他們停止輕率的舉措。到漢口便立即買了去上海的船票、以最快速度趕到了上海,將我的表兄帶回了武漢,從此,他就生活在武漢家中。
他是我祖父的第一個第三代孫輩,又繼承了曾姓,自然成了曾家最受寵的人。我奶奶蒲守道,她具有史上最完美最無私的母性,她理解女兒,相信她一定在做有意義的事,而且一定是出生入死無可奈何的事,於是她便付出無微不至的愛,讓秋哥得到了完美慈愛的照料。
(二) 秋哥在曾家長大
1938年,在武漢那不平凡的歲月裡,他才三歲。經常來我家的冼星海先生特別喜歡他,他也牙牙學唱著抗日歌曲。這位大音樂家曾將他放在我們家的私家黃包車上、拉著他在我家的公新裡巷道里瘋跑,逗他玩。自己也樂得滿身大汗。記得有篇回憶文章還提到過“三歲小孩指揮星海唱歌”一事:那時他三歲,拿了指揮棒要指揮星海伯伯唱歌。星海故意裝得很緊張,站得筆直,秋哥“指揮”慢,他就慢慢唱,秋哥指揮快,他就唱快,最後秋哥指揮風快,他快得唱不清,逗得秋哥和一旁圍觀的人大笑。
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爺爺攜曾家逃亡大後方。秋哥後來給我講了很多在重慶、木洞鎮、綦江趕水鎮流亡時的故事,講到“五三大轟炸”、講到“大隧道慘案”的僥倖錯過,講到奶奶轟炸時為保護我的受傷,講到最困難歲月的艱辛……讓我知道了我出生前後重慶流亡年代的很多事,我把這些寫進了《老通成曾家》的《不屈歲月》一章中。
抗戰期間,秋哥的父母在抗日前線,是新四軍的傑出幹部(另有文史和文學作品記載)。
秋哥在最後的日子裡,躺在病床上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海凝望著天花板對我喃喃回憶著:為了躲避轟炸,祖母帶家中女幼躲到木洞鎮多年,我的二姑曾竹恆將他視為己出,給了他終身難忘的愛。還利用自己當代課老師的條件,讓不到五歲的他進了木洞鎮小學。秋哥天資聰穎,成績竟一直名列前茅。秋哥對房東的孩子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對我如敘述親人般,講述他們後來的成長,特別是參軍赴朝和犧牲的那位房東哥哥的事蹟。
他哽咽敘述道:45年日本投降後,我們急著回漢,但買不到船票,那時想出川的人很多,在重慶朝天門為了買到一張出川的船票,就是等上兩個月也不會有影子。到九月,全靠爺爺在江湖上的朋友幫忙,讓奶奶帶上我們倆乘一小木船劃到江中,到江心去上輪船,上船後就擠在大副室邊上的過道上。奶奶把我捂在懷裡,席地而睡。秋哥說,過三峽時風有些大,輪船又嚴重超載,不知是吃水太深還是江水太淺,船底還“咯噔”了一下,把一船人嚇得齊聲尖叫。他說那聲音如有形,定可見如船形筆直地射上雲天。幸好有驚無險。我們的船安全航行了七天六夜——因沿途均有重量級人物登船,每個碼頭都耽誤很久。
回到漢口,我們一起臨時住在福熙大將軍街(蔡鍔路)中央電影院後面一棟樓房裡。當時爺爺準備復業,可資金不足,打算叫十歲多的秋哥當小學徒,在“老通成”門口賣煙。幸好被奶奶堅決抵制,這才讓叫秋哥等待進“法漢中學”初一讀書。
街邊人行道上,席地坐滿了投降待遣返的日本兵,秋哥帶我去拿小石子擲去“打鬼子”,我雖才三歲,但對日本鬼子的仇恨已是刻骨銘心了,當然很取樂。結果有個日本兵竟跳起來拿竹竿追打,幸虧有中國警察吼住了……
第二年,我曾大病過一場。那時候我父親還為秋哥請了個家庭教師。我長大才知道,是共產黨地下工委書記劉實,就以此為掩護潛伏在我們家中,為我黨得到蔣軍將突襲五師的計劃後,派人化裝成記者到鄂北送到了張體學同志處,幫助五師順利突圍。劉還在解放武漢前夕進行保護城市的組織工作……
直到解放後,我的姑母(已改名曾子平,任崇明縣黨委書記)回來,我才知道:秋哥原來不是我親哥!
我上小學後,他進一步成為了我崇拜的偶像。除了給我講過很多故事,引導我早早閱讀了《水滸》、《西遊》、《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書籍,讓我有了最早的愛憎與立場外,還教我畫地圖。他送了我一本《二戰後世界形勢圖》、要我幾十張一張張臨摹完,從此整個世界地圖印在了我心中。
我們還回憶起孩童時常常一起自己扮演《西遊記》遊玩,他拿根買的“金箍棒”扮孫悟空,表哥李聞陶拿個“釘耙”演豬八戒,我只能隨便拿個什麼當沙和尚了。
特別不能忘的是那些年的夏夜,我們在家裡平臺上乘涼,他躺在竹床上教我認天上的星星,給我講宇宙速度、萬有引力等方面的知識……我覺得他無所不知,他在我不到十歲時就提前把我帶入了中學生眼裡的科技世界,看他幫我借的科幻小說。

左起:秋哥、我、冰哥(李聞陶)、大妹(曽先恢)公新裡6號平臺1951年
秋哥十幾歲時在武漢“市一男中”讀書時就很優秀,是學生會的幹部。曾經偷偷寫信給報名參加志願軍。
不過不幸的是,他曾因一次意外摔倒留下腦震盪後遺症。
(三)秋哥走上革命路
秋哥畢業後保送到哈軍工,曾三次在軍旗前照相(這是最高榮譽)!大學畢業時被破格授銜中尉,又被保送到蘇聯留學。那正是中蘇意識形態極為敏感的60年代初期。秋哥在莫斯科堅守著祖國的信念和期盼,曾作為留蘇學生代表在大使館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

那天大家爭著靠近周總理,秋哥便站在了使館首長一起(二排左一)
他還勇敢地參加過紅場反修示威,其間,哥有一次歸國探親。也就在此時,秋哥有了一份無與倫比的福分:我有了一個美麗、賢惠、能幹、負重的大嫂。反是我哥,他“外勤內懶”,重事業而不喜歡理家。最糟的是,他身體不好。
秋哥回國後,與我嫂子在西安工作過一段時間。文革後期,他調到北京工作。
在我的一生中,他從不間斷地以大哥身份教誨我,影響著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現在寫到這裡,我不禁又淚水難忍……
我第一次到北京找到他時,他住在北河沿大街、一個破舊的大雜院裡。和前後夾著的王府井、故宮形成極大對照。一間簡陋的主室和倚此搭蓋的貧寒的“偏刷”,擠住著他一家四口。這就是當時共和國的國防科研人員。他們就這樣為我國的強大貢獻著自己的青春。
(四) 秋哥與疾病鬥爭的那些年
從我哥三十多歲起,就不幸被各種頑固可怕的不治之症圍攻。他的血壓經常高達200以上,進入四十歲以後,他四肢開始浮腫,行動充滿病態,心臟、腎臟……身上所有的器官都冒出可怕的致命疾病來,“病危通知”像訂購的報紙一樣,源源不斷飛到他的家中。讓我的擔憂從心頭噴出:我富有才華的哥哥,當一片明亮的天地在你成熟和年富力強的歲月裡出現時,你怎麼竟會這樣?這到底是怎麼了,秋哥?
今天回憶到這裡,我又要說:我哥又是幸運的,因為他娶到了世上最賢惠、最盡心的嫂子。也就是那年,我第一次見到了敏麗姐姐。她那時不到四十,因勞累已經明顯有些憔悴。但我在京短短几天,就看到大哥的福分了。敏麗姐無怨地擔起著我哥一生無微不至的看護。她包攬下了所有的家務活,承擔兒女的瑣事,當時,這位駐京科研人員的妻子,還為家裡做著一套套的木匠活!他們簡陋的家中,唯有她親手做的傢俱最為耀眼。
我哥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文革的折磨把我的身體徹底搞垮了。七十年代初,我的血壓一直在210/120mmhg以上,最高時達到240/140mmhg! 為了“追回”被政治運動耽誤的歲月,從七十年代初我被調來北京參加新裝備的設計研製後,我就一直(常常是揣著病假條)帶病堅持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常常是沒日沒夜地突擊趕活,幾乎完全顧不了家裡的事。有好多年,我們部隊實行‘休週末’制度:週六下午下班回家,週日中午就得離家往駐地趕,平時是不能回家過的。除了回家那一點少得可憐的時間抽空檢查和輔導一下孩子們的功課外,全部家務事都落在她的身上。到1983年夏,我自己也終於積勞成疾,被病魔‘打倒在地’,一病不起好些年。雖經醫院搶救脫險,但如果沒有我老伴後來的精心照料,不但我很可能早就撒手人寰,我們的一兒一女也絕不可能有他們志得意滿的今天!”
正是多虧了秋哥堅強的性格加上敏麗姐數十年如一日的周到照顧,讓他一次次奇蹟般地闖過重病甚至是死神關口。進入新世紀後來,我每天都在網上等著秋哥或敏姐發來的郵件,以確定他的平安(我儲存秋哥發來的郵件數千!)一旦哪天中斷,我就會打電話過去,求得放心。是的,多虧有嫂子,才讓我放下心來。這幾十年如一日的照顧,她的辛勞和心中的苦楚、在她表面堅定後面的內心委屈,我這個弟弟都能猜到!多少次危難中,我唯一寄予希望的救星就只有賢惠的敏麗姐了。我對敏姐充滿了感激之情,我承認這感恩的出發點,不能不說有些自私。也許哥哥也向我隱瞞和淡化了自己很多病痛。但不管怎麼說,沒有她,我哥的生命奇蹟是難以想象的!
因網路的發展,他與我的文字往來變得少有的頻繁。十多年前,我開始動手寫以家族經歷為原型的長篇小說《漢口老通成曾家》,他為了幫助我,及時給我講了很多我所不知道的往事。當我寫完第一部便給他傳去了電子稿後,記得那天已是深夜近12點,我都入睡了,突然接到他的長途電話。他是那麼激動,聲音顫抖,說我把他記憶中的爺爺奶奶復活了:“他們兩人在蘇州的對話,我覺得你就在他們身邊!”又反覆地說:“他們就是那樣的,我記得的外公和外婆就是那樣的!”那天他在電話中大聲抒發了一個多小時,鼓勵我把小說寫成精品。 以後一連幾天,他又給我來過多次電話。幾乎每讀完一章節都迫不及待地發表看法。他對我在書中的具體情節提出了很多他的意見,補充了很多他所記得的生活細節。他的記憶是那麼好,對我的評論是那麼認真,加上他的文學功底,對我的幫助而言,這世上還沒有一個人這樣!
為了更真實,我後來又專程沿著他為共和國的誕生走過傳奇戰鬥一生的父母年輕時戰鬥過的地方,去查詢資料,考察體驗他們的經歷。他則遠在千里對我的旅行採訪始終關注。當我聯絡上新四軍的老戰友後代和寫過他父母的作家龔桐前輩後,他與我同步分享,向我毫無保留地抒發自己作為一個革命者“棄兒”的複雜感情,讓我更深地瞭解了他。
我遺憾的是,我離開北京後他的離世我不在他身邊!
寫到這裡,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淚水,暫停……
我感謝上蒼,他的子女也都已成才,他第三代的學習又優秀耀眼。秋哥在最後的日子裡,曾反覆對我訴說他的欣慰。
回首一生,秋哥不愧是我們兄弟姐妹們的驕傲。他給了我說不盡的幫助,一直到我步入古稀,他都還不倦地教授我他的人生心得,他的政治經驗,他對世界的觀察,他對文學作品的看法……
我在心裡說:秋哥,您安心去吧!您終於擺脫了病痛的折磨,相信您在天國一定正默默注視我們,我記得你對我的期望,我會照您說的,走完剩下的人生。
我們兄弟姐妹都以有他這樣傑出、睿智的哥哥而自豪。他是解放軍坦克研究的高階研究員。我們都知道,大閱兵中看到的99A坦克,就有他的一份心血與貢獻。從我國第一代裝甲戰鬥車輛的設計研製工作他就參加了。在我國坦克穩定器教學實驗室建設中,在中型坦克初樣車研製會戰中,在一系列坦克技戰術效能指標標準的研究和會戰中,都有我們哥哥的影子,他留下了大量著述,我們為家族中有這樣一位大哥哥而感到驕傲!我對他的仰慕,早超過了親情!
願敏姐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