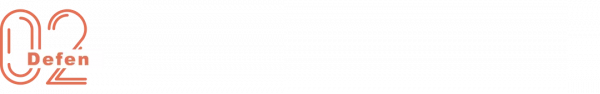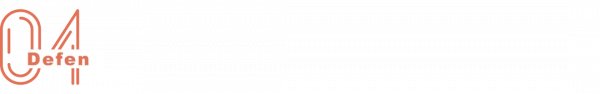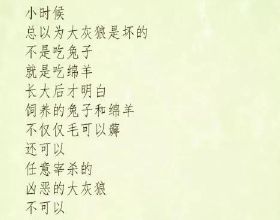豆瓣評分9.5,它輕鬆摘下包括戛納金棕櫚在內的十一項國際電影大獎。
2005年,它入選美國《時代週刊》評出的“全球史上百部最佳電影”。
這部28年前的《霸王別姬》,講透了時代大背景下兩位京劇伶人一生的悲歡離合。
無論是張豐毅飾演的段小樓,還是張國榮扮演的程蝶衣,這兩位從小一起長大的師兄弟,一人生,一人旦,一出《霸王別姬》配合得天衣無縫,更是滿堂喝彩,譽滿京華。
尤其是程蝶衣,更是達到人戲不分的境界。
他演的虞姬在臺上對霸王情深義重,慷慨赴死。而臺下的師弟對師哥,也是從一而終,別無二心。
他想跟師哥唱一輩子戲:“說的是一輩子!差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算一輩子!”
最後,蝶衣在飾演虞姬時拔劍自刎,結束了一生。
他終究明白,自己一直活在了戲中,而戲遠非人生……
“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
程蝶衣,不是一開始就這般“瘋魔”,人戲不分。
那時,他還只是一個叫“小豆子”的9歲男孩。因為做妓女的母親實在無法將他帶在身邊,因此被送到了關家戲班。
但因為他天生六根手指,被戲班主拒絕,稱:祖師爺不賞飯吃。
於是,母親將兒子的臉蒙上了衣服,用一把菜刀切下了多出的六指,尖利的嚎叫聲在衚衕裡不斷迴響。
也從此拉開了他與戲劇結緣的一生。
小豆子長得清秀俊美,是天生的旦角。學戲時,每每唱到《思凡》:
“小女子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師傅削去了頭髮。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
他總是會唱錯成,“我本身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
對小豆子來說,雖然母親是一個妓女,生存環境可能也與常人不同,但隨著生理的成長,他已逐漸感知到屬於男性的體驗,對自己的身體建立一定的感覺和認知,並表現出與男性相符合的著裝、言語和舉止。
甚至,無論被師傅怎麼毆打,他還是改不了口。
這是無意識的口誤,也是男性本身具有的倔強和力量。他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是個男兒郎,並且倔強地想要保護好自我的性別同一性。
我們每個人的發展,都會經歷著“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換句話說,也就是個體在尋求自我的發展,比如“我是誰”“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有怎樣的理想”等方面的探索。
性別的穩定建立,也隸屬其中。
說到底,我們每個人在人生舞臺上伸展自我,必得先有個清晰的自我。
如果自我的同一性還沒確認,無法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性別認同”等,也就很難在現實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周遭的一切如夢似幻,像虛無泡影,無法體驗到踏踏實實的人生價值和意義。
“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
小豆子的自我發展,是充滿曲折的,更是外界所有環境累加產物。
從9歲被母親拿菜刀砍掉手指開始,小豆子身體的自然完整性得不到尊重和保護,而被外界拿著標尺界定砍掉了。
旦角的外在身份以及戲班的環境,不斷地強迫他一次次進入女性的角色裡。
戲班的師傅用酷刑一次次地告訴他:你不是男兒郎,而是女嬌娥。不要雌雄不分,入了化境。
後來,小豆子在戲園老闆那爺面前又一次出錯。這一回,師兄小石頭也用一根菸管插進他的喉嚨,狠命地攪動直到嘴角出血,大聲罵著“讓你錯,讓你錯!”
這是一次重大的轉折。
如果說,師傅,關家班,那爺等人對他性別角色的逼迫是從外面進行的,那麼小石頭則真正從他的內部世界瓦解了他原有的性別認同,徹底的,乾脆的。
因為,這是小豆子被母親拋棄後,所唯一依戀之人。
這是那個學戲的歲月裡,寒夜裡給他一床厚棉被,練功時偷偷踢掉一塊壓他骨頭的磚頭,因為唱錯被毒打而一直保護他的人。小石頭,甚至是在他偷偷從戲班逃走後又重新回去的理由。
而這一回,一切他依戀的或痛恨的,周遭的一切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勢必要把他塞進“女嬌娥”的角色認同裡,不再有他自己。
終於,他張開了滿口是血的嘴巴,唱了起來:
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為何腰繫黃絛,身穿直裰,見人家夫妻們灑落,一對對著錦穿蘿,不由得人心急似火……
“人要自個兒成全自個兒”,從外界的逼迫到內心的認同,小豆子接納了自己的命運,用一種被動的、違心的、逆來順受的方式。
換句話說,真實的生命自我卻被徹底地閹割和壓抑了。
小豆子終於成了程蝶衣,一個出色的旦角。無論哪次登臺,都是眾人蜂擁追逐。世人都道,程蝶衣演活了虞姬。
說到底,這只是讓自己去符合外界的期望,滿足他人的需求,充分地認同讓別人滿意的角色。因為,只有在這樣的身份角色裡,才能得到那些尊重、讚賞、價值,還有愛。
而同時,真實的生命活力也只能被牢牢困在這個角色裡,動彈不得。
一個蒼涼的手勢,悲之,哀之。
他困在了錯誤的身份認同中
程蝶衣,在錯誤的身份認同中被困住了,成了一隻作繭自縛的蝴蝶。
他的所有情感,都投注給了師兄段小樓,無論是臺上還是臺下。
“從一而終”,是程蝶衣自己的承諾,也是對師兄的期許:“我們就這樣唱一輩子戲不成嗎?”
可是這一切,段小樓做不到。他對蝶衣說:“唱戲得瘋魔,不假,可要是活著也瘋魔……在這人世上,在這凡人堆裡……咱們可怎麼活喲?”
所以,舞臺上一演完霸王,段小樓便去了妓院找樂子,後來甚至娶了妓女菊仙。
段小樓對程蝶衣說,“你是真虞姬,我是假霸王。”真正是戳中實質。
程蝶衣的戲夢和情感,終究是錯付了。
他憎恨菊仙,認為師兄被這個女人給搶走。所以段小樓要和菊仙定親,他毫不給臉,當面搶白菊仙並甩袖而去。哪怕二人結婚後,他也堅持稱菊仙為“菊仙小姐”,而不改口“嫂子”。
這更像是一場女人和女人之間的微妙戰爭。
但菊仙的存在,並不足以壓垮蝶衣。真正摧毀他信仰的,是段小樓的背叛。
文革期間,段小樓為了自保出賣了程蝶衣。他揭發他給日本人唱戲、當漢奸、抽大煙、甚至揭發他用身體討好大漢奸袁世卿……
程蝶衣生命的所有苦痛,被當眾揭發,公之於眾。而同時,他對師兄那份從一而終的情感,如孩子般的深層依戀,也被抽走了。
生命就像一席華美的袍,裡面爬滿了蝨子。
沒有什麼奼紫嫣紅,斷壁頹垣,沒有什麼才子佳人,帝王將相。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為自己造的一場“太虛幻境”。
程蝶衣,最後自殺了,在四人幫倒臺之後。而這,恐怕是他的宿命。因為,他進入了虞姬的角色,卻沒有能力從中抽離,他的自我已和虞姬的皮肉長在一起。分離之時,就是身份的喪失,自我的死亡。
而這樣的結果源頭可能是:根本沒有一個獨立的自我。
因為將自我的稜角磨平,百般武藝地迎合、容納別人,在一個世人贊同的角色裡深度捆綁;
因為將自己所有的幻想都投射出去,在一段親密關係裡,一個理想化的人物身上得到替代滿足。
因為自己身上找不到,所以從別人身上、外部世界尋找,然後與之融為一體,來得到活著的“良好虛假感受”。
可到頭來,因為喪失了主體性,一切賺到的價值、愛、讚賞完全經不起檢驗。輕輕一碰就碎成渣渣。
唯一留下的,便是程蝶衣困在錯誤的身份認同裡過去的大半輩子。他心心念唸的,少一天、一個時辰都不算的一輩子。
人這一生的使命,是認識自己
回過頭來看,人是需要有認同角色的能力的。
程蝶衣人戲不分,充分認同虞姬的角色,所以他唱出了一曲絕世的“盛代母音”。
而我們普通人也需要這份認同能力,幫助我們在各種家庭或職業角色裡更好地遊刃有餘,適應環境,收穫成就。
但如果我們只能認同角色卻無法抽離,也會有一定的問題。
比如有些朋友說:
“他喜歡溫潤可控的女人。所以,和他戀愛時我總是讓自己看起來溫柔。但這樣的我,老是被領導說工作不夠幹練。”
“我老婆是個小學老師。可能平時訓學生訓慣了,回到家也跟我講話跟訓小朋友一樣,真讓人受不了。”
“從寶寶出生起,我的代號就是某某的媽媽。我的生活沒有自己,全部圍著寶寶的需求轉。”
生命如此豐沛和厚重,我們終究不能只活在一個角色裡,所以需要釋放那些被困住的生命能量,然後向四面八方伸展出觸角,讓它們自由流動,輕快起舞。
可以做的,有以下幾個方向:
比如,無論在生命的哪個階段,都不要放棄對自我的真實探尋,不要放棄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穩定同一性。
像山本耀司所說,讓自己去和很強的東西、可怕的東西、水準很高的東西相碰撞,然後知道“自己”是什麼。
比如,學習抵擋外界的控制,辨析內在和外在的聲音,要了解自己所認同的到底是什麼。
現在的我,所做的事,所承擔的角色,到底是為了滿足自我的需求,還是為了符合父母師長的期待?
真實的自我,又到底是怎樣的?
再比如,不斷地發展人格的獨立性,建立彈性的自我邊界,同時擁有認同和抽離角色的能力。
那可能意味著,你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收回你寄託在別人身上的幻想,減少對他人贊同角色的依附,從你我不分的融合里長出一道“門”來。
就像程蝶衣自殺之前,又唱起了當年學戲時的臺詞:
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他終於把幻想統統收回了,把男性的身份還給了自己。
在古希臘聖城德爾斐神殿上刻著一句著名箴言:認識你自己。
依我看,無論是程蝶衣還是我們,都將要沿循著這條路徑,一路向前。
策劃 | 艾米
編輯 | 餓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