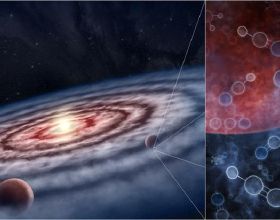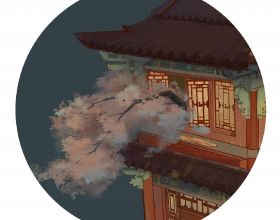加拿大作家法利·莫厄特(1921—2014)畢生致力於環保,從處女作《鹿之民》(1952)開始,包括代表作《與狼共度》(1963)等,莫厄特的作品屢獲殊榮,經常引發熱議。1981年,莫厄特獲得加拿大國家二等官佐勳章,這是加拿大最高榮譽之一,以表彰他的傑出貢獻。
《鯨之殤》講述了莫厄特親眼目睹的一頭懷孕的雌鯨死亡的故事。莫厄特竭力想要拯救她,希望幾度復燃幾度熄滅,這個迷人的巨大生物最後消逝在人間。一部憂傷但不美麗、詩意卻很殘酷的非虛構作品,喚醒人類心底尚存的良知。書中穿插講述了近代以來發達的捕鯨業與工業文明所造成的鯨的滅頂之災,這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一個族群的共同命運。
《鯨之殤》
作者:法利·莫厄特
譯者:高建國 李雲濤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6月
鯨之殤,源於瘋狂的“現代化”
捕鯨起於何時,已經無從知曉。根據美國作家基斯·A.斯韋德魯普、弗吉尼亞·安布拉斯特編著的《認識海洋》的說法,歐洲最早的捕鯨大約始於公元800年至1000年的挪威。最初法國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在比斯開灣捕鯨,16世紀初期,巴斯克捕鯨者穿越大西洋來到加拿大。他們沿著拉布拉多設立了多個捕鯨點,將座頭鯨和露背鯨的鯨脂加工成鯨油,然後穿越大西洋運回歐洲。這筆大費周章的生意之利潤極其豐厚。
在無電的時代,鯨油蠟燭的照明度和使用時間比一般蠟燭要好得多;鯨鬚由上百片有彈性的骨板組成,可以作為撐起胸衣和裙子的骨架,很受貴族女性的歡迎;龍涎香是一種從抹香鯨腸內取出的蠟狀物,與香水混合可以製造定香劑,或作為藥品;鯨肉可以潤滑輪子,也能用來清洗身體……對於鯨產品的狂熱需求,促使了捕鯨業的發展,鯨一個地方接著一個地方,一個種類接著一個種類地消失了。到了19世紀晚期,大多數海域的鯨已經減少到商業性滅絕的地步,也就是說,數量少到不具商業捕撈價值。
《鯨之殤》的故事發生於20世紀70年代初加拿大的伯吉奧群島。伯吉奧位於奧克斯·巴斯克港以東九十英里的海岸,地形險峻,鮮為人知,散居的漁民和零星的水手是僅有的人類居民。現代化席捲之處,遙遠之地不再存在,誰也難逃瘋狂的魔咒。《鯨之殤》描述了該地迅疾的工業化程序,為了方便集中“勞動力資源”,許多零散的小社群被強制搬遷,政府斥巨資修建了一個冷凍漁業加工廠,然後以荒唐的低價“賣”給了私人,聚居區變成了貧民窟,生活條件惡劣,自然環境惡化,人們對現實充滿抱怨和不滿。
這種心態是釀成悲劇的原因之一。人類的心靈脆弱不堪,被艱辛的勞作磨礪得粗糙。當人類變得麻木、失去了同情心之後,一頭受困於海灣的鯨,她面對的就將是無盡的惡意。人們企圖殺害她,牟取利益,而且百般戲弄,譁眾取寵,不斷地驅趕她,大聲喧譁笑鬧,把她作為射殺的靶子,富人駕船遊戲,窮人成了觀望的看客,莫厄特單薄的阻止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遭到譏嘲。
人怎樣對待動物,是人與人之間的預設與參照
人類為什麼虐待動物?人類為什麼相互殘殺,弱者向更弱者揮刀?澳大利亞生物倫理學家彼得·辛格曾經說過,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動物遭受的痛苦,人類對動物的壓迫是物種歧視,漠視動物的人也會漠視人類族群裡那些不幸的個體(比如殘疾人),還會恃強凌弱,甚至製造種族屠殺。哲學家阿甘本說過,無法見證和不能言說的東西是我們真正要在奧斯維辛現象中捕捉的未到場之物,人怎樣對待動物,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預設與參照,是人之為人的一個先決條件,人與動物、世界和環境的關係,標誌著一個重要領域的邊界。
導致雌鯨危境的直接原因,是她為了追逐鯡魚而不小心進入了狹窄的奧爾德里奇灣。她為什麼這麼不小心呢?因為她懷孕了,需要大量的食物,而食物的匱乏導致了她的冒險。在關注鯨的命運之時,也要關注鯡魚。這種小型魚類是海洋生物鏈的重要一環,鯡魚的消失將給其他魚類帶來飢餓的威脅。人類使用了配備高光度的圍網船來大幅提高效率,這些被捕撈的鯡魚很少用於食用,主要被製成了沒有什麼價值的魚粉,海洋生物卻因此而面臨滅絕。
人類的兇殘開發,是造成海洋生物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英國生態保護學家卡魯姆·羅伯茨在《假如海洋空蕩蕩》裡提出警告,必須注意底拖網式捕撈的危害:它將所有海底生物連根拔起,這是一種深具破壞性且造成嚴重浪費、危及今後的壞方法。人類的鯡魚船一直不停地在捕撈,而鯨只需要滿足自己食量的魚群,在可持續發展上,人要向鯨學習。
人類向鯨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鯨之殤》讓人感到痛心之處,還有鯨表現出的溫柔和安寧。與雌鯨同時受困海灣的,當時還有一條漁船,雌鯨讓出了航道,漁船得以脫離困境,然而訊息傳播引來了不懷好意的人群。直至死亡,雌鯨從未試圖攻擊人類,儘管憑她的力量,至少能掀翻幾條小船,而她只是儘量躲避,她能憑本能分辨像莫厄特這樣極少數善待她的人而親近他、接受他的靠近。這是一條長鬚鯨,她屬於一個五條鯨的群落,在她受困後,她的夥伴們隔著海灣陪伴著她,長鬚鯨的習性是一夫一妻制,有條鯨總是待在灣口,與雌鯨同步噴水、發出鯨鳴,彷彿在默默守護她,鼓勵她。
那些在成熟生物中持久存在的東西
《鯨之殤》被譽為非虛構版《白鯨》。兩部作品文筆都很出色,主題也有相似之處,都寫了作者對於鯨和海洋生態的認識,傳遞了作者對於海洋的哲思。
梅爾維爾說鯨乃至高無上之物,因為它是大洪水之前就存在的生物,彷彿具有某種古老的神性,他仔細描寫解剖鯨的細節以表明人類肆無忌憚的褻瀆。梅爾維爾藉以實瑪利之口進行形而上學的思考,進行“物化”的討論,探尋神“下降”到自然的秘密。“那些在成熟生物中持久存在的東西必定存在於胚芽中。持續不是在未來,而是在過去;來世是永恆的,因為它已經過去;雖然今天建造了一座堅固的新紀念碑,但只有當建造它的磚塊像太陽一樣古老時,它才會永遠矗立。”以實瑪利意識到大海的真正威力,不管人類如何炫耀進步,不管未來技術如何發展,即使到了天荒地老、世界毀滅之日,海洋都有能力損害和懲罰人類。
人類並非大海的異族,人類也是大海的後代。幾乎所有的族群都有類似的傳說:人類源於水,人的靈魂是一縷空氣。科學證明,人體最主要的成分是水。莫厄特在書中也寫了許多科學論據,進化稍好的鯨大腦,究其複雜程度和能力水平而言,與我們人類大腦相當,甚至更優。莫厄特寫道,鯨和人類從共同的祖先中分離而來,一個成為海洋中最高貴的生命形式,另一個變作陸地上可以駕馭一切的動物。在重新相遇時,人類展開了單方面的戰鬥,而鯨只能垂死掙扎。書中關於鯨滅絕的歷史梳理,觸目驚心。
莫厄特的書寫與孜孜不倦的努力,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興起的環保運動的一股潮流。在《鯨之殤》的後面部分,我們看到了社會輿論力量的介入。莫厄特說鯨可以作為旅遊宣傳的噱頭,他試圖以利益策略調動當地人的熱情,向新聞媒體的撒網爆料也終於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和政府的授權行動,雖然這些措施未能挽救那條雌鯨,我們終究看到了微薄的希望。
希望仍然渺茫,在書中,莫厄特的努力常常被視作可笑的、不通人情世故的滑稽舉動,但正是蕾切爾·卡遜、法利·莫厄特等個人的不懈努力,推動了20世紀中葉環保運動的興起,終於匯成洪流。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呼籲停止商業捕鯨。1980年代,國際捕鯨委員會達成了普遍協議的捕鯨禁令(日本、挪威和冰島未參加),鯨的數量目前正在緩慢回升。不過,鯨仍面臨著很多危險,大量的鯨死於傾倒入海的垃圾或被汙染物毒殺,在海洋生態沒有得到全面改善之前,所有海洋生物的處境依然很危險。
在《鯨之殤》裡,這條名叫“莫比·喬伊”的長鬚鯨沉入海洋的深處,迴歸了神秘中心。在《白鯨》裡,黃昏中,抹香鯨臨死時翻過身面向太陽,直至死亡。我們活著,活在這世上,也會陷入困境,也會遇到災厄,我們的歸宿又是怎樣的呢?有沒有太陽指引靈魂的飛昇?
作者|林頤
編輯|張進
校對|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