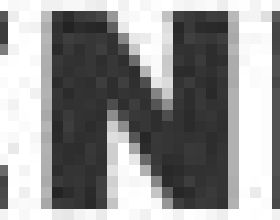從很早的時候起,人們就把成群結隊飛行的鳥看作一個整體,對它們如何做到叢集飛翔充滿好奇。群飛的鳥兒不僅展現了靈動身姿,更是炫耀了速度與協同。它們在極速群飛和急轉彎中如何做到完全協調一致?其中的秘密是什麼?
椋鳥為躲避猛禽攻擊,上演鳥浪奇觀。新疆庫魯斯臺草原,數千只紫翅椋鳥為躲避草原鷂等猛禽的攻擊在空中不停地變換隊形,時而像一隻蝴蝶,時而變換成羽毛,時而又像一隻大鳥,就像有人指揮它們在空中“作畫”一般,動作整齊,隊形有序。(許傳輝攝)
一群黑壓壓的黑腹濱鷸在沼澤地上空高速盤旋,直到有一隻灰背隼出現,它們在同一時刻轉向,黑腹濱鷸明亮的白色臀部閃爍著,以驚人的速度將隊伍重新排列成沙漏形。遙遠的天邊傳來椋鳥群的鳴叫聲,有一萬隻甚至更多,它們在地平線上遮天蔽日,像一隻舞動的水母。
鳥兒為什麼叢集飛翔
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人們就把成群結隊飛行的鳥看作一個整體,並對它們如何做到叢集飛翔而充滿好奇。古羅馬人相信,鳥類叢集飛翔是上帝的傑作,它們在飛行中被神引導,才能萬鳥如一,隨心飛行。20世紀初的科學家跟古羅馬人的觀點差不多,他們在探索鳥兒們的心靈感應,認為只有集體思維保持一致,才能共同行動。
當然,許多鳥類都會成群結隊,但是隻有少數會真正一起飛行。20世紀70年代,美國羅德島大學生物學家弗蘭克·赫普納(FrankHeppner)提出了所謂“飛行群”的概念:即高度組織的航線或叢集。鵜鶘、雁和其他水禽會形成“一”字形或“人”字形,大概是為了利用空氣動力學來節省體力。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飛鳥群應該說是那些形成巨大的、不規則形狀的群體,如椋鳥、濱鷸和黑鳥。鳥群的速度有多快?它們通常以64千米/小時或更高的速度飛行,在密集的群體中,它們之間的空間可能只比身體長度多一點。然而,鳥群可以做出驚人的急轉彎,在人類看來,動作完全協調一致。試想在高速公路上,你和周圍所有高速行駛的司機一起做出完全沒有經過事先排練的躲避動作,就能體會出這其中的艱難。
難怪觀察家們一直在尋找解釋。赫普納30多年來一直在研究群體飛行的鴿子,他認為群鳥飛翔是透過某種基於神經系統的“生物電”進行交流。
然而,如今有賴於從高速攝影到計算機模擬的技術創新,使生物學家能夠前所未有地觀察和分析鳥類群。其他學科的科學家,包括數學家、物理學家,甚至經濟學家也對這一現象產生了新的興趣。因此,研究人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群體飛行的真相。
赫普納說:“我們現在還有許多事情搞不清楚,但我認為我們正在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我們將會在未來5年內知道鳥類是如何有組織地成群飛行,以及它們為什麼會這樣做。”
反嘴鷸組團安家,編隊飛行。一群反嘴鷸在江西鄱陽湖南磯溼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飛翔,組團安家,編隊飛行。(嚴賢攝 鳥網·早起的小鳥)
落單的鳥兒更危險
從某種層面上講,成群動物集體行動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鴨子、角馬、鯡魚還是群居的昆蟲。更多的眼睛和耳朵意味著找到食物的機會增加,同時及時發現侵略者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當捕食者猛撲過來的時候,鳥群會快速作出回應。許多研究表明,群體行動中的個體在落單時,更容易受到傷害。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集體行動所造成的迷惑性。透過群體的快速旋轉或簡單的個體沿軸線上的側身,黑腹濱鷸能夠將羽毛的外觀從黑色轉變為明亮的白色,製造出一種快速的閃光效果,可能會驚嚇或迷惑捕食者。研究表明,灰背隼在獵殺濱鳥的過程中,追逐個體時最為成功。鷹隼確實會緊緊地追趕擁擠的黑腹濱鷸和其他濱鳥,但當攻擊導致一隻鳥落單時,捕獵的成功率會大幅增加。換句話說,數量意味著安全,待在一起的鳥往往會一起生存。義大利鳥類學家克勞迪奧·卡雷爾(ClaudioCarere)參與了一項在羅馬對成群椋鳥的合作研究,他認為:“落單總是更危險的。”
英國進化生物學家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Hamilton)1971年創造了“自私的叢集”一詞來描述這種現象。他寫道,每一個群體成員的行為都是出於簡單的自我利益。當捕食者接近一個群體時,群體中的所有個體都會移動到最安全的地方,即群體的中間,以減少被捕獲的危險。對幼年濱鳥的觀察表明,要掌握這一點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因為它們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學會形成有凝聚力的群體。正如它們所做的那樣,自然選擇決定了那些最不善於與群體共處的鳥最有可能被捕食者捕獲。
廣東汕頭韓江口濱海溼地的“鳥浪”。每年春季遷徙高峰期,來自澳洲及東南亞的北遷鳥兒陸續來到汕頭,在韓江口溼地這個“中轉站”停歇並補充體能,再踏上前往西伯利亞等北方繁殖地的漫漫征程。(視覺中國供圖)
群鳥飛翔來自於秩序的支撐
自身利益可以解釋許多觀察到的群體運動狀態,比如密度。但它不能解釋鳥類是如何獲得同步移動和避開捕食者所需的資訊的。群體中的每一隻鳥不可能同時看到一隻快速飛來的獵鷹。那麼,它們怎麼可能知道要朝哪個方向移動來避開危險呢?科學家們在對魚群的研究中發現了線索。海洋中許多群體物種也能像最具凝聚力的鳥群一樣複雜地活動,而且它們更便於研究,因為人們可以在開放式的水族箱中對魚群進行觀察和拍攝。20世紀60年代,俄羅斯生物學家德米特里·拉達科夫(DmitriiRadakov)對魚群進行了測試,發現如果每一條魚都能簡單地與鄰居協調行動,它們就能夠成功地避開捕食者。他描述道,即使只有少數個體知道捕食者來自何方,它們也可以引導一個龐大魚群,指揮它們的鄰居和鄰居的鄰居跟隨轉向。不同於有明確領導的列隊飛行的雁群,叢集是民主的,它們在基層發揮作用,任何草根成員均可以發起其他成員都會追隨的運動。
拉達科夫的理論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得以完善。那時計算機程式設計師開始建立模型,展示模擬動物群體如何對其內部個體的運動作出反應。結果表明,每隻鳥在飛行時,只要遵循3個簡單規則就足以形成緊密結合的群體。一是避免碰撞,二是保持速度一致,三是與同伴往相同的方向移動。將這3個特性輸入到計算機模型中,就可以建立任何你喜歡的生物的“虛擬群”。它們可以改變密度,改變形狀,並像現實世界中的鳥類一樣,在很小的空間內急速轉向。從《獅子王》到《海底總動員》,電影製作者都是使用類似的軟體來描繪和模擬大群動物的真實動作,無論是狂奔的角馬還是漂浮的水母。
角馬群橫渡馬拉河被稱為天國之渡,也是東非野生動物大遷徙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大批角馬為遷徙而渡過馬拉河,它們需要成群結隊快速過河才能躲避潛伏在河中的鱷魚。(視覺中國供圖)
然而,現實世界並不像軟體那樣執行。基礎模型的一個問題是,它不能充分解釋鳥群如何像它們那樣快速反應。這是韋恩·波茨(WaynePotts)在20世紀70年代末還在做研究生時認識到的。波茨現在是猶他大學的生物學家,他對華盛頓州普吉特灣的黑腹濱鷸做了詳盡的研究。透過拍攝鳥群的影像,並逐幀分析每隻鳥是如何移動的,他發現了一個旋轉的波紋穿過鳥群,就像體育場中觀眾所做出的人浪一樣。他給自己的發現命名為“歌舞團假說”。一個舞蹈演員在開始踢腿前等待他相鄰的同伴移動,同樣,黑腹濱鷸觀察周圍的許多鳥,而不僅僅是最近的同伴,尋找下一步動作的線索。這一發現終結了古老的心靈感應理論。
數萬候鳥在膠州灣上空盤旋覓食。深秋時節,隨著氣溫下降,越冬于山東青島環灣沿海溼地的灰斑鴴、黑腹濱鷸、白腰杓鷸等鴴鷸類候鳥叢集在海岸線,場面壯觀。(視覺中國供圖)
只要跟周圍7只鳥協調行動,百萬只的鳥群就能聚而不散
成千上萬的椋鳥每年都會成群結隊地在羅馬的棲息地過冬。每天在黃昏前,它們在昏暗的天空中,從日間覓食的鄉村橄欖樹林中飛出。正如美國自然文學作家瑞秋·卡森對有關鳥類可預測的習性所做的描述那樣,成千上萬的鳥聚集在一起,形成密集的球形、橢圓形、圓柱形和波狀線條,在瞬間改變著它們的群體形狀。椋鳥群激怒了許多居民,人們厭倦了它們留下的糞便,而也有許多人十分欣賞它們精湛的飛行表演。
“當椋鳥靠近棲息地時,它們經常會受到鷹隼的攻擊,此時它們會呈現出令人驚訝的群體行為。”卡雷爾說,“它們壓縮和分解,分裂和合並,形成‘恐怖波’—從瞬間接近的鷹隼身邊閃開,看上去十分壯觀。”
在丹麥西南部的沿海溼地,春季的一些椋鳥鳥群數量可以超過100萬隻,當地人稱他們下午晚些時候會出現“黑太陽”,鳥群會使天空變暗。但還是羅馬的椋鳥更方便進行研究,因為它們的主要棲息地之一是在位於城市的中央火車站和羅馬國家博物館分館之間的一個公園。
成群椋鳥聚集變換隊形,似神秘天外來客。2020年10月,英國蘇格蘭格雷特納。夜幕降臨前,成群椋鳥聚集在空中盤旋,變換形狀,似神秘天外來客。椋鳥成群結隊聚集在一起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降低被捕食的風險,同時還可以提高覓食效率。(視覺中國供圖)
最近的兩個冬天,來自泛歐洲合作專案StarFLAG的研究人員在歷史悠久的馬西莫宮殿屋頂上記錄了很多個小時,他們將兩隻聯動的攝像機對準成千上萬只正在表演特技飛行的椋鳥群。一些研究人員以前曾用高速立體攝影來分析鳥群整體結構,但這隻適合相對較小的群體。一旦一個鳥群超過20只,它的結構就很難梳理。“你必須說出從不同的攝像機拍攝的照片中誰是誰,而它們在不同影象中看起來很不一樣。”安德里亞·卡瓦格納說,他是一位與StarFLAG合作的義大利物理學家,“人眼很難分辨,上千只鳥時就更是完全不可能。”他們使用從統計力學領域引進的,透過檢查材料的分子結構來解釋其特性的軟體,卡瓦格納和其他物理學家現在已經能夠在不同的照片中相互匹配多達2600只椋鳥。這使得它們能夠比以前更精確地繪製出鳥群的三維結構圖。在螢幕上他們可以把眼睛看到的鳥群看作是一團圓形的堅實整體,並把它們理解為一個球體,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些更復雜的形狀,比如像煎餅、圓柱或者一個開口杯子。他們可以從任何角度審視它,並觀看它以10幀/每秒的速度改變形狀。
其結果是將可量化的觀察注入一個充滿推測的領域。透過放大三維重建,研究人員可以瞭解群中的某個椋鳥個體彼此之間的空間關係。他們發現,無論一個群體從外面看起來多麼密集,它的成員並不像網格上的節點那樣均勻分佈。相反,像高速公路上的司機一樣,每個成員的後面和前面都有很大的空間。椋鳥似乎並不介意鄰居在他們身邊或上面或下面,只要它們前面有空間。
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在飛行方向上有一條清晰的路徑,使得鳥類需要突然改變飛行路線時發生碰撞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就像被鷹隼攻擊時那樣。但是,這種空間不對稱的真正美妙之處在於,研究人員已經能夠利用它計算出每隻椋鳥密切關注的鄰居的數量—波茨“歌舞團假說”的量化闡述。透過觀察相鄰椋鳥運動之間的相關性,它們可以顯示出每隻鳥總是關注相同數量的鄰居,無論它們距離近還是遠。
那麼鄰居的數量有多少?卡瓦格納認為是六七隻。他指出,群中的椋鳥幾乎總能看到更多附近的鳥,但數量可能與鳥類的認知能力密切相關。實驗室測試表明,鴿子很容易辨別出多達6種不同的物體,但不能更多。這似乎足夠了,精神集中在一個或兩個以上的鄰居,使椋鳥能夠在需要時快速機動。但是,把所關注的鄰居數量控制在6到7個,可能會避免讓來自更遠的鳥類的不可靠的或者是過度的資訊弄得大腦混亂。
然而,它們所做的一切是否只是監視鄰居還不得而知。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幾位StarFLAG合作者一直在利用這些被密切關注的鳥群來校準計算機模型,這種計算機模型比以前任何一種分析群體行為的計算機模型都更加複雜。他們正試圖改進物理學家建立的模型,以便更準確地反映出椋鳥所面臨的真實條件,比如重力和空氣湍流。研究人員還試圖理解飛行中的椋鳥是如何交流的?雖然每個人都同意椋鳥用視線近距離導航,但這可能不是它們所擁有能力的全部。
“我認為這是聲音和視覺兩個方面的問題。”卡雷爾說,“但是沒有人知道它確切的工作方式。”他認為椋鳥甚至可以利用來自近鄰氣流的觸覺來引導它的方向。顯然,從這些最平凡的鳥兒的身上人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鳥類群飛對人類的啟發
弗蘭克·赫普納相信研究人員很快就能解釋許多這樣的謎團,即使他繼續質疑關於群體行為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設。例如,他想知道,為什麼在羅馬上空的椋鳥如此壯觀地叢集飛行了好幾分鐘才安定下來?“如果它們真的想避開獵鷹,為什麼不更快地消失?它們所做的不是在躲避捕食者,而是在吸引捕食者。”赫普納說。他推測可能是發生了某種基於數學的基本行為,物理學家稱之為“緊急屬性”。在這種情況下,整體要比各部分的總和大得多。椋鳥可能僅僅是因為它們的個體程式設計所造成的複雜行為順勢而為,比如叢集,是必然發生的。對於人類來說,應該能夠理解,因為我們知道這是簡單的生物法則,比如人類對色彩鮮豔、移動的物體產生興趣的原始本能,也會導致不可預測和明顯不合理的行為,比如千里迢迢飛到布朗斯維爾去看一隻金冠戴菊。
赫普納說:“這可能是因為這些行為就像是鳥類遵循規則的邏輯副產品。你完全有可能從可預測的規則中得到不可預測的行為。”也許羅馬的椋鳥會對人們的集體決策有所啟發。一些隸屬於StarFLAG計劃的科學家正在基於此項發現研究選民如何影響彼此的選擇,以及在某地設立新的銀行分支機構的決定是否構成了蜂擁行為的可能性。
對某些人來說,這種理解群體行為的實際應用,可能與瞭解神的意圖一樣有價值。然而它們的價值可能比確認人們是如何影響群體的價值要低。在過去的幾年裡,在羅馬過冬的椋鳥數量並沒有那麼多,但是隨著氣候變化,加上其他因素,使羅馬更適合它們生活。但隨著棲息地和食物的改變,許多濱鳥群的數量卻正在減少。
然而,最典型的群體行為啟示,可能是對理解和享受群鳥飛翔的探索。人們想知道整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但也想簡單地欣賞它。不管計算機模型如何假設,那些閃爍的黑腹濱鷸和像雲煙一樣快速旋轉的椋鳥將仍然是引人注目的景象,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會繼續表演下去。(資訊來源 《森林於人類》雜誌 PeterFriederici 撰文 選自AllAboutBirds專欄 康奈爾鳥類學實驗室授權 劉建國編譯 編輯 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