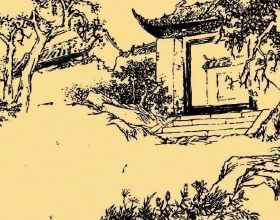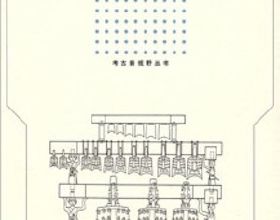來源:曲靖日報-掌上曲靖
摘要:文化,塑造了城市的品質,彰顯了城市的魅力,是城市的靈魂。爨文化是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經西晉、南北朝至唐朝天寶七年(公元748年)523年間,爨氏家族統轄雲南(當時稱“南中”)所造就的文明。文章在對爨氏政權的興亡、二爨碑和爨碑書法、爨鄉古樂、潦滸陶瓷等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提出如何挖掘、打造與定位“爨文化”。
關鍵詞:二爨碑;爨氏政權;爨文化;爨碑書法;爨鄉古樂;潦滸陶瓷
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獨特的文化。深入挖掘自己的文化資源,能夠在傳承和創新中不斷髮展不斷繁榮。文化,不僅塑造了城市的品質,展示了城市的風貌,更是城市魅力的集中體現,是城市的靈魂,決定著城市的核心競爭力。
一個地方的競爭,一個城市的競爭,核心的競爭力是軟實力,軟實力最重要的是文化。文化不能沒有根,文化的根是傳統文化,也就是歷史文化。談論曲靖的歷史文化,繞不開“爨文化”,但曲靖的歷史文化並不等於爨文化,爨文化只是源遠流長的曲靖歷史文化的重要一環。在此之前,原始社會時期,曲靖就有輝煌的文化遺存,秦漢時期,曲靖是人類歷史上開發最早的區域之一;在此之後,明清時期,掀起過文化建設的高潮;民國,也創造了一個高度。曲靖是雲南最大的革命老區,近代以來,從重九起義到護國運動,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湧現了許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曲靖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城市,說它古老是因為歷史悠久、積澱厚實,說它年輕是因為發展不快、影響不大。“爨文化”對於曲靖而言,既是一個永恆鄉愁,又是一段湮沒歷史;既是曲靖風情,又是曲靖風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在雲南文化發展史上,爨文化是繼古滇文化之後崛起於南盤江流域的歷史文化,具有上承古滇文化、下啟南詔大理文化的歷史作用。一方面,就歷史角度講,爨文化是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經西晉、南北朝至唐朝天寶七年(公元748年)523年間,爨氏政權統轄雲南(當時稱“南中”)所造就的文明,這是“爨文化”狹義的概念;從源頭上說,爨文化是中原漢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外來文化與曲靖及其周邊少數民族文化長期大融匯大雜交後開出的一朵獨具特色的奇葩(多元體、複合型文化),這是“爨文化”廣義的概念。另一方面,“爨文化”又是一個消亡得相當徹底的文化歷程,在歷史長河中恍如曇花一現,因此,也有部分史家對“爨文化”一直持否定態度。
“二爨碑”,即:“爨寶子碑”,全稱是“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墓”,俗稱“小爨碑”,立於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405年);“爨龍顏碑”,全稱是“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墓”,俗稱“大爨碑”,立於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之所以分大小,是因為形制上的大小差別。國務院1961年公佈的全國第一批重點保護文物,“二爨碑”皆在其中。天下名碑數不勝數,被列為國家級第一批重點保護的碑刻全國僅11塊(書法類7塊),曲靖佔3塊(都是書法類),極其罕見(另一塊是“段氏與三十七部會盟碑”,俗稱“會盟碑”,建於北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此碑開創了彝族與白族民族大團結之先河)。發現“小爨碑”的是曲靖知府鄧爾恆,發現時間是1852年,發現地點是麒麟區越州鎮楊旗田村;發現“大爨碑”的是雲貴總督阮元,發現時間是1827年,發現地點是陸良縣馬街鎮薛官堡村。小爨碑立碑早於大爨碑53年,卻晚大爨碑25年才被發現。小爨碑被發現之前,被一戶世代做豆腐的農家用作壓制豆腐的工具,大爨碑被當地老百姓用來“摜穀子”。“二爨碑”被發現的過程以及之後的經歷,似乎暗藏諸多天意,極富傳奇色彩。
二、爨氏政權的興亡
爨,是統治雲南五百年的一個古老家族的姓氏。爨氏,是漢族,不是少數民族。爨時代,“南中”的面積包括現在雲南的全境和四川南部、廣西西北部、貴州西部以及緬甸、寮國、越南的一部分。爨氏自中原南下,到三國後期,逐漸統轄了“南中”廣大疆域。魏滅蜀後,西晉接管了蜀國統治的“南中”,於公元271年在“南中”設立寧州,治所在味縣(今麒麟區),之前也在味縣。寧州的建立,讓曲靖成為一個文化交融發展的重要地帶。從這個時候起,作為寧州首府的曲靖,正式成了完全意義上的雲南統治中心。雲南(當時稱寧州)不再附屬四川(當時稱益州),正式成為全國19個州之一,改變了歷來為巴蜀附庸的局面。雖然三國時諸葛亮南征平定大姓孟獲叛亂後,曾廢益州郡改建寧郡,並將治所由滇池縣(今晉寧),遷到味縣,設庲降都督管轄南中七郡,庲降都督府駐地也從平夷縣(今貴州畢節)遷至味縣,但庲降都督是軍事性質的機構,不是行政機構,而寧州則是直屬中央的行政機構,這在雲南郡縣制度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自此,滇東盤江流域(“爨氏政權”)取代滇池區域(“古滇王國”)成為雲南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爨氏家族的興起,是歷史給予的一次特殊機遇,也是漢文化在這一地區長期滲透的產物。爨氏集團是“軍政合一、政教合一”的封建領主割據政權,在其統治時期,由於中原王朝處於戰亂之中,無暇顧及遙遠邊地“南中”(雲南),爨氏政權趁之採取“奉中原王朝為正朔”,實際形成“開門諸侯,閉門天子”的格局。“南中”既接受朝廷任命的官職,又保留世襲頭銜(即政治上的“雙軌制”)。東漢以來,中原長達數百年戰亂,客觀上造成對大姓勢力的放縱,導致爨氏家族雄長“南中”數百年,但爨氏十數代統治者,從未出現割據稱王或該元稱號現象,始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多民族的團結,始終沒有脫離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
“南中”戰亂較少,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出現“爨寶子碑”描述的“山嶽吐金”,“物物得所”,“牛馬被野”,“邑落相望”的繁榮景象。《新纂雲南通志》記載,當時曲靖(爨氏政權腹心區)的經濟與內地接近,“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多名馬”;“爨龍顏碑”的描述是“獨步南境,卓爾不群”(透過這8個字,可以想象當時曲靖在全國的地位、形象和影響力,那種自信、豪邁與底氣,可謂爨時代的“曲靖精神”,即:自強不息、開拓創新、開放包容、民族和諧的精神)。伴隨著大量漢民的不斷遷入,使得曲靖及周邊世居少數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文化習俗、思想觀念發生重大變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不斷滲透、相互同化,逐漸混為一體。這時的“爨文化”,嚴格說,是漢文化與當地少數民族文化融匯雜交後開出的一朵獨具特色的奇葩。正如五百年後(元朝),蒙古人踏碎精美的宋詞,日耳曼人燒燬輝煌的羅馬宮殿一樣,“南詔滅爨”將璀璨的爨文化“煙燼灰滅”。
爨氏家族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獨霸一方、據地稱雄時間最長、跨越朝代最多的家族之一。但是,為什麼爨氏政權史籍缺失難覓蹤影?為什麼爨氏後人神秘失蹤不知何往?為什麼空遺下兩塊爨碑少有其他線索?究其原因,有三種分析:一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動盪不安,始終沒有建立起統一的中央王朝,國家處於分裂狀況;二是爨氏統治區距離中央政府太遙遠,且山川險峻,中央政府無力顧及,更別說控制;三是南詔滅爨後,緊接著實行種族大遷徙,《蠻書》記載:“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北至龍和城以東,蕩然荒矣”,這種“掃地出門”的結局,讓爨氏腹心區的曲靖遭遇徹底的毀滅性災難。
隋朝建立,結束了內地兩個多世紀無休止戰亂,自然不會讓爨氏家族在南中繼續其割據局面。隋文帝兩次出兵雲南,將爨氏家族首領爨翫全家逮捕後帶回長安,處死爨翫,“諸子沒為役”(《新唐書·兩爨傳》)。但此舉未能控制南中地區,爨氏其他首領繼續據有雲南。到了唐朝建立,改變策略,將爨翫之子爨宏達放回南中,任命為昆州刺史,對爨氏控制區實行籠絡式羈縻統治。這種狀況維持了一百多年,到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爨氏內亂,爭權奪利,南寧州大鬼主(鬼主,即宗教和政治首領,既是部落直接統治者,又是神職人員、祭祀主持人。信奉“鬼教”,其實就是祖先崇拜,鬼主便是祖先的化身,能溝通天、地、人三者間的關係,具有人神參半的特殊身份。這樣一種身份,使鬼主在部落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這權力是爨氏家族賴以統治基層的神化力量)爨崇道殺了昆州刺史爨日進,又暗害了爨氏家族的主心骨南寧州都督爨歸王,爨歸王的妻子、出身烏蠻的阿奼從孃家(烏蠻部落)搬援兵對抗爨崇道,並向崛起於洱海地區的南詔求助(唐初,洱海周圍有六大部落集團,其中蒙舍詔居於南部,稱為“南詔”。從唐開元初,歷經20餘年兼併戰爭,南詔統一了洱海地區,並企圖侵吞爨區),南詔首領皮邏閣“老謀深算”,不僅為爨歸王之子爨守隅向中央政府申請襲任南寧州都督一職,達到拉攏、分裂之目的,得到批准後,還將兩個女兒,分別嫁給“冤家對頭、形如水火”的爨守隅(爨歸王之子)和爨輔期(爨崇道之子),以圖控制爨氏家族。之後,皮邏閣在唐朝縱容下、與阿奼母子配合,發兵殺了爨崇道父子,滅了諸爨領主,佔有爨區。皮邏閣將諸爨中唯一剩下的阿奼母子遷往南詔。《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蠻下》記載:天寶七年(公元748年),爨氏內訌,相互殘殺,崛起於洱海之濱的少數民族政權“南詔”的閣羅鳳(皮邏閣之子)乘機率軍攻陷石城(曲靖),佔領兩爨之地後,為摧毀爨氏勢力,命令進駐爨區的昆川(昆明)城使楊牟利武力脅迫西爨白蠻,遷徙爨區20餘萬戶、100萬人左右到滇西永昌,徹底瓦解了爨氏的統治。滇東地區發達的經濟文化遭到了毀滅性打擊,“爨文化”衰落了。遷徙到滇西的西爨白蠻,是當時雲南先進經濟文化的代表,雖被迫西遷,卻在客觀上帶去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發達的文化,與洱海區域的經濟文化相交融,經過逐漸發展,形成了新的文化型別——南詔大理文化。唐初南詔滅爨,雲南文化又成少數民族文化,從漢至唐推進了四百多年的漢文化戛然而止。
公元749年,即南詔滅爨第二年,南詔在唐朝扶持下建立南詔國,結束了爨氏政權五百年的雲南霸主地位。公元751年,唐朝鮮于仲通率師至曲靖,閣羅鳳向吐蕃求援,唐軍大敗,南詔割據雲南局面形成。曲靖失掉雲南中心地位,滇東烏蠻稱雄,促成三十七部崛起(“西爨白蠻”大量西遷後,散居山林的“東爨烏蠻”逐漸移居平地,形成若干部族,其中較大的37個,史稱“三十七部”)。爨氏在曲靖的區域性統治,一直持續到明朝中葉“改土歸流”之後,前後加起來有1300年左右。
關於爨氏家族的後代具體如何,因無明確的文獻記載,爭論較多,但可以肯定,爨氏家族並未滅絕。大理出土的“南詔德化碑”記載南詔國大臣就有爨姓,爨泰曾為南詔國學士。大理國的開國君主段思平從通海起兵時,得到舅父爨判(“三十七部”盟主)的大力支援,登極後封爨判為巴甸侯,皆有史籍可考。成都出土的一塊唐代墓誌,墓主是“襲南寧郡王”爨守忠(爨歸王之子、爨守隅之弟),時任唐朝的劍南西川節度副使、南寧十四州都督,雖是遙授和擺設,說明爨氏家族一部分歸附唐朝,並在唐朝世襲郡王爵位。爨守忠駐節嘉州(四川樂山),所領“南寧十四州”,其實就是被南詔佔領的區域。唐王朝利用爨氏家族在雲南的影響,保持對南詔國的威懾。但是,為什麼後來沒有了爨姓?顯赫一時的家族難道沒有後裔了嗎?有人認為,爨氏的後裔改姓了,因為沒有強有力證據,很多人不以為然。50年代初在大理鶴慶找到一塊明朝初年立的碑,叫《寸升碑》,敘述其祖先本為稱霸南中的爨氏,南詔大理時保有貴族身份,改為“寸”姓,曾有人擔任過大理國丞相,元代時為土官,明朝軍隊進入雲南後又率先歸附。說明爨氏家族西遷後的分佈並不侷限於保山和大理,而是很廣的。一些研究者認為:爨地被南詔佔領後,爨地的所謂爨人也發生變化,一部分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白蠻”被強迫遷移,很大一部分和洱海地區的其他部族一起,逐步形成今天的白族,留在當地山區保留本民族習俗較多的“烏蠻”,保有自己的部落組織,逐步成為今天的彝族。到了明清時期,文獻提到的“爨人”,大多指現在的彝族,而提到的所謂爨文,也是彝文了。
“南詔滅爨”後,僅從文化角度講,是“文明的中斷、文化的倒退”,就是說沒有進步反而退化了,因為南詔大理是農奴制政權,文化極端落後,一直持續到元朝都是退化。
三、爨碑書法
兩漢文章以散文和漢賦為主,魏晉之際,兩者合流,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樣式,就是六朝時代的駢體文。“爨寶子碑”的碑文,便是駢體文出現後早期的文風,駢散結合以駢為主,既有漢代散文的古奧宏麗,又有六朝駢文的綺靡華麗。“爨龍顏碑”的碑文,又演變為以散體為主,駢體為輔,散文風格極為濃厚,表現了散文復興的趨勢,這種復興趨勢的發展,到了唐朝中葉,便形成韓柳古文運動,產生了唐宋八大家。由此可見,“二爨碑”的文體出現在我國文學史發展的轉折時期,開六朝和唐宋兩階段文學的風氣之先。到了清朝後期,“二爨碑”已名滿海內外,但對“二爨碑”的欣賞,主要表現在對其書法的推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由兩漢的隸書向隋、唐的楷書演變過渡,這個過渡階段的字型,在書法史上稱為“北碑和南碑”(碑刻中的魏碑稱北碑,東晉和南北朝的碑刻稱南碑),這個時期,上至帝王下到士庶,無不以書法為其雅好。“爨寶子碑”書法是南碑的早期作品,康有為稱之“魏晉正書第一本”, 周鍾嶽稱為“南碑瑰寶”,實非過譽之辭。 多數研究者認為:爨氏時代,因遠離中央政府,對中原日漸規範的楷體尚未完全瞭解與掌握,二爨碑正好記錄了這種似隸非隸、似楷非楷的過渡書體。魏晉時期,國家幾度下令禁碑,傳世的碑帖極少,因此,“二爨碑”的出土填補了南無名碑的空白,其聲名遠播,除了書法的高古之外,發現之地也令世人驚詫。“爨寶子碑”之後53年的“爨龍顏碑”,楷書成分大大增加,但仍有隸書風味,被康有為譽為“隸楷極則”“神品第一”。阮元在《爨龍顏碑跋》中稱:“此碑文體書法皆漢晉正傳,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雲南第一古石,其永寶護之”。
“二爨碑”的外形制作、碑文與中原漢文化一脈相承,且與所處時代(東晉)“盛行老莊”的風尚相一致。“爨寶子碑”中“至人無想,相忘江湖”的思想與晉人崇尚自然、縱情山水的人生理念十分貼近。碑文讚譽爨寶子“少稟環偉之質,長挺高邈之操,通曠清格”“發自天然,冰潔簡靜”的句子與晉人注重人品氣度、喜歡浮誇虛華的審美傾向相吻合。從書法角度看,雖然沒有“爨體”這一體例,但都知道特指“爨碑”字型。如今的曲靖,無數人能寫“爨體”,各種各類的牌匾多以“爨體”書寫,成為顯著的地域特徵。
“爨碑書法”的筆畫結構在隸楷之間,兼有篆書遺姿,忽隸、忽楷、忽篆摻拌,可謂“三體合一”的融合物,因為沒有留下書者姓名,各種猜測版本流行,有代表性的是兩例:一是本地一書家,由著性子寫,歪也罷正也罷,錯也罷對也罷,方也罷圓也罷,隸也罷楷也罷,偶爾還弄幾筆篆書,所以有了“爨碑”樸拙的美、灑脫的美、醜到極致的美;二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厭世高人,書寫了得意之作,不願留下姓名,後人把碑文那種無序的排列,歪歪扭扭的結構,方圓並用的點畫運筆,狂放灑脫、剛柔並濟、動中求靜的構思,臆想為刻意為之。甚而還有人揣測碑文書寫者揮毫時的情狀,也有兩個版本在曲靖流行:一是得意之時的獨創書法。縱觀 “爨體”,既無篆書的古韻端莊,也無魏碑的典雅,更無楷書與隸書的嚴謹,神馬行空,肆意揮灑,不避醜拙,屬得意時任情潑墨、揮灑自如的酣暢淋漓之心境,這時書法的美,彷彿大家閨秀濃妝貴婦之美;二是失意之時的發洩之作。端詳“爨體”,它的魅力是原始的、野性的、蠻悍的,“爨體”的美恰恰在於它的不美或者無意去追求美,同敷粉薰香、濃妝豔抹的美不同,是不加修飾、不加雕琢,不避醜拙的野、蠻、怪的美,屬失意時憤世嫉俗、孤芳自賞的狂放悲愴之心境,這時書法的美,有如小家碧玉清純少女之美。但猜測終究是猜測而已。
康有為評論“小爨”書體:“端樸若古佛之容”“ 樸厚古茂,奇姿百出”“在隸、楷之間,可以考見變體源流”,李根源稱頌“小爨”書法:“下筆剛健如鐵,姿媚如神女”; 康有為評論“大爨”書體:“若軒轅古聖,端冕垂裳”“下畫如崑刀刻玉,但見渾美,佈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學者顧峰在其著作《雲南碑刻與書法》中說:“書法雄強茂美,參差有致,疏密相間,筆力遒勁,氣勢宏偉,像刀斧擊鑿而成,有隸書筆意,其方筆略兼圓筆,其方筆又比六十四年後的《張猛龍碑》渾厚大方,其圓筆又比五十三年後的《鄭文公碑》凝重挺拔。”
爨碑書法可謂獨樹一幟,但在當下書法界,對其價值的認可並不高。在多元審美背景下,大力推介、研究、臨摹“二爨碑”,積極塑造、包裝一批各具特色的“爨體書法家”,拓展書法藝術視域,擴大“爨體書法”影響力,構建“中國爨書之都”,最終形成標誌性、品牌性的地域書風,對於爨鄉曲靖,意義重大。
四、爨鄉古樂
現代的曲靖人茶餘飯後談論“爨文化”,無非是從散存於殘篇斷簡中的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宗教信仰、婚喪習俗、祭祀、慶典、醫藥、建築以及那些流落於民間的詩文、歌舞、音樂、戲劇、曲藝、字畫、陶瓷以及各類傳說、軼聞、野史、故事等等來進行牽強附會、生拉活扯,以尋覓其蹤影,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與證據,截至目前,仍然只有“二爨碑”等少量文物。這裡要強調的,是一個長期存在最具特色的“音樂活化石”、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曲靖洞經古樂。
每週四下午兩點後,麒麟區南城門樓上,有個古樂會,例行排練,一曲曲“此譜只應古時有”的旋律,餘韻繞樑,凝重肅穆,彷彿天籟之聲,讓人感覺時光倒流上千年,充滿飄逸的神秘感。演奏遠古聲音的,是1983年重新籌組的一個民間團體:爨鄉古樂會。當年成立時,是一個平均年齡超過70歲的團隊,最大的90歲,最年輕的50歲,成員有14人。因為人才與資金的青黃不接,古樂會從成立之初就一直傳承乏人、運轉艱難。印象深刻的是“三老”:人老、裝置老、曲子老。雖然把中斷了多年的“古樂會”陸續恢復起來,但我仍然擔憂:這千年絕唱,一不小心就真的成了絕唱,再也沒有人唱了!30多年過去了,古樂會秉持著一個十分樸素的信念,有太多心酸和不容易:不為錢,不為名,為了把老祖宗的東西(文化遺產)傳承下去!聽爨鄉古樂,彷彿來自遠古的聲音在時空深處迴響。由於時代變遷,不少洞經古樂演奏團體,在演奏時把唱詞做了改動,爨鄉古樂力圖保持原始韻味、原汁原味,即老輩人怎麼演奏,現在人就怎麼演奏,老輩人怎麼吟唱,現在人就怎麼吟唱,就與滇西、滇南的差別不小。演奏古樂的民間團體不少,但運作正常的可謂鳳毛麟角,所有古樂演奏團體,面臨一個共同的嚴峻問題:隊伍老化,後繼乏人,資金緊缺,維繫艱難。某種程度上說,爨鄉古樂是“牆裡開花牆外香”,不少外地人慕名而來,而本地人知道的並不多。雖然古樂會定時演奏,但有些自演自聽的尷尬。古樂會的成員,絕大多數是年老體弱之人,不乏帶病演出者。10年前,我陪同幾位外地人去聆聽爨鄉古樂,那天的演出,讓我們感慨感動、記憶猶新:有3位會員因病正在住院,未能參加,演出過程中,1名會員又因病無法堅持,中途退場。直到2017年7月應邀再去,欣慰的是:這支爨鄉古樂會仍然正常運轉,增添了不少新鮮血液,並有了一定的經費保障,現在更名叫“曲靖洞經古樂會”。但是,對洞經古樂的未來我還是不敢持樂觀態度,畢竟,這個民間古樂演奏團體的骨幹成員幾乎都是老年人,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
“爨鄉古樂”源遠流長、經久不衰,始於秦漢,自西晉、南北朝到隋唐,經歷代演變,至明朝洪武年間,吸收融入中原宮廷曲譜、江南樂府、絲竹管絃等流派,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公元1579年),逐漸填入《太上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等經文,始稱洞經音樂或廟堂音樂,被譽為“東方的古典交響樂”,屬雲南極具代表性的音樂品種,曲靖市各縣區都有。洞經是套在樂譜中的唱詞(即用經文作唱詞),音樂是實質,換句話說,洞經音樂的樂譜是支柱和靈魂,而唱詞則是隨時代而變遷的一種文字反映。音樂分為“經腔”和“曲牌”,有唱詞叫“經腔”,是經文中的韻文部分,和詩詞相近,“曲牌”即曲調,主要用於各種禮儀活動時的配樂,也作經腔的間奏。洞經音樂不同於佛教或道教唸誦經文的聲腔,完全按照傳統的五聲調式和七聲音階的韻律發音並進行演奏。演奏洞經音樂的樂器,主要分為管絃樂和打擊樂兩類。管絃樂,主要是笛子、二胡、琵琶、三絃、古箏、嗩吶、洋琴等;打擊樂主要是大鼓、小鼓、大鑼、小鑼、絞子、雲樂、翠鼓、罄、木魚、碰鈴等。洞經會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稱謂,有稱“會”和“學”的,也有稱“坊”、“堂”或“壇”的,有的地方還有文、武洞經會之別。1915年,時任廣東虎門中將司令的趙樾出資在家鄉(今麒麟區)辦了一個叫“寶善堂”的洞經會,傳承至今(趙樾故居位於麒麟區西門街32號)。洞經會作為一種民俗禮樂,禮,從外向內,端正人的行為;樂,從內向外,淨化人的心靈。在雲南民族民間音樂文化中,“洞經音樂”以其莊重肅穆、曲調優美紮根於廣大人民群眾中。但個人以為,無論“曲靖爨鄉古樂”還是“麗江納西古樂”,都屬漢族移民至滇“雜交變異”儲存下來、並在各個民族地區生根開花的文化現象之一,嚴格說,脫胎於洞經音樂,絕非本民族原有之文化。
五、潦滸陶瓷
位於曲靖市麒麟區越州鎮的潦滸,是一個依山傍水、風景秀麗、因陶而興的古村落,因為這裡的陶土、瓷土、釉土、褐煤等資源豐富,追溯歷史,潦滸在宋朝開始燒磚瓦,明朝製陶瓷,清朝做碗碟,民國有了現代意義的陶瓷工廠,如今,潦滸既有現代化的陶瓷企業,同時儲存著手工拉胚、柴火燒陶等傳統技藝。明清時期建成的12條龍窯至今仍可使用。一直以來,潦滸陶瓷伴隨著曲靖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燒製陶器,離不開龍窯。龍窯,是古代人用柴草、木材燒製陶瓷的土窯,因其形狀如一條臥龍而得名。中國最古老的龍窯始於戰國時期。龍窯是古代陶瓷燒製最主要的窯型。陶瓷窯爐種類繁多,除柴燒龍窯外,還有煤燒蒲蘿窯、氣燒隧道窯和輥道窯、抽屜窯等多種窯型。古龍窯依一定的地勢或坡度,用土、石、磚砌築成直焰式圓筒形的穹狀隧道,一般長約30-70米,高約1.6-2米,分窯頭、窯床、窯尾三部分,頭尾空間較小,中間最大。千百年來,潦滸人民和龍窯一起,創造了不少輝煌。最興旺的時期,潦滸有龍窯20多條,製陶作坊近200家,從業人員近3000人,全村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在燒製陶瓷。潦滸現存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龍窯和龍窯遺址有16處,仍然還在使用的龍窯有12條。潦滸現有古窯池5座,是分別建於明代的老窯、新窯、王家窯、許家窯和建於清代的沙溝窯,其中新窯長達110多米,據考證,是目前中國最長古龍窯,且儲存完整,堪稱龍窯活化石。潦滸沿襲至今的人工手工拉胚、龍窯柴燒這一古老方式,在全世界都屬罕見,完全夠資格打造中國龍窯博物館。
從元朝至今,潦滸的陶瓷生產從未停歇,不僅是滇東及滇東北區域的陶瓷生產製作中心,也是陶瓷產品的集散地和批發市場。歷經千年,潦滸的陶瓷文化沒有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反而因時間的打磨而熠熠生輝,一代代手藝人的不斷傳承和秉持,讓潦滸充溢著太多的魅力和故事。
如今的潦滸,呈現出陶瓷業、農業、旅遊業並舉,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潦滸陶的魅力,體現在龍窯柴燒後不可預測的窯變與落灰,一把有收藏價值的陶壺,必須經過千度高溫柴火燒製,而燒製一爐窯,除要消耗5噸左右的柴火,還有製陶人數十日的精心守望與殷殷期盼。潦滸不僅有手工拉胚、柴火燒製的傳統技藝,也有現代高科技的製造工藝,潦滸的陶瓷製作方法幾乎涵蓋了人類陶瓷史上各個不同階段的工藝。徜徉在潦滸古鎮,時常會遇上一些藝術家和文化人,在為那些雛形的陶瓷泥胎賦詩作畫。欣賞著一件件的陶瓷作品在匠人手中旋轉、揉捏,陰乾後透過火燒得以涅槃重生,溫暖就會湧上心頭,油然感懷於潦滸人的專注,併為他們的堅守肅然起敬。
六、結語
“爨碑”所處時代,正是中國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文化史上一個動亂年代、多事之秋,又是文化史上“百花齊放、文藝復興”的時期。這個時代以前——漢代:在文藝上趨於質樸,在思想上定於一尊,統治於儒教;這個時代以後——唐代:在文藝上趨於成熟,在思想上儒、佛、道三教支配。這個時期是中國人精神上大解放、人格上大釋放、思想上大自由的時期。
擁有“二爨碑”的曲靖以“二爨之鄉”自居,世居爨氏政權腹心區的曲靖人自稱“爨人”無可厚非,“爨文化”作為一個地域特徵明顯的文化現象存在,是不爭的事實。爨人是一個複合型的人們共同體,這與嚴格意義上的“民族”不盡相同。爨人不是由某個單一民族直接發展演化而來,而是有漢人、滇人為主包括古老族群的人們融合而成。爨人在雲南發展過程中,逐漸融有古滇人血統,並繼承以昆明晉寧為中心的滇文化,創造了爨文化,成為南詔大理文化的淵源。民間流傳爨人使用的“蝌蚪文”,如今無人識得其模樣,“蝌蚪文”被彝族認為是彝文的起源(唐朝時位於馬龍的東爨納垢部酋長後裔阿軻,歷時3年,將所創造的1840個彝文,編撰成《韙書》,因文字形似蝌蚪,被統稱為“蝌蚪文”)。爨人把蛇當作自己的神祗,把蛇看作吉祥、幸福、美麗的化身,蛇崇拜在爨文化中一直佔有重要位置。在古爨人後代彝族支系撒尼人中,有一個世代相傳的悽美故事流傳於曲靖及周邊,即阿詩瑪與阿黑的故事,用詩的語言敘述了勤勞、勇敢、善良、美麗,“貧窮卻不為富貴所動”的男青年阿黑和女青年阿詩瑪之間的不幸愛情和悲慘命運。“阿詩瑪”,漢義即“蛇女”的意思,而蛇女則是古爨人崇拜的圖騰。撒尼語“詩”即“蛇”,“瑪”即女孩之意,且阿詩瑪是“蛇年蛇月蛇日出生”,集吉祥、善良、美貌於一身的撒尼美女。
往事已經流逝。很多人知道大理段氏,但很少有人知道比大理段氏更古老、存在時間更長的曲靖爨氏;很多人聽說過“麗江納西古樂”,但很少有人知道比“麗江納西古樂”還要古老的“曲靖爨鄉古樂”。
“爨文化”的致命悲哀在於:研究來研究去,依然只是兩塊爨碑及少量零散史籍。要認真思考的是:開創了雲南五百年曆史的曲靖,應賦予它怎樣的內涵?或者說要如何提升、打造它,怎樣去挖掘、定位,給它塑造和秉持一個什麼樣的城市靈魂呢?
主要參考文獻:
[1]西漢·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
[2]南朝·宋·范曄:《後漢書》
[3]西晉·陳壽:《三國志》
[4]東晉·常璩:《華陽國志》
[5] 唐·樊綽:《蠻書》
[6] 北宋·宋祁、歐陽修、範鎮、呂夏卿:《新唐書》
[7] 元·李京:《雲南志略》
[8] 明·諸葛元聲:《滇史》
[9] 明·張紞:《雲南機務鈔黃》
[10]清咸豐《南寧縣誌》
[11]清·鄂爾泰:《雲南通志》
[12]民國·周鍾嶽、趙式銘:《新纂雲南通志》
[13]民國·劉潤疇:《陸良縣誌稿》
[14]範建華:《爨文化論》
[15]梁曉強:《南詔史》
[16]楊蓴:《三碑點校註譯》
[17]《曲靖陶瓷史》(王啟國編著)
[18]《阿詩瑪》(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版)
[19]《二爨》(成明編著)
備註:寫於2009年,修訂於2017年,該文中部分內容曾刊發於《曲靖日報》
作者簡介:戴興華,工作於曲靖市委黨校,著書三本,發文近百篇,研究方向為曲靖地方史與民俗文化。
本文來自【曲靖日報-掌上曲靖】,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資訊公共平臺提供資訊釋出傳播服務。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