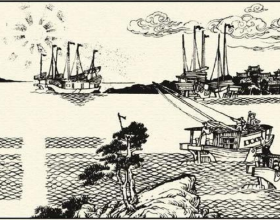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特別是春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孔子、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鬼谷子等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如群星閃耀,一時瑜亮。
漢朝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漸漸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按我的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後來,有兩個很大的特點:
一個是家國情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另一個是琴棋書畫,修心養性陶冶個人情操。
尤其是隋唐以來,因為大力推行科舉考試,使得一大批文人得以做官,讓文人實現了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也使中國的社會結構呈現了另一個顯著的特點。
這個特點就是使社會結構呈現了“士農工商”的排序。
讀書做官排在了第一位,而經商辦實業排在後面。
當時的商人被鄙視到什麼程度呢?
舉個例子,詩仙李白,天縱英才。大唐的科舉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考寫詩,以李白的水平,如果去參加考試,估計不是第一,也必進前三。
可是很不幸,李白沒有資格參加科舉,為什麼呢?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大商人。
儘管家財萬貫,但他父親也無法給李白換來一張參加科舉考試的准考證。
所以中國傳統文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瞧不起商人,認為無奸不商。
進入現代社會後,商品經濟已經滲透到了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
經濟學成為現實生活中一門重要的學問。
改革開放後,我們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經濟學思維對很多人來說是非常匱乏的。
今天我就借一首古詩,來談一談文人和商人的世界有什麼樣的不同。
這首詩名叫《蠶婦》。
在我讀書的時候,是進入教科書的。
寫這首詩的作者名叫張俞,宋代人,原詩如下: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翻譯一下是:一個養蠶的農村婦女,難得地去了一趟城裡(如果經常去,她不會有這樣的感觸,也許找個機會就留在城裡了),她看到城裡的富人,都穿著絲綢衣服。但那些富人是不養蠶的,而作為養蠶人的她,卻穿不起絲綢。於是她回到家裡後,覺得非常的委屈,大哭了一場。
詩人張俞顯然是一個傳統文人,文人天然對底層的人抱有同情心,而且這種同情心是相當感性的。
反過來說,如果他的同情心是理性的,那就不可能寫出這樣流傳千古的詩。
他透過這個現象,認為社會是不公正的,所以為底層的百姓疾呼。
這種品質是中國傳統文人的良心,如果他視而不見,如果他不大聲疾呼,他自己都會和自己過不去。
類似的情形還有很多,比如同樣是宋朝的梅堯臣寫的《陶者》: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
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
也是同樣的意思。
除了文人士大夫階層有這樣的認知,民間也廣泛流傳著這樣的觀念,比如有一句俗語:木匠睡的沒張床,瓦工住的破瓦房。
這些視角,都是傳統讀書人的視角。
以經濟學人(商人)的視角來看《蠶婦》這首詩,又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經濟學人(商人)會從一件絲綢衣服到底是怎樣生產出來的角度,來分析這首詩。
首先當然是要養蠶。
但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蠶絲賣給蠶販子,再由販子賣給作坊主,然後組織工人繅成生絲(現代企業稱之為白廠絲),然後編成絲綢,再送到染坊去染色,染色之後印花;印花之後要整理,之後還要設計剪裁,最後才變成穿在城裡有錢人身上的一件絲綢衣服。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做一件絲綢衣服,牽涉了諸多的工種以及大量勞力。
而養蠶,儘管是第一環,非常重要,但僅僅是這其中的一環而已。
從經濟學角度,一句話概括就是,養蠶的農婦是做不成絲綢衣服的。
因為既沒有這個能力,也付不起這樣的成本,所以蠶婦穿不起絲綢衣服是很正常的,不能簡單地歸結到社會不公上。
這麼一分析,如果同意這個觀點,那麼詩人張俞的同情心就“一錢不值”了。
在詩人的眼中,或者說從詩中的表達來看,好像絲綢衣服是養蠶的農婦直接生產出來的,而其他所有工種所付出的努力和收穫的報酬,都被忽略了。
其實在商人看來,每一道工序都透過自己的付出,使得本來便宜的蠶絲一步步地變成了昂貴的絲綢衣服,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工種都獲得了自己應得的酬勞(當然,這裡也許有不公平的因素存在,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產業鏈)。
所以從商人的經濟學角度來看,詩人的邏輯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