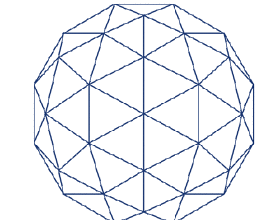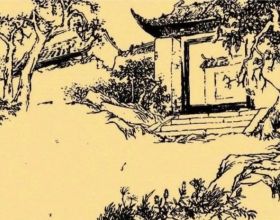劉遠鵬
全文2400餘字,讀完約5分鐘
臺灣作家李昂在小說《殺夫》中為我們描繪了一起慘案。主角林市是一個傳統社會下的悲劇女性——母親因飢餓瀕死,被迫與闖入村子計程車兵發生關係以換取兩口飯糰,被發現後遭到“宗法處置”——林市自己則被當做“肉票”,半賣半送“嫁”給了屠戶陳江水,最後因不堪忍受虐待,奪過豬刀,用物理手段“解構”了面前的“男性主體”。
這是一部極富現實感的小說,它不以跌宕情節取勝,也不存在宏大敘事,有的只是 “飲食男女”的生活真實。陳家飯桌,幾乎是整場故事發生的場景,關於“吃”的種種對抗與交鋒,更是基本串起了所有情節。李昂說,“《殺夫》是吃不飽的文學。”
小說中的兩個要點“飲食男女”,可以很好地幫我們理解傳統中國宗法觀念影響下的社會。從一個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悲慘遭遇,我們可以看出社會深層的傳統性別秩序。
▲ 《殺夫:鹿城故事》封面 臺北:聯經出版,1983
▌飲食秩序
在中國傳統社會,飲食不僅是生存的必然需求,更有其獨特的衍生意義。臺灣學者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提到,中國民眾對“吃”的態度與歐美國家截然相反,歐美人進食“只是給自己的身體加燃料”,但對於中國人,進食與生存的關係被顛倒,生存的意義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吃。考古學家張光直也認為: “食物和吃法,是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核心之一,也是中國人精神氣質的組成部分。”
因此,飲食秩序也就重要到足以折射出尊卑光譜。春秋時期鄭國公子宋就因僭越染指國君鼎中鱉羹而招致殺身之禍,夫妻之間這個秩序也違背不得。陳家的飯桌上,陳江水總是先坐下來吃飯,林市站在一旁伺候,待丈夫吃飽喝足,才能吃殘羹冷炙。
從近年的網路輿論中可得知,這種“女人吃飯不上桌”的觀念,至今仍盤踞在眾多家庭的飯桌之上。家族聚會,常常是男人圍坐在屋子中心,縱情喝酒、放聲交談,話題總是離不開政治博弈或經濟交鋒,好像他們剛從北京或華盛頓歸來;女性則往往縮坐在角落,一邊照顧幼兒,一邊交流家長裡短。
▲ 林市在疲憊地洗碗。 電影《殺夫》
這種經由飲食而確立的秩序,經過了漫長的流變和發展。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秩序在傳統禮法中佔據了重要地位,被用作一種手段規訓著帝國的臣民,一直滲透到家庭和夫妻關係之間。被視作婚姻生活典範的“舉案齊眉”,出自《後漢書》中梁鴻和孟光的故事:“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傳統社會中,儘管女性在家庭承擔著烹飪的性別分工,也並不代表她擁有了廚房的主導權。
比如,“祝福”是一項極其神聖的祭祀儀式,像《祝福》中祥林嫂這樣“不潔”女人經手獻給神明的食物,無疑是對儀式的玷汙,所以“祥林嫂,你放著罷”;李安《飲食男女》里老朱對家庭廚房的絕對主宰,則象徵著他在家庭中不可撼動的主導角色;而陳江水殺豬的過程,其實也隱喻著一種對生命的暴力和統治。神聖、主導的部分,從來是屬於男性的——這從日常飲食行為就開始建構起的一套穩固的尊卑秩序,實現了社會對女性的“規訓”。
▲ 退休國宴大廚老朱正在為子女做飯。電影《飲食男女》
▌夫妻秩序
許多讀者會認為,《殺夫》中的屠夫陳江水,對女性沒有一絲一毫的關愛和尊重,是個徹頭徹尾的“厭女者”。
這顯然忽視了李昂在小說中安插的一個重要情節:陳江水因林市的月事而“觸黴頭”,遂前往鎮上“來青閣”去探望風塵女子金花。
對金花,陳江水充滿溫情:當得知金花要回夫家生活時,對她昔日在夫家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憤怒並打抱不平,發自內心地擔憂她的未來的日子。
在金花面前,陳江水甚至顯得安分守己,他安靜地枕在情人的身邊,耐心地講述著早已說過多遍的童年往事。
這與陳江水對林市的殘忍施虐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在兩個女性身上似乎分裂出兩種矛盾的人格:其一是殘忍蠻橫的施虐者,幾近將自己的妻子視作奴隸,其二卻是溫存體貼的親密愛人,對情人充滿溫情和愛意。
這樣一個矛盾的男性形象,是許多傳統宗法家庭的真實寫照。婚姻,只是一種無法逃避的義務,和對家族延續應盡的責任。
孫隆基認為:“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中國,一個人是不完整的,他甚至都不能構成存在的單元,沒成過家的單身漢、瘋子等等,他們會被排斥在家族體系之外,或者被忽視得厲害。必須結婚生子構建一個完整家庭,才會構成一個被尊重的獨立單元。”
因此在傳統婚姻當中,愛情的缺位簡直理所應當。《殺夫》中的林市,婚前甚至從未見過陳江水,只是因為親族長老的授意,便並非出於自身意願地將一生託付給了這個男人,照顧他的飲食起居,為他繁衍後嗣,而丈夫為維繫夫妻尊卑秩序而施加的暴力,甚至被歷代王朝的司法實踐加以認可和鼓勵。
秦朝透過立法確定了丈夫對“悍妻”的懲戒權,漢代進一步規定,只要“非以兵刃也,雖傷之,毋罪。”明朝對家庭暴力的寬容甚至達到了無視生命權的地步——明律條文:“凡妻、妾因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殺死者,杖一百。若夫毆罵妻、妾,因而自盡身死者,勿論。”
可以說,丈夫對妻子的欺凌,不單單是男性憑藉個人意志對女性實施的個案暴力,更是整個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規訓。女性做飯不合丈夫心意、意見與丈夫相左,乃至對丈夫露出不滿和慍怒,都被視作對父權尊嚴的挑釁和宣戰。作為人倫綱常在基層社會的施行者,為夫,自然“理所應當”懲戒這種“忤逆”行為。
而對“愛情”的追求,則需要到婚姻之外,尤其是青樓去尋找,正如陳江水與金花的關係。
《殺夫》中陳江水對林市的暴力,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性格缺陷,他不過是響應了父權制社會下對男性的“期許”,扮演了“應有的丈夫形象”。
到最後,他用來脅迫林市的屠刀——這把父權家庭鍛造的“雙刃劍”,在林母的靈位前,被林市轉而拿起砍向了他自己。小說的高潮佈設在這樣一個充滿習俗色彩的場景中,既象徵著林市為母親的復仇,也暗含了對以父權制為核心要義的宗法關係的反抗。
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透過受教育權和就業權的普及,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是,在表面上的男女平等外,我們仍然能在社會的深層結構中發現傳統宗族秩序的幽靈。正如《殺夫》所展現的,在許多細微、易被忽略之處,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仍然存在。比如14歲的奧運冠軍全紅嬋因其“光宗耀祖”的成就,被“恩賜”載入族譜,即使身處2021年,女性仍然只有在成為奧運冠軍之後,才能擁有男性一生下來就擁有的待遇。
頭圖來自張藝謀導演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電影中的“掌燈錘腳”同文中介紹的飲食一樣,都象徵著傳統宗法家庭對女性的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