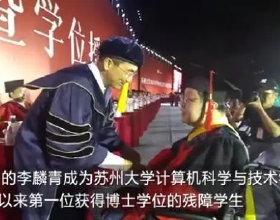葉聖陶先生是現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學家、新中國語文教育的奠基者,與呂叔湘、張志公一起被尊稱為“語文三老”。葉聖陶先生投身教育工作70餘載,他的“五論”(學生本位論、生活本源論、實踐本體論、習慣本旨論、工具本質論)教育思想源自實踐、博大精深,自成體系。“凡為教,目的在達到不需要教”“教師之為教,不在全盤授予,而在相機誘導”“語言文字的學習,就理解方面說,是得到一種知識;就運用方面說,是養成一種習慣”……葉老留下的許多教育名言被廣為引用,今天看來,對於推動中小學教育教學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葉老還有一句話影響很大,那就是“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一些語文教師或教學研究者常引用這句話來闡釋自己的觀點,但筆者發現,有些人對葉老這句話存在誤解甚至曲解,與葉老的原意往往背道而馳。
葉老當過中小學語文教師,也當過大學語文教師,新中國成立之前與之後累計編寫過17套小學和中學語文教材。“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絕非葉老一時心血來潮之語,而是他一以貫之的教育思想。據查證,早在1945年,針對當時語文教育中存在的種種弊病,葉老在《談語文教本——〈筆記文選讀〉序》一文中正式提出“語文教本只是些例子”的說法。1978年3月,粉碎“四人幫”後的中國百廢待興,在北京召開的一次語言學科規劃座談會上,葉老在題為《大力研究語文教學,儘快改進語文教學》的發言中指出:“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憑這個例子要使學生能夠舉一反三,練成閱讀和作文的熟練技能。”現在大家普遍引述的語文教材“例子”說,主要起源於此。
葉老當時的講話是對十年動盪給語文教育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的撥亂反正。拋開特殊的時代背景,今天,站在新一輪課程教學改革的角度,我們該如何理解“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這句話?
深刻認識“例子”的作用和價值
“無非”亦即“不外乎”“只不過……罷了”的意思。從字面意義和日常語言表達習慣出發,一些人由此得出教材不重要的結論,從而輕慢教材、忽視教材,認為教材“可有可無”,教師在教學時“可用可不用”。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葉老自己對這句話的內涵有明確界定:這是“說語文教本的性質跟作用”(《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第183頁)。說教材是例子,絕不是指對待語文教材的態度。
我們在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時會發現,這些學科教材的編寫邏輯,總體上是演繹式的(當然,在匯入某些知識、講到某些知識的形成時也會用到歸納的思維方法),以學科的理論知識體系為統率,依照一定的內在邏輯,分章節展開。在這些學科的教材、教學中,也有很多“例子”,但這些“例子”的主要作用,一是幫助加深對某個概念、定理、公式的理解,二是應用所學知識去解決相應的問題。而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邏輯是歸納性的,需要教師和學生透過一個個“例子”,也就是一篇篇課文,去學習、思考、總結出一些語文學科的知識來。因此,語文學科的“例子”(課文),是語文知識的“載體”,是學習的“憑藉”,離開了這些“例子”,語文學習就無從談起。由此觀之,語文教材的“例子”,其功能、作用和價值,比數理化等自然科學學科教材中的例子(舉例、例題)大得多,二者不可相提並論。
有人可能會說,為何中小學語文不能像其他學科一樣,基於學科的系統性和概念體系進行內容分解,按照章節和知識的邏輯體系來編排呢?筆者想這個問題包括“語文三老”在內的眾多教育專家肯定都曾想過,但是自語文學科誕生百餘年來,每冊語文課本由若干篇課文組成的體例沿用至今未變,定然有其道理。字、詞、句、篇、語、修、邏、文等方面的語文知識,需要學生依託具體的載體和情境去體會、感悟,由“一”而“三”,由感性認知到理性總結。知識隱於課文中,這不僅是由語文學科獨特的性質、地位、功能和學習方式決定的,也是順應兒童青少年母語學習思維發展規律的要求。
體會“例子”選取背後多方面的考量
對“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的另一大誤解是認為語文教材的選文具有隨意性——既然課文只是“例子”,用哪個“例子”不用哪個“例子”,有那麼重要嗎?
長期以來,社會各界對於語文教材的選文高度關注,中小學課本中多了哪篇文章、少了哪篇文章,往往會成為大眾關注的熱點話題,乃至引發爭議。這種現象充分說明,語文教材選文茲事體大,絕不可憑個人的偏好率性而為。
多年來,語文教材的選文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髮展、創新。一些經典篇目數十年來在教材中極少缺席,成為幾代人的共同記憶,但每次教材修訂,選文總會有所增刪。這種增或刪,絕對不是隨意的,而是有著十分全面而深刻的考量。
筆者認為,“例子”的選擇至少要考慮三個方面的情況:首先,要考慮到教材建設是“國家事權”、具有體現國家意志的性質,應站在立德樹人、鑄魂育人的高度看問題。以2017年開始使用的義務教育統編語文教材為例,為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整體滲透”,在選文上,一是加強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教材中古詩文方面的內容有較大比例的增加;二是加強了革命傳統教育的內容,收錄了大量革命傳統經典篇目;三是加強了國家主權意識教育的內容,增加了一些相關篇目。
其次,要考慮文章自身的“品質”,按照統編語文教材總主編溫儒敏教授的話來說,就是要“文質兼美”,“選文既要突出經典性,又要兼顧時代性,還要重視選擇思想格調高、語言形式美、值得誦讀涵泳的作品,強調體裁的多樣性,涵蓋古今中外各種文體。”要達到上述目標,需要廣泛徵求各領域專家的意見,論證課文內容的準確性和歷史真實性,以及是否符合科學常識,經過反覆討論、斟酌,最後才能定下來。
再其次,要考慮學生的思維發展規律及不同年齡階段的接受情況,一篇課文多長、生字量多少合適,牽涉哪些語文知識,都需要站在學生的角度換位思考。某一篇文章,放在五年級可能很好,放在三年級學生難以理解,就不合適了。
由此可見,教材中的每一個“例子”都不是隨意選入的,更不能隨意更換。
用好例子,從“教教材”到“用教材教”
葉老“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這句話,當時主要是針對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教材至上論”的,那就是拘泥於教材、死啃書本,以為把課文背得滾瓜爛熟、把課文涉及的知識點講全講透,語文學習就達到目的了。這樣的弊病,在經歷多輪課改後的今天依然廣泛存在。
在語文教學過程中,如何正確對待“例子”、用好“例子”?按照葉老的說法,教材只是“舉一隅”,希望學生能學得方法,養成習慣,“以三隅反”。要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教師從“教教材”走向“用教材教”。
教材是依託,是憑藉,但不是語文學習的全部。語文是母語教育,語文教育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承載著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使命。因此,語文學習必須透過“舉一反三”,學一例而知一類,由語文課本走向更廣闊的語文天地。
要重視教材、吃透教材而又不拘泥於教材、超越教材,這對教師的專業素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師在教課本上的“一”時,自己腦子裡要先有“三”,也就是要有廣博的知識視野,要提前準備好與某篇課文相關聯的學習資源。這和我們日常說的“給學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是一個意思。
由此,筆者想到課程週刊版面上開設的“讀統編語文 品傳統文化”這個欄目。開設這個欄目,是想讓語文教師分享講授涉及傳統文化的課文時的經驗和感悟,但遺憾的是,多數教師寫的稿件並不符合要求。很多文章的前半截——“讀統編語文”寫得“很到位”,以至於寫成了對某首古詩詞或某篇文言文逐字逐句的“精講”,但由此擴充套件延伸出去的部分——“品傳統文化”,卻沒有寫出來或僅寥寥數語、淺嘗輒止。而實際上,後半截才是落腳點。
當然也有寫得非常棒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語室主任朱於國就是其中一位。比如他在寫到小學一年級的識字課“天 地 人”時,從簡單的三個字,講到古人對天、地、人的認識,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等;又比如他把教材中與數字有關的古詩詞整合起來,讓學生體會中國古代詩詞妙用數字所產生的審美效果;他把小學語文教材中寫秋天的13首詩詞聯絡起來對比分析,讓人看到同樣是秋天,在詩人筆下卻呈現出或悲愁傷感、或明豔高潔等截然不同的意境,品味秋之人生詩意。還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小語室的楊禕老師,她在詳解蘇軾的《題西林壁》時,由“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兩句詩,擴充套件到對宋詩“哲思”特點的分析。語文教師在教學時,也應這樣由此及彼、縱橫聯絡、拓展延伸,只有這樣才能既充分用好“例子”又不囿於“例子”,讓學生既見樹木又見森林;才能以“例子”為跳板,帶領學生走向更深更廣的文化世界。
從“教教材”走向“用教材教”,還包含一層意思,那就是要培養和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讓學生的認知從低階的死記硬背轉向高階的遷移應用。這就要求語文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充分尊重學生主體地位,在教學方式上注重啟發、激發,而不是越俎代庖“滿堂灌”。唯有如此,才能如葉老所說——“把知識化為自己的血肉”“化為自己的實踐”。而這,不正是當下所倡導的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嗎?
(作者:汪瑞林 系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