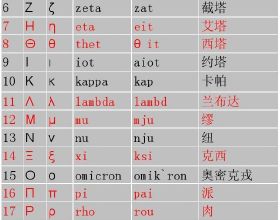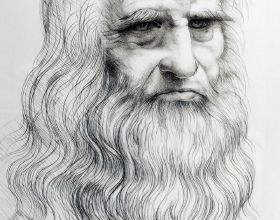我爺爺是個倔強且吃苦耐勞的漢子,從來不知疲倦,感覺不舒服也不肯就醫,最終因肝癌離我們而去。
那個我深愛的慈祥老人卒年僅62歲,很長時間我都恨自己沒有能力留住他。30年前,填報高考志願時,爺爺的面容浮現在眼前,我毫不猶豫地填寫了第一志願——首都醫學院(現為首都醫科大學),希望自己能夠攻克疑難雜症,讓親朋好友健康長壽。
5年的臨床醫學本科學習後,我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並被幸運地分配在“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朝陽醫院呼吸科工作。在這裡我接受了嚴格的呼吸專科培訓,正式成為一名呼吸科醫生。終於,可以告慰爺爺在天之靈了:我為患者解除痛苦,挽救生命!
後來,我隨恩師張傑教授來到北京天壇醫院呼吸科,經過磨鍊逐漸成為學科骨幹,把呼吸內鏡介入治療做到全國領先。此時,我也接受了一項光榮的使命——援藏。能夠在雪域高原為藏族同胞服務,我的內心很激動。
漸漸地,我感悟到,在嚴酷的條件下,生命其實更加頑強堅韌——本以為沒有先進的醫療裝置,呼吸衰竭的患者在自然乏氧的條件下不可能康復,但當出院的患者端著青稞酒致謝時,我的眼睛溼潤了;當滿是泥灰的外傷創面快速癒合,膿毒症並沒有發生時,我被震撼了……在敬畏生命的同時,我產生了新的認識:醫學的能力是有限的,自然的力量是無限的,我們探索醫學的努力應該是無窮盡的!
時光荏苒,我已在臨床工作25年,經治的患者越多越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感覺,太多驚心動魄的病例讓我們或驚喜、或惋惜,或無可奈何。
回顧自己從醫的心路,從單純地保障家人的健康到為更多人解除病痛,從醫學無所不能的認知到客觀全面地看待醫學本身。正如近代醫學大師威廉·奧斯勒所言:“醫學是不確定的科學與可能性的藝術”,世界上沒有兩副相同的面孔,也沒有兩個完全齊同的生命個體,因此,同樣的疾病也會顯現出不同病理反應和病態行為。我在成長也在蛻變,但護佑生命的從醫初衷永遠不會改變。
(本報記者崔興毅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