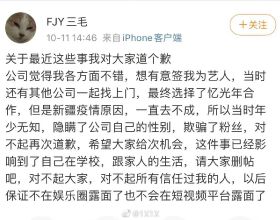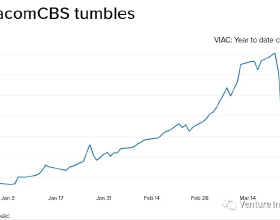前不久,在越南叢林中生活了41年的現實版“人猿泰山”何文朗(Ho Van Lang)因肝癌去世,享年52歲。
8年前,村民們在深山老林中發現了何文朗與父親何文成(Ho Van Thanh),並將他們帶回照顧。
何文朗
令人唏噓的是,這對在大自然中僅憑雙手就能荒野生存、茹毛飲血的父子,僅在現代社會生活了幾年就雙雙離世,很多人猜測是含有化學成分的加工食品和酒精害了他們……
悲劇的發生,還要追溯到半個世紀前的一場戰爭噩夢。
1972年,還在越南軍隊服役的何文成收到一個噩耗——家鄉的村子被美軍轟炸了。
顧不上任何思考,何文成日夜兼程趕了回去,沒想到母親和兩個大兒子已經被炸死,僅剩下妻子和兩個幼子。
示意圖
為了不讓妻兒再次受到傷害,何文成帶著他們躲到了安全的地方。
然而,在喪母之痛和喪子之痛的刺激下,飽受越戰痛苦的何文成出現了精神問題,逐漸展現出暴力傾向,開始時不時地毆打妻子。
何文成
後來某一天,何文成再次出現幻覺,以為美軍要打來了,癲狂的他失手把妻子打暈,慌亂中抱著還不到兩歲的何文朗跑進了森林。
恢復理智後,何文成也曾回來找過妻子,但鄰居們都擔心這個女人會被再次襲擊,於是對他謊稱人已經死了。
從那天起,心如死灰的何文成就帶著兒子一起封閉在森林裡,一待就是41年。
何文朗與父親何文成
起初,何文成和兒子何文朗也只是住在森林邊緣,隨著附近村民對樹木的砍伐,這對父子乾脆搬到了森林深處,徹底與世隔絕。
為了活下來,何文成帶著兒子逐漸摸索出了一系列生存技能。
在何文朗的操作下,“擊石取火”像動畫一樣簡單方便,乾草三兩下就被點燃。
父親在軍隊學到的捕獵技能也派上用場,把竹子做成的簡易捕夾放在草叢中,不到半天就能逮住一隻竹鼠。
用刀將竹鼠內臟掏出,然後放到火上烤,直到竹鼠渾身發黑,何文朗最愛吃的“菜”就做好了,特別是鼠頭,那是他最喜歡吃的部分。
除此之外,猴子、蛇、蜥蜴、青蛙、鳥類還有蜂蜜等都是父子倆40多年來穩定的營養來源。
吃的問題解決,再說穿。
這些年,他們身上的衣服也是自己DIY的,用刀將樹皮剝下來,再放到水裡泡軟,晾乾後再用乾草縫起來,這樣一套“手工定製”能穿好幾年。
這些年,何文朗還和父親一直收集森林中的炸彈碎片,用它們做了十多把刀具,功能從砍柴、切肉、鋤地到砍樹等樣樣俱全。
就這樣,一個只屬於父子倆的烏托邦世界被他們經營得井井有條。
離地5米高的小樹屋,
木竹做的雨衣,
吃飯、喝水用的鐵碗鐵桶……
然而,這樣與世隔絕的生活還是迎來了一場“小意外”。
還記得何文成的另一個小兒子嗎?他叫何文崔(Ho Van Tri),當年父親發瘋後帶著何文朗躲進森林裡時,他才六個月大,沒人知道為何當初他沒被帶走。
何文崔
在何文崔12歲那年,自己曾和叔叔們進入森林找到過父親和哥哥,但不管眾人如何勸說,父親何文成始終不相信越戰已經結束,甚至對自己這個小兒子沒有任何記憶,在父親眼中,他就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陌生人。
無奈,何文崔只能每年兩次去森林中看望他們,順便帶些大米、油、鹽等生活必需品。
直到2013年,幾名採蜂人進入森林後發現了這對“行為怪異”的父子,並迅速報了警。
經過5個小時的搜尋,搜尋小組終於找到了他們。
當時,何文成已經82歲,身體狀態每況愈下,在當地政府官員的勸說下,父子倆終於同意走出森林,回到現代社會。
然而,下山後的父子卻面臨著更加困難的挑戰。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叢林外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對於習慣了原始生活的他們來說,迴歸現代無異於走進外星文明。
二人融入社會的第一步就是“學說話”。
父親何文成只會說越南的少數民族語言,兒子何文朗更慘,41年的叢林生活沒接觸過任何人,而父親又寡言少語,自己只會說寥寥幾個字。
此外,穿衣服、上廁所、用碗筷吃飯、和人交流、看電視……都要一點一點學。
特別是飲食結構的改變,他們還要慢慢擺脫野味,讓身體適應加工食品的攝入。
其次,何文朗的世界觀也迎來了一次巨大的洗禮。
在他的認知中,對時間沒有任何概念,只知道天會亮會黑,而月亮,就是外面的人類用繩索掛到天上的“燈”。
性別意識更不用說,在森林生活的幾十年裡,自己總共就見過5個外人,還都被嚇得落荒而逃。直到下山後,他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不同於自己身體的“女人”。
不光如此,人與動物的和諧共處也讓何文朗十分震撼。
在村子裡,他甚至看到有些人家裡養著小貓小狗,對待它們像小孩一樣照顧。田地裡,還有人牽著水牛耕種……
在以前的森林生活中,這些活著的東西都是自己的餐中物,即便遇到體型大的物種,不是自己嚇跑它,就是它嚇跑自己。
同樣,文明社會的“社交”也困擾著他。
下山後,父子倆都住在弟弟何文崔家。某天中午,村裡兩個小孩一直在他們屋外大吵大鬧,忙於其他事兒的弟弟就讓何文朗出去,把兩個熊孩子給嚇唬走。
但在何文朗的理解中,對自己產生困擾的人就要直接“清除”,於是抄起棍子就開始瘋了一樣打,甚至轉頭還要對弟弟家被嚇哭的孩子下手。
弟弟回憶說:“打人時,他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也沒有任何情緒,就像是對待一個物品一樣。”
“如果我讓他拿刀去捅人,他二話不說就會執行,並不會思考其中的好壞,也不會意識到那個人會死。”
在弟弟的多年教導下,何文朗已經學會了一些“對與錯”的基本認知,如果現在讓你問他“殺人是好是壞?”他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壞的”。
可如果往深了問“為什麼殺人是壞的?”得到的回答也只會是一陣沉默後的微笑。
2017年,父親何文成因病去世。自那以後,何文朗就愈發孤獨,他一直覺得只有森林才是自己的家。
於是,何文朗乾脆從弟弟家搬到了距離村子四公里以外的小木屋,那裡是森林的邊緣,能聽到林間的風聲。
為了養活自己,何文朗每個月都會回到村子一兩天,賣掉逮來的田鼠,以及自己種的玉米和香蕉。偶爾,他也會幫人砍柴,但經常放下木頭就走了,根本意識不到收錢。
回小木屋時,弟弟和妻子也會往他的背籃裡塞大米和其他食物,儘可能地照顧他。
有時,他還是會進入那片和父親一同生活過的森林,在附近的溪流中洗洗手、洗洗臉,然後嚼著檳榔,看著遠方靜靜地坐著。
看著小屋周圍新長出來的香蕉,何文朗又想起了以前和父親一起吃的時候,酸酸的甜甜的。
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去年11月,某天,何文朗突然覺得腹痛難耐,經醫院檢查是肝癌晚期,已經到了無法治癒的地步。
關於病情產生的原因,醫生也無法給出確切解釋。
何文朗的一位朋友和其他村民猜測,是文明世界的壓力和飲食上的改變,一點點腐蝕了他的身體。
他的這位“朋友”是著名探險家Alvaro Cerezo,為了深入瞭解那段過去,他曾和何文朗一起回到那片森林,一同生活5天。
相處中,Cerezo用鏡頭記錄下了何文朗最脆弱、最感性的時刻。在他看來,文明社會的一切無時無刻不在壓迫著何文朗的神經,會亮的電燈泡、裝有人的電視機……都讓這個“泰山”十分困惑。
“他一生都生活在森林,然後突然來到了文明世界,開始吃加工食品甚至喝酒,我一直擔心他的身體無法應對這麼劇烈的變化。”
這點也得到了弟弟的證實,剛下山時,何文朗除了嚼檳榔、喝綠茶外,沒有別的興趣愛好。漸漸地,哥哥跟著自己學會了喝酒,但喝了段日子,他才發現哥哥對酒精過敏。
“我不讓他喝了,他還生我的氣,問憑啥我能喝他就不能喝,為了不讓他出危險,我也跟著戒了酒。”
為了適應變化,這都是他付出的“代價”。
儘管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何文朗還是表達了自己當下的願望:“我知道我病得很重,但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找到治療的辦法,我想活得久一些,看著我弟弟的孩子長大。”
遺憾的是,何文朗的願望沒能實現,他的生命停在了2021年9月。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弟弟、弟媳、侄子侄女還有其他親戚都一直陪伴在他身邊。
翻天覆地的動盪人生至此結束,或許,何文朗經歷的迷茫、孤獨和不理解比別人多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生命的最後,一直被愛包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