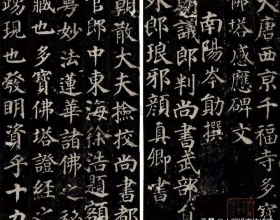壯族作家凡一平的長篇小說《四季書》發表於《作家》2021年第2期,小說講述了共產黨員韋正年傳奇的一生。
韋正年的傳奇始於1937年冬天。那一年,5歲的韋正年身患痢疾,已經奄奄一息,束手無策的家人只好將他抱到上嶺村的巖洞中等死。因為當地傳統觀念認為,死在家裡的晚輩不好投胎,還會折長輩的陽壽。但幾天後,韋正年竟然神奇地好了起來,還獲得了一種特殊的能力——能夠在黑暗中看見東西,並且比別人看得更遠。
《四季書》的故事時間跳躍幅度很大,以主人公韋正年為中心,透過插敘、補敘的形式將故事鋪展開,但這並沒有讓故事變得破碎,反而獲得了一種獨特的敘述張力。這樣的處理方式是巧妙的,如果按照固定的線性模式進行敘述,反而會顯得枯燥乏味。作者將小說分為冬、夏、秋、春四個篇章,這四個篇章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勾連,共同建構了韋正年跌宕起伏的生命變奏曲。
小說的四個篇章以季節命名,既點出了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又有深刻的隱喻味道。正如作者在小說中所寫的:“如果人生分四季,四季是四個篇章或四個籮筐,那麼他(韋正年)的人生,冬季寫的是生命,裝的是關於活著的故事。夏季寫的是自由,裝的是追求的夢想與現實。秋季寫的是愛,裝著愛人、親人與自己的情感。那麼春季的篇章寫什麼呢,春季的籮筐裝著什麼呢?死亡和骨骸。”凡一平像歸納同類項那樣,將生命、自由、愛、死亡四個重大的人生命題,分別置於四個不同的季節、不同的“籮筐”裡進行集中描繪,展現了作家強烈的結構意識,也讓讀者能更準確地把握故事的演進線索。
《四季書》給我們塑造了韋正年這個豐富飽滿的藝術形象,他當過兵、當過地方幹部,退休回到家鄉後還發揮餘熱,帶領侄兒們創辦鄉村企業。戰場上,他是英勇無畏的戰士,在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官場上,他是敢作敢為的黨員幹部,在“大躍進”時期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指出政策的問題,讓一縣百姓免於飢餓;商場上,他是光明磊落的企業家,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入獄8年,出獄後仍堅持還欠款。
韋正年的生活充滿了艱辛與坎坷,他在冬季獲得生命,在夏季獲得自由與夢想,在秋季收穫愛情,卻總是在春季遭遇死亡或戰爭。這像是一個魔咒,無論韋正年收穫多少,都會在萬物萌發的春季被清零,“死神總是春天來敲門,像是固定不變準時拜訪的客人或朋友”。1941年春天,上嶺村110口人被日本人殘忍屠殺;1952年春天,韋正年所在的志願軍38軍傷亡6700人;1964年春天,第一任妻子何菊因患抑鬱症,跳江自殺;1969年春天,第二任妻子鄭雅琴患上產後風,不幸病逝……每一個春天,對韋正年來說,無疑都是最難熬、最殘酷的季節,他不得不在春天一次又一次回憶關於死亡的事件,又不得不在春天一次又一次經歷新的死亡。
儘管遭受了種種磨難,但在韋正年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始終昂揚向上的頑強生命力。他戰勝了痢疾、躲過了日本人的屠殺,經歷槍林彈雨卻不曾受傷,想上吊自殺又因繩子斷了沒有成功。因為主張解散公共食堂、開放市場經濟,被免去縣長職務,連降三級,發回原籍當武裝幹事。但他並沒有任何怨言。韋正年是樂觀的、堅忍的,無論是仕途的不順,還是生活上的苦難,都沒有打垮他的意志。談到這裡,我們得回頭看看作者在題記中引用的那句詩:“在我身上沒有痛苦”。這句詩出自米沃什的《禮物》,我們不妨再結合詩歌的前後文來看看,“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個並不使人難為情/在我身上沒有痛苦/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與帆影。”在詩行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一種平靜的力量,不幸並非真的被忘記了,而是被消解掉了。同樣,我們在韋正年身上也沒有看到痛苦,他用共產黨人的韌性與堅定的理想信念,消解了自己身上的痛苦,獲得了內心的安寧,因而可以平靜地應對一切。當然,韋正年面對苦難所表現出來的從容淡定,與他多年的軍旅生涯也有著密切關聯。正是戰場上血與火的考驗,鍛造了他鋼鐵般的意志。
在《四季書》中,除了對生命、自由、愛、死亡四個人生命題的書寫,還有第五個命題,即:出走與迴歸。1946年的夏天,韋正年離開了上嶺村,開始追逐他的自由與夢想。這時的韋正年,也許並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但走出閉塞的大山,讓他的人生獲得了更多可能。但無論走得多遠,他始終牽掛著自己的家鄉、牽掛著上嶺村。經歷槍林彈雨、官場沉浮、商海跌宕之後,韋正年又回到了他日夜眷念的上嶺村。他像一位將軍那樣,檢閱著上嶺村的一切,他探望村中老人,給他們發紅包、和他們聊天,企圖用自己身上最後一點熱量溫暖上嶺村。當他預感到自己的死亡即將到來的時候,他又去到上嶺村後山的巖洞。他曾在這個巖洞完成了與死神的第一次較量,80多年以後,他決定在這裡迴歸大地。
韋正年的一生,貫穿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也見證了21世紀前20年新時代的社會發展變化。儘管《四季書》對於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著墨不多,但我們仍然能在小說中發現屬於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烙印。在某種程度上,韋正年是一面鏡子,透過他的人生歷程,我們看到了時代變遷的軌跡,也看到了一個忠誠擔當、擁有堅定理想信念的共產黨幹部形象。韋正年能夠在黑暗中視物,眼睛能夠比別人看得更遠,這一特異功能固然具有魔幻色彩,但也有豐富的象徵意味。能夠在黑暗中視物、行走,是因為心中有光;能夠比別人看得更遠,是因為胸懷遠大理想。
站在建黨百年這個時間節點,來審視韋正年這一藝術形象,可以看出韋正年其實是萬千優秀共產黨員的化身。100年前的共產黨人,不正是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的嗎?韋正年的成長也與共產黨員陳明倉有關,他將陳明倉視為自己的“革命領路人”。正是在陳明倉的鼓勵下,韋正年報名參軍,成為了國民黨軍隊中的一枚“棋子兵”。在青樹坪戰役中,為了讓解放軍順利突圍、減少傷亡,作為國民黨師部文書的韋正年,在傳遞檔案時篡改了長官的手令,並帶領一個連的戰士向解放軍投誠。經過組織考察後,他如願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此後,韋正年一直以嚴格的組織紀律要求自己,無論是當軍隊幹部,還是轉業當地方父母官,他都保持著剛正不阿的姿態,從來不以權謀私。但上嶺村的人以及他的父母,對此都非常難以理解。因為當上一方父母官的韋正年,並沒有讓家中的生活發生太大的改變,他的哥哥一直是農民。在困難的時候,他的4個弟弟妹妹甚至餓死了,為此韋正年的父母一直心懷怨言。
縱觀整部小說,令人稍感遺憾的是有關韋正年的“革命領路人”陳明倉的敘述過於簡單。韋正年離開上嶺村後,拿著先生樊正庭的信,投奔到陳明倉家中。陳明倉當時是國民政府柳州行政監督區稅務局局長,而14歲的韋正年僅憑藉對他的一些舉動和言語的觀察,就判斷陳明倉是共產黨柳州工委的重要人物,或許有些武斷。接下來,小說很快又跳到了3年後,陳明倉希望韋正年參軍當“棋子兵”,打入國民黨軍隊內部,並且舉薦他任國民黨師部文書。但到了部隊後,陳明倉這條線索就不見了,他作為韋正年“革命領路人”的身份明顯被弱化了。而在青樹坪戰鬥中,韋正年篡改文書、率部投誠的行為,也完全是出於自己的一腔熱血和衝動,而非來自共產黨組織或陳明倉的指點。在小說裡,韋正年固然是聰慧的,但任何一個英雄的成長都需要一個過程,淡化了這個過程,將“投誠事件”的發生簡單歸結為某種偶然性,無論是從歷史邏輯還是事理邏輯來說,都是值得仔細商榷的。
儘管有一些遺憾,但凡一平的長篇小說《四季書》仍然不失為一部優秀的作品,一部充滿隱喻的時間之書、生命之書。季節的輪轉,為小說鋪設了充滿詭譎的自然背景;時代的變遷,為小說鋪設了風雲變幻的社會背景。故事的主人公韋正年,正是在這兩種藝術底色下,完成了生命的出走與迴歸。(李富庭)
來源: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