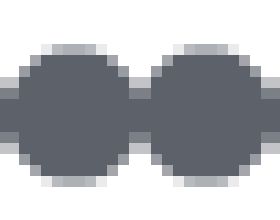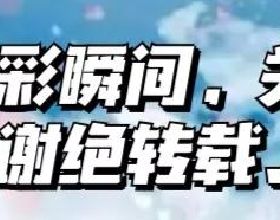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 朱康

夏爾·波德萊爾(1821-1867)像,埃米爾·德洛伊(Émile Deroy)繪於1844年。
一次是憂鬱(mélancolies),一次是憂鬱(la Mélancolie)
1844年,二十三歲的夏爾·波德萊爾感激於年長他十七歲的聖伯夫(Sainte-Beuve)的詩與小說帶來的教益,在寫給後者的信中獻上了一首詩。在詩中,波德萊爾回顧了自己“乏味的少年時光”,自十歲喝“學習的苦奶”之後所過的“麻木而疲憊的修道院似的”中學生活:在那裡,文學教育戴著傳統的枷鎖,聖伯夫的韻律遭受著教師們的反對。波德萊爾因而寫道:
幻思的季節,繆斯整整一天
都緊緊抓住一口大鐘的鐘錘;
憂鬱,在正午,當一切都在沉睡,
她一隻手托住下巴,在走廊深處,
…………
Saison de rêverie, où la Muse s'accroche
Pendant un jour entier au battant d'une cloche;
Où la Mélancolie, à midi, quand tout dort,
Le menton dans la main, au fond du corridor,
[…………]
Saison de rêverie——幻思的季節:在rêverie這一詞語的語義場中,同時匯聚著白日夢、幻想以及沉思。在這個季節裡,一段時光被定格在“正午”(midi),乏味、麻木、疲憊被歸結為“憂鬱”(la Mélancolie)。
這是波德萊爾的寫作中第一次出現“憂鬱”(mélancolie)的字眼,而他整個的詩歌生涯這時也不過剛剛有一個開端。在瓦爾特·本雅明的論說中,“憂鬱是波德萊爾的天才的營養源泉”(《巴黎,十九世紀的都城》[Paris, die Hauptstadt des XIX. Jahrhunderts]);而在讓·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的闡釋中,“憂鬱是波德萊爾親密的夥伴”(《鏡中的憂鬱》[La Mélancolie au miroir])。這首獻給聖伯夫的詩因而有了起源的意義——本雅明所說的那種起源:“在產生和消逝中正待生成者。”(《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這首獻給聖伯夫的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僅僅是私人之間的贈詩,要到1867年波德萊爾去世之後,或許是在1887年一冊以波德萊爾的遺作與未發表信件為主要內容的書裡,它才第一次從私下轉入公共的視線。從一個開端,到一個終點,從一個詩人的形成,到一個詩人的完成,一次自我的回憶,最終變成了自我的悼念。
這當然不是波德萊爾對自己少年時光的唯一一次回憶,在後來的一則自傳中,波德萊爾寫道:“1830年之後,里昂中學,打架,跟老師和同學吵架,沉重的憂鬱(lourdes mélancolies)。”——對同一段時光的兩次回憶:一次是憂鬱(mélancolies),一次是憂鬱(la Mélancolie)。這後一種憂鬱,Mélancolie,一個陰性的名詞,在一個詩句之中而首字母大寫,且還長出了“托住下巴”的手。顯然地,這是一個人格化形象,一個女性的人格化形象。由是,在波德萊爾的兩次回憶之間形成了這樣一種關係:一個懷著憂鬱(mélancolies)的男人,面對著一種作為女人的憂鬱(la Mélancolie)。
這是德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丟勒(Albrecht Dürer)的憂鬱。在1845年所寫的《1845年的沙龍》(Le Salon de 1845)裡,看著一個名為讓莫(Louis Janmot)的畫家所畫的一幅“嚴肅而憂鬱”的女人肖像,波德萊爾想起“優雅的丟勒”,並將他歸類於“德國古代的大師”。1514年,在銅版畫《憂鬱I》(Melancholia I)裡,丟勒刻下了一個坐在天平、沙漏、圓規、幻方之間,用“一隻手托住下巴”的、強健的、長著翅膀的女子。
這也是波德萊爾的同時代人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憂鬱。在《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的獻詞裡,波德萊爾稱他為“完美的詩人”,而他為丟勒的《憂鬱I》寫了一首題為“憂鬱”(Melancholia)的長詩,收於1838年出版的《死亡的喜劇》(La Comédie de mort)。在詩中,先於波德萊爾,戈蒂耶稱丟勒是“德國的大師”,並完全一致地使用了“一隻手托住下巴”這樣一個短語。雖然波德萊爾未必要透過戈蒂耶才能習得這些用詞,但至少在書寫的表面上,圍繞著丟勒,他們形成了一種彼此呼應的關係。不同的是,對戈蒂耶來說,“一隻手托住下巴”是丟勒的動作,畫中的女子是丟勒本人、是丟勒本人的憂鬱的投射。在戈蒂耶的描述中,丟勒懷著“布林喬亞的誠實”“莊嚴的沉鬱(tristesse)”,“沉鬱地幻思著(rêves)人類的命運”。這種幻思有著天使的外貌,因而他的憂鬱被人格化為“偉大的天使”:穿著“樸素的衣服”,“充滿幻思和深深的苦楚(douleur)”。
正如丟勒將自己倒映在畫裡,戈蒂耶將自己倒映在了關於丟勒的詩裡。對於波德萊爾來說,戈蒂耶對丟勒的讚頌,轉過來也是對戈蒂耶自身的呈示。在1859年所寫的《論泰奧菲爾·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中,波德萊爾稱讚戈蒂耶這一“完美的文人”屬於“偉大的憂鬱派”,“他的憂鬱具有一種更積極、更物質的性質,有時候接近於古代的沉鬱”。——戈蒂耶所說的“莊嚴的沉鬱”化成了“古代的沉鬱”。“古代的沉鬱”,一如丟勒是“古代的大師”;且又如丟勒是“優雅的丟勒”,波德萊爾從戈蒂耶的詩裡看到了“優雅的憂鬱”(les gracieuses Mélancolies),她和“純粹慾望”“高貴的絕望”一同“居住在詩的超自然領域”。
一半是現代,一半是永恆
從丟勒到戈蒂耶,三百多年間,憂鬱以同一個人格形象、同一種書寫形式(一個拉丁文的Melancholia)傳遞。對於觀看過《憂鬱I》,閱讀過《憂鬱》的波德萊爾來說,憂鬱因而成了“永恆的憂鬱”(l'éternelle Mélancolie)。在《1859年的沙龍》(Le Salon de 1859)的《雕塑》一節裡,波德萊爾寫道:
永恆的憂鬱在像她一樣平靜的池水中映照著自己的面容。幻思者從那兒經過,傷心又陶醉,望著這尊肢體強健卻因一種隱秘的痛楚(peine)而無精打采的大雕像,說:這就是我的姐妹!
這就是為什麼,在獻給聖伯夫的詩裡,波德萊爾會在“幻思的季節”裡與憂鬱(la Mélancolie)相遇,他正是從憂鬱身邊經過的幻思者。憂鬱的雕像是幻思者的——因而憂鬱是幻思的——姐妹。憂鬱是一個強健的女子,她包含著幻思,她只比幻思多了苦楚與痛楚,或者說是多了痛苦——Mal或Malheur:重要的不是它的稱謂,而是這些稱謂所標識的它的結構性的位置。正是因為這份痛苦,憂鬱被組合入另一種人格化的關係。在《焰火》(Fusées)中的一則寫於1856年的筆記裡,波德萊爾說道:
快樂(la Joie)乃是美的最庸俗的裝飾之一,而憂鬱(la Mélancolie)則可以說是美的傑出的伴侶,以致我很少考慮(我的大腦是一面魔鏡嗎?)一種不包含痛苦(Malheur)的美(Beauté)。
一方面是憂鬱和快樂圍繞美所形成的對比,另一方面是憂鬱和美透過痛苦所形成的聯姻。包含著痛苦的憂鬱在波德萊爾的大腦裡成為包含著痛苦的美,波德萊爾的大腦作為魔鏡,如同“永恆的憂鬱”用於映照自己面容的水。
痛苦是憂鬱的成分,這個大寫的、作為概念的痛苦(Malheur),同時也是波德萊爾自身的小寫的、作為體驗的痛苦(malheur)。對於波德萊爾來說,這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痛苦,在《焰火》的一個括號裡,他宣佈,正是痛苦讓他有勇氣承認他“在審美上的現代(moderne)”。痛苦關聯起現代,在這一點上,波德萊爾繼承了他的前輩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一方面,正如波德萊爾自己所追認的,夏多布里昂開創了戈蒂耶歸屬其中的那個“偉大的憂鬱派”(《論泰奧菲爾·戈蒂耶》);另一方面,在目前可查閱的文獻中,夏多布里昂第一個在法文中使用了“現代性”(modernité)這一詞語:在1830年開始撰寫、1849年才出版的《墓畔回憶錄》(Mémoires d'Outre-Tombe)中,他說到了“海關建築與護照的粗俗與現代性”。不過,與夏多布里昂在生活意義上對“現代性”作日常化的理解不同,波德萊爾則在美學層面上予“現代性”以充分理論化的解釋。在1859年寫作、1863年發表的《現代生活的畫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中,波德萊爾先將美理解為一個由“永恆的、不變的成分”與“相對的、暫時的成分”組成的“二重性構造”,然後在藝術的框架中提出了那個關於“現代性”的著名的、精微的定義:
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恆和不變。
憂鬱是美的伴侶,而藝術則是美的替身或分身。在“永恆和不變”這一藝術和美共有成分的對面,藝術之中的“現代性”置換了美之中的“相對的、暫時的成分”。波德萊爾“在審美上的現代”,對應著憂鬱之中的痛苦,因而憂鬱之中的幻思,也就指向了美與藝術之中的“永恆”。同美與藝術一樣,憂鬱也是且必須是一個“二重性構造”,它的一半是來自現代性的痛苦,另一半是對永恆性的幻思。因此波德萊爾才會在發表於1857年的《風景》(Paysage)中“雙手托住下巴”,一邊眺望“工場”“煙囪和鐘樓”,一邊眺望“那使人幻思著永恆的巨大天空”;才會在發表於1859年、獻給雨果的《天鵝》(Le Cygne)裡宣稱:
巴黎在變!可是在我的憂鬱中
卻毫無變動!腳手架,石塊,新的王宮,
老的市郊,一切對我都成為寓言,
我的親切的回憶比岩石還要沉重。
在一種計量式的關係中,回憶比岩石沉重,不變比變沉重,亦即,過去比現在沉重,永恆比現代沉重,因而,幻思比痛苦沉重。沉重,透過1859年的“比岩石還要沉重”的回憶,可以看到1844年的“沉重的憂鬱”。
一半比另一半沉重。這裡的每一個二重性構造,都不是並列、對稱、均等的組合,而是不斷髮生著從另一半向這一半的傾斜、偏轉與遷移,從另一半向這一半的運動。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波德萊爾將永恆性比作藝術的靈魂,將現代性比作藝術的軀體,於是藝術的任務便被規定為“從過渡中抽出永恆”。而這一從現代性到永恆性的運動自然同時也是從痛苦到幻思的運動。在《論泰奧菲爾·戈蒂耶》中,被波德萊爾視為“幻思者”的戈蒂耶就以其“帶有韻律和節奏的苦楚”,“擺脫了當下的現實所引起的尋常的煩惱,因而更自由地追求美的幻思”。

路易·達蓋爾(Louis Daguerre):《坦普爾大街街景》(1838),攝於巴黎,這是第一張拍到人的照片。
偉大的天使,小巧的情婦
從現代到永恆,從痛苦到幻思,藝術的二重性疊加著憂鬱的二重性,最終抵達的是美的二重性,是美本身。在《1846年的沙龍》(Le Salon de 1846)裡,波德萊爾寫道:
由於藝術永遠是透過每個人的感情、激情和幻思而得到表現的美,亦即統一體(l'unité)中的多樣性,或絕對者(l'absolu)的不同方面,所以,批評時刻都觸及形而上學。
“統一體”“絕對者”,批評正是在這些概念裡觸及的形而上學。準確地說,應該是“德國的形而上學”:在1860年發表的《人造天堂》(Les Paradis artificiels)裡,波德萊爾藉助於一個英國鴉片吸食者的經歷說到這一名稱,並列出了“康德、費希特、謝林”的名字。而正是在謝林的《藝術哲學》(Philosophie der Kunst, 1802-1805)裡,藝術諸形態被看作“絕對者中的特殊形態”,藝術本身被視為“絕對者之流溢”。
經由德國的形而上學(至少可以經由斯塔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在1810年出版的《論德國與德國人的風俗》[De l'Allemagne]中介紹的德國形而上學),波德萊爾不僅找到了藝術的位置,更是獲得了辯證的推論方式。謝林在《先驗唯心論體系》(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 1800)裡所說的以精神的機制為根基、從先驗哲學裡抽象出來的“從正題到反題,又從反題到合題的進展”,在波德萊爾《1859年的沙龍》(Le Salon de 1859)論述智慧與瘋狂關係的片段裡有一個曲折的回聲:
這正是哲學永久的反題,本質上屬人的矛盾,一切哲學與一切文學幾個時代以來就一直圍繞著這個矛盾打轉……
永恆與現代、痛苦與幻思,正是這樣的兩對屬人的矛盾,每一對矛盾中的前者構成了後者的反題,而藝術與憂鬱正是矛盾被解決之後所形成的合題:二重性構造於是變成辯證性構造,辯證性構造裡發生著辯證性運動。
辯證性運動意味著,一方面是事物的運動,另一方面是認識的運動,兩方面共同構成了概念的運動。因此,在謝林那裡,“藝術創造的東西唯有透過天才才是可能的”,而在波德萊爾這裡,藝術與憂鬱只有透過“現代生活的英雄”才成立,它需要認識的主體懷著英雄的氣概、特殊的激情、嚴峻的習慣與莊嚴的舉止從現代性“抽出”永恆性,自痛苦“追求”幻思。可是,當波德萊爾環顧自己的時代,看到的卻是“每個人的絕對而分歧的自由、努力的分散與人類意志的分裂”,看到的是少數的“卓越而痛苦的離經叛道者”與多數的“缺乏信念和天真”的“平庸之輩”(《1846年的沙龍》)。藝術的領地因而被無限地分割,憂鬱的形態因而被截然地分化。

居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繪波德萊爾像(1848)
正是在這裡,我們需要再回顧戈蒂耶的《憂鬱》一詩。而在那裡,在丟勒的憂鬱之外,戈蒂耶還寫了“我們的憂鬱”。與丟勒的“偉大的天使”相比,“我們的憂鬱”是小巧的情婦,她是一個體弱多病的年輕女郎,有著蒼白而迷人的膚色,避居於“新鮮的英國式小屋”。兩種憂鬱,它們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關係:天使的憂鬱與情婦的憂鬱,英雄的憂鬱與庸人的憂鬱,強健的憂鬱與虛弱的憂鬱,積極的憂鬱與消極的憂鬱,以及,德國的憂鬱與英國的憂鬱。
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裡有一個題為“憂鬱和理想”的專輯,專輯內有四首題作“憂鬱”的詩,更為人所周知的是,他有一部題為“巴黎的憂鬱”的散文詩集。這些在中文裡被翻譯為“憂鬱”的詞語採用的均非法語本有的mélancolie,而是來自英語的spleen,在法語裡,它是一個陽性的名詞(le spleen)。對此,讓·斯塔羅賓斯基在《鏡中的憂鬱》裡的解釋是,這是波德萊爾針對“憂鬱(mélancolie)”的泛濫化與庸俗化運用所開展的一種詩學逃避,是“求助於近義詞,求助於同義詞,求助於隱喻”所進行的一次詞語轉移。

卡洛斯·施瓦布(Carlos Schwabe):《憂鬱和理想》(1907)
轉移,從體液說到解剖學的轉移:本義為黑膽汁的mélancolie轉移為本義為脾臟的spleen。
——可為什麼是英語?
修士病,英國病
根據波德萊爾後世的同胞安德烈·勞克(André Rouch)在《懶惰的歷史》(Paresse: Histoire d'un péché capital)一書中的追溯,Spleen被引入法語文學發生在1753年,在那時,“屈服於誘惑的修士被‘正午之魔’俘虜後數百年,‘憂鬱’(spleen)這個無聊的幽靈,這個慾望的陰險敵人向我們襲來”。在勞克的敘述中,1753年引入的Spleen同奈瓦爾(Gérard de Nerval)1854年發表的《不幸的人》(El Desdichado)所表達的情緒相一致。
波德萊爾認識並熟悉奈瓦爾,他斷定奈瓦爾的一大快樂就是從流浪中“提取出憂鬱(mélancolie)”。而在《不幸的人》中,奈瓦爾的確宣稱自己是“陰暗、鰥寡、無以安慰者”,琴上刻著“憂鬱的黑日”(le soleil noir de la Mélancolie)。從這一“黑日”的意象來推論,spleen是憂鬱(mélancolie)的黑色部分,或者說,它是一種黑色的憂鬱(un noire mélancolie)。在《人造天堂》裡,波德萊爾兩次說到後者,一次直接將它與“幻思”並列,另一次則是在那位英國鴉片吸食者“將幻思的物件變成難以避免的現實”之後,那時隨之而來的便是“深深的焦慮(angoisse)與黑色的憂鬱”,空間感與時間感都被破壞,於是——
建築物與景緻的巨大外形讓人類的眼睛感到苦楚。換言之,空間膨脹到無限。可是時間的擴充套件往更加強烈的焦慮轉變……
Spleen並不是mélancolie的替代者,而只是mélancolie分化的一個結果,而正是作為這一結果,它才對應著那俘虜了修士的“正午之魔”。“正午之魔”,肇端於《聖經·詩篇》所說的“午間滅人的毒病”,在公元四世紀的修士埃瓦格里烏斯(Evagrius)的《修道》(Praktikos)裡被列入八宗罪(八惡魔),成為第六罪“acedia之魔”的別名。Acedia,在中文裡常被翻譯為“懈怠”“懶惰”,甚或是“淡漠憂鬱”。在埃瓦格里烏斯的論述中,這一惡魔在第四時(今上午十時)至第八時(今下午二時)之間襲擊修道院裡的修士,以緩慢移動乃至如同停滯的太陽讓他們體驗到時日的漫長,削弱他們的信仰和意志,從而使得他們“懶於祈禱,弛於苦行,不時地貪眠,反覆地沉睡”。

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Acedia(1558)
而只需把時間換作十八世紀,把修士換作英國人,在“正午之魔”的位置上就會出現le spleen。1733年,一位名為喬治·切恩(George Cheyne)的蘇格蘭醫生出版了一本名為“英國病”(The English Malady)的書,該書有一個長長的副標題:“或,論各種神經性疾病,如憂鬱(Spleen)、癔病(Vapours)、精神低落、疑病症式或歇斯底里式紊亂(Distempers)等”。在切恩的論述中,這些神經性疾病,是“富有者、縱樂者與懶惰者的疾病”,是“奢侈與懶惰”的產物,而之所以被呼作“英國病”,因為這正是“我們的”——“我們的”空氣、天氣、土壤、食物,“一般居民的富足與寬裕,高等人士的閒散與久坐,在巨大、擁擠因而不健康的城區裡生活的情緒”所產生的紊亂,尤其在倫敦這個“全球面積最大、容量最高、佈局最密、人口最多的城市”,“這些紊亂呈現出最劇烈、最驚人的病徵”。在這裡,Spleen與Vapours最為微妙,它們既是英國病的兩個子類,同時,包括melancholy在內的英國病的“一切病徵都被呼以Spleen與Vapours的總名”。鑑於1733年的這樣一本著作,1753年,在社會尤其在城市社會發展程度上不及英國的法國,在其語言中引入spleen也就不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同樣自然的是,1855年,在《論笑的本質》(De L'Essence du rire)中,波德萊爾直接將“spleen的霧王國”作為英國的別稱。

蓋斯(Constantin Guys):《名利場》(約1875-1885)。蓋斯被波德萊爾稱為“現代生活的畫家”。
從正午之魔到le spleen,在波德萊爾自己的表述中,也有這樣一個轉變的歷程。在獻給聖伯夫的詩裡,當波德萊爾將里昂中學比擬為“修道院”,於是馬上就出現了“正午”。他與他的同學被拋入修士般的生活,因此也必然遭受並期待“正午之魔”的襲擊:“一切都在沉睡。”一切都在沉睡,憂鬱(la Mélancolie)卻保持著清醒。於是,“憂鬱,在正午”,對於處在及回憶“幻思的季節”的波德萊爾來說,就成了憂鬱與正午的一次結合,一種對比,以及一場鬥爭。
在《惡之花》中的一首發表於1851年的《壞修士》(Le Mauvais moine)裡,波德萊爾自稱“懶惰的修士”;在《焰火》的另一則可能同樣寫於1856年的筆記裡,波德萊爾斷定“懈怠(l'acedia),修士的疾病(maladie)”。懈怠削弱或懸置了修道院對修士的絕對統治,但同時也延宕或壓抑了修士反修道院的實際行動。所以在1855年發表的《貝雅德麗齊》(La Béatrice)裡,波德萊爾做了一個道德性的評價,他把在“正中午”(plein midi)看到的惡魔稱為“兇毒的惡魔”:他們嘲笑他的“苦楚的歌唱”,並自稱是他的“這些老花招的祖師”。雖然這裡的“惡魔”是一個複數的名詞,正午之魔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個,但卻在它自身與波德萊爾之間確認了一種複雜而曲折的關係:正午之魔引導了波德萊爾的反抗,這反抗最後指向了正午之魔本身。
巴黎的憂鬱(Spleen),憂鬱(Spleen)的巴黎
在1860年發表的《巴黎幻思》(Rêve Parisien)中,當波德萊爾從印度大麻帶來的對金屬、大理石和水建成的人造都市的幻思裡醒來,在他的耳邊和眼前展現的是這樣的現實:
鐘擺以葬禮的聲調,
粗暴鳴響正午的時刻;
天空正傾瀉下陰暗,
向著沉鬱麻木的世界。
《巴黎幻思》由兩個詩章組成,這一節屬於第二個詩章。與懈怠之魔支配下的情形相比,在這裡,在同樣的正午,死亡取代了沉睡(在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神話裡,死亡之神與睡眠之神是孿生兄弟),陰暗取代了緩慢移動的太陽。陰暗,奈瓦爾所說的“陰暗”,當它傾瀉而下,吞噬了戈蒂耶所說的“沉鬱”,巴黎的正午於是就成了一個spleen的世界。
雖然在《巴黎幻思》中並沒有出現spleen的字眼,但是,對於波德萊爾來說,吸食印度大麻本身就是spleen的後果。在1851年3月發表的《論酒與印度大麻》(Du Vin et du haschisch)中,波德萊爾勸誡大家謹慎服用印度大麻時說:
您不要自己去做這種經歷,除非您有某種討厭的事情要完成,除非您的精神傾向於spleen,如除非您有一張期票要償付。
從這裡到《巴黎幻思》,潛存著一個完整的故事:因精神傾向於spleen而進入大麻的幻思,在幻思結束後面對著spleen的世界。當然也可以將這個故事倒過來講述,或者說這本來就是一個迴圈:正是因為世界的spleen,所以精神才傾向於spleen。
《論酒與印度大麻》是波德萊爾使用spleen一詞的開始。一個月以後,在“冥府”(Les Limbes)這一總標題下,波德萊爾發表了十一首詩,其中有三首題為“Spleen”。這三首詩,在1857年出版的《惡之花》中,有兩首分別被易名為“快樂的死者”(Le Mort joyeux)與“破裂的鐘”(Le cloche fêlée)。更改後的標題是對兩首詩的主題的分別的揭示,也是對spleen的含義的分別的解釋:一種特定形態的死亡與時間。而在那首保留著原來標題的詩中,這兩個元素匯入特定形態的空間,一個屬於波德萊爾的spleen的世界被第一次完整地呈現。《巴黎幻思》中的那支為正午報時的鐘擺(le pendule),先就是在這首詩中,發出了帶有傷風之音的悲鳴。且也正是在這裡,在這首詩的開頭,被稱為“雨月”的五月,面對使它感到氣惱的“整個城市”——
它從甕中把大量陰暗的寒冷,
灑向附近墓地的蒼白的亡魂
把一片死氣罩住多霧的市郊。
同《巴黎幻思》的第二個詩章一樣,在這裡,瀰漫著陰暗與死亡。且又如英國是“spleen的霧王國”,在這裡,巴黎被描寫為spleen的霧城市。彷彿是在英國與巴黎之間,spleen以霧為中介在傳遞。雖然直到1869年,波德萊爾才將他的散文詩集命名為“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但在波德萊爾的詞語使用當中,spleen這個英國病幾乎從一開始就屬於巴黎,屬於巴黎的“整個城市”。因而,那裡所呈現的,不僅是巴黎的spleen,還是spleen的巴黎,借用斯塔羅賓斯基在《鏡中的憂鬱》裡的說法,“spleen的地位是支配性的”。
“Spleen的地位是支配性的”,因為斯塔羅賓斯基發現,在《惡之花》中,它只出現於標題而不出現於詩句。但其實,在波德萊爾全部的寫作中,除了上文提到的“spleen的霧王國”與“精神傾向於spleen”,spleen均只被施用於標題。正是在標題這一位置上,spleen經歷著一場上升的運動:從《惡之花》中的篇名與專輯名,到《巴黎的憂鬱》這一書名。沿著spleen這一詞語上升的曲線,《巴黎的憂鬱》是《惡之花》的延伸,或者說,spleen(憂鬱)是mal(惡)的延伸,正如spleen是一種病(maladie),而maladie乃由多義的mal派生而成。事實上,在兩本書之間,兩個詞語在使用上形成了一種對蹠的關係:在《惡之花》中,spleen處於支配性的地位;而在“巴黎的憂鬱”這一更高的支配性下,到處都可看到mal或其派生詞的痕跡,如“塵世的罪惡(mal)”“在淒冷的悲慘之中侵襲我們的那種熱病(maladie)”以及“無法醫治,而且無可彌補”的“真正的痛苦(malheur)”。
在語義上,spleen與mélancolie處在同一個“憂鬱”的維度;但在結構上,spleen只關涉mélancolie的那個名為“痛苦”的區域性。之所以spleen會擠入mélancolie所曾佔據的表達的場域,是因為當後者從古代走入現代,它的二重性構造隨人類意志的分裂而分裂。只有少數人還擁有完整的憂鬱(mélancolie),而在多數人那裡,痛苦與幻思不再以矛盾的關係相互結合,而是以並置的形態彼此隔離。幻思不再是人們在痛苦中追求的目標,而是透過大麻、鴉片或酒所達到的虛假的效果。痛苦也不再是人們憑藉幻思所克服的物件,而是在當下的現實中所獲得的真實的體會。當痛苦失去來自幻思的彌補與醫治,mélancolie便無可挽回地轉化成了spleen。
憂鬱的(Spleen)正午,憂鬱的(Mélancolique)落日
在心理形態上,spleen是不再追求幻思的痛苦,於是在時間形態上,它便對應著無法抽出永恆性的現代性。“短暫、過渡、偶然”被推到了神聖的位置,且以物理的、機械的方式被打上了堅固的標記。時鐘作為計時的工具,贏得了主人的權力:在《惡之花》的《時鐘》(L'Horloge)一篇裡,波德萊爾將它稱作“恐怖的、無情的、不祥的神”。正是依賴於時鐘,時間在不同單位之間被反覆切分,從時到分,從分到秒,由此,一小時三千六百次——
現在一秒一秒都在發出強有力的莊嚴的聲響,從掛鐘上傳出的每一秒鐘的聲音都在叫著:“我就是‘生存’,難以忍受的、毫無寬容的‘生存’!”(《巴黎的憂鬱·二重的房間》[La Chambre double])
正是秒這一時間單位,標畫出了“偶然”的位置與“短暫”的長度,而秒與秒之間機械地轉換構成了“過渡”。每一秒都在喊叫,叫出的卻又是同樣的言語,於是“過渡”同時意味著重複——空洞的重複:“現在的時間被壓縮成一個數學的點,就是這個數學的點也在我們能夠肯定其產生之前消失過一千次。”(《人造天堂》)

雷克斯·惠斯勒(Rex Whistler)為波德萊爾的《時鐘》一詩所作的插畫(1924)
然而,被重複的不僅是時鐘上的每一秒,還有時鐘自身。那個在《惡之花》裡作為標題被書寫了一次的“時鐘”,在《巴黎的憂鬱》裡的標題位置上又出現了一次。而這一次它還帶來了兩個變體:貓的眼睛與貓一般的女人的眼睛。在那裡,從未使用過時鐘的中國小孩經由前者推知“現在還沒有完全到正午”,已習慣並厭倦了時鐘的詩人本人則從後者那裡看到“永恆”,看到“總是同樣的時辰”——
沒有分和秒的劃分,——不在任何時鐘上標明的靜止不動的時辰,可是,這種時辰,輕得像一聲嘆息,快得像眼睛的一瞥。(《巴黎的憂鬱·時鐘》)
在貓的眼睛與貓一般的女人的眼睛之間的是時鐘,於是在“還沒有完全到正午”的時刻與永恆之間的便是現代性。在這裡,詩人以“沒有”和“不”這樣否定意味的用詞,既把永恆放到了現代性的反面,同時又把現代性理解成了永恆的基準。這一永恆如同酒與大麻所製造的那個作為虛假效果的幻思,它受現代性的限制,是對現代性的顛倒。永恆的時間靜止不動但又短暫易逝:“快得像眼睛的一瞥”;現代性的時間短暫易逝但又靜止不動:在“分和秒的劃分”裡空洞地重複。現代性因此獲得了一個隱喻的形象,它是已經完全到來的正午,是歷史的正午,在這裡,時間因重複而形同靜止,就像在修道士那裡,正午的太陽因緩慢而狀若停滯。在《惡之花》的第四首以“Spleen”為題的詩裡,天空——
把整個地平線全部包圍,
降下比夜更沉鬱的黑晝;……
黑日在黑晝裡移動,留下的軌跡只是無差別的黑。分和秒的劃分只有數學的意義,以致承擔著報時功能的——
那些大鐘突然暴跳如雷,
向天空發出恐怖的怒吼,……
“憂鬱,在正午”,因而同時也就是“憂鬱,在現代”。正是由於正午與現代性之間的隱喻關係,波德萊爾才反覆地讚頌“午後”“黃昏”與“落日”。在他那裡,“午後”可以有永恆的性質與天堂的色彩,“黃昏”能夠安慰受劇烈苦楚折磨的靈魂,而“落日”,作為一個充滿了生命的靈魂的形象奉獻著幻思,引人歌唱祖先與往昔。尤其是“落日”,它一方面歸屬於浪漫派,在他們那裡,“蒙福的是能滿懷熱愛/向那比幻思更美的落日致禮的人”(《惡之花·浪漫派的落日》[Le Coucher du soleil romantique]);另一方面關聯著浪蕩子(le dandy),在他們身上——
浪蕩作風(Le dandysme)是一輪落日,猶如沉落的星辰,壯麗輝煌,沒有熱力,充滿了憂鬱(mélancolie)。(《現代生活的畫家》)
在波德萊爾的描述中,浪蕩子擁有閒暇與金錢,習慣於他人的服從,從愛情中體驗熱烈的或幻思式的任性,以衣著的絕對簡單證明自己的與眾不同。進而,波德萊爾斷言,浪蕩子是人類驕傲中最優秀的成分,是頹廢的英雄,他們有著挑釁的、高傲的態度,致力於反對與清除平庸。於是,dandy與dandysme,作為同樣借取自英語的單詞,與spleen之間形成了一種語義的與精神的張力。在剛剛的這一句引文中,以“浪蕩作風”為中介,“落日”與“憂鬱”被串接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種對立:spleen的正午,憂鬱的落日。
波德萊爾試圖以落日否定正午,以憂鬱對抗spleen,以幻思醫治並彌補痛苦,以永恆性超越並完成現代性。正因為此,他就像他所崇敬的美國作家愛倫·坡一樣,“是並將永遠是一位真正的詩人”——
他不願與眾人摩肩擦踵,當落日的地方燃起焰火時,他卻奔向極東的地方。(《再論埃德加·愛倫·坡》)
1867年8月31日上午十一時,波德萊爾以四十六歲的年齡,在他母親的懷中去世:他死於正午。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