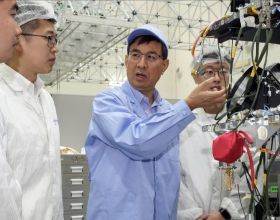五山文學是日本漢詩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其漢詩創作以鎌倉室町時代“五山十剎”的禪僧群體為主。以詩僧為主要創作群體的五山漢詩,與倡導“苦吟”、工於煉句的晚唐詩歌多有牽繫,尤其隨著五山後期社會動盪、禪林式微,詩僧心境與晚唐詩的衰颯習氣亦相契合。景徐周麟(1440—1518),號宜竹、半隱,近江(滋賀縣)人,著有《翰林葫蘆集》十七卷。上村觀光評價其集,在儲存史料的豐富性上可與義堂周信(1325—1388)的《空華集》相媲美;而在文學方面,則與橫川景三(1429—1493)的《京華集》一起,被視為文明(1469—1486)以後五山文學的代表性著述(上村觀光《翰林葫蘆集·解題》)。
景徐對晚唐詩歌的接觸,首先來自由南宋周弼編選、主要收錄中晚唐近體詩的《唐三體詩》。他憶及幼時從用堂中材學詩:“小子甫五歲,養於先師手。……教以梁千字文、唐三體詩及空和尚外集,皆俾背誦之,忘一字則賜一拳。”(“文明十八年二月住景德寺拈香”語)這種對《三體詩》的記誦濡染之功,於景徐後來的創作影響深遠。《三體詩》中清新淡遠、曉暢流麗的晚唐律、絕,尤其得到他的青睞,他總結偏愛的詩風即為“幽暢平淡”(《跋東山玉岑珍侍者百詩後》)、“清絕可愛,累累乎端如貫珠”(《光室字銘有序》)。這在景徐集中多有體現,其詩多處化用晚唐此類詩句。如“南朝古寺鐘聲遠,曉夢尚迷煙雨樓”(《便面春日廟》),乃化用杜牧《江南春》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見楓遠不上寒山,咫尺君家幾往還。此地停車無鳴道,風吹紅葉在松間”(《楓林停車》),則是句句對應杜牧《山行》;“曉風入夢奉天殿,殘月長庚夜夜心”(《送了庵和尚入大明國》),乃巧用李商隱《嫦娥》“長河漸落曉星沉”“碧海青天夜夜心”,表達對友人的思念。集中還有數首詩,對趙嘏的“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長安晚秋》),極盡模仿之能事。如“殘星數點故人在,一派銀河第五橋”(《星夕後逢故人》)、“玉樹一聲人倚樓,張妃酒醒髻鬟愁”(《玉樹後庭花》三首其二)、“殘星數點雁橫處,起託封書先問君”(《奉寄大明正使堆雲大和尚》)等等。在《又次前韻者五篇·其二》中,景徐周麟更直接以“殘星數點”形容晚唐詩:“諸老東西才折指,殘星數點晚唐詩。”此句一語雙關,一方面詩人為禪林的蕭條零落深感悽愴,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他心中的晚唐詩歌圖景——如“殘星數點”所描摹的,幽靜淡遠又不掩悽清衰颯之色。
因此,景徐周麟的漢詩創作,還承襲了晚唐詩寒僻蹇澀、尖新奇絕之一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對“寒”與“殘”二字的鐘愛。寒,既指體感之寒冽,也關取境之寒僻,是晚唐僧詩的一大特徵。景徐即有不少詩歌涉及“寒”境,如《爐存火似紅》:“五更吹火倚風爐,寒氣剝床先及膚。”《次月江試筆韻》:“未識青春度玉墀,餘寒思澀和詩遲。”《門前梅意》:“卻遭僧氣奪春去,月下敲門詩尚寒。”尤其後二首,已明顯透露出“郊寒島瘦”對其漢詩創作的影響,詩僧幽居的枯冷竟把春的暖意也奪去,只留下月下敲門的寒寂,想象可謂尖新。而與“殘”相關的意象,在景徐詩中也大量出現,包括殘夜、殘燈、殘星、殘夢、殘月、殘雨等20餘種,詩人竟以“殘僧”自謂。“殘”是一個極具時間性的詞彙,指將盡未盡、掙扎著存在卻終將湮滅的事物,體現出詩人的枯冷心境和對事物的觀照習性,這在“晚唐體”詩歌中即大量存在。如五代詩人李中就將“千里夢魂迷舊業,一城砧杵搗殘秋”(《海城秋夕寄懷舍弟》)、“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海上從事秋日書懷》)視為其最得意的詩句。景徐對“殘象”的偏愛,表明他刻意營造一種耽享其中的、寒僻奇絕的意境和愁緒,這既與其時代處境、詩僧身份相合,也與他對“晚唐體”的自覺取資有關。
此外,景徐周麟對晚唐詩風的接受,還體現在他對“苦吟”精神和煉字鍛句創作態度的推重。宋人有謂“苦吟不脫晚唐詩”(劉克莊《自勉》)、“(詩)至晚唐而工”(楊萬里《黃御史集序》),已指出晚唐詩人於苦吟中極鍛鍊之妙的創作特徵。景徐周麟亦不掩對這一姿態的效仿,如其《孤吟》:“天外片心堪細論,掉頭拍膝月黃昏”,寫覓詩的專注和得句的興奮;“青雲不負故人約,尚有敲門覓句僧”(《開窗宜月》)、“可遊月下推敲界,莫擲人間壒圾堆”(《答雲英》),則是用賈島“推敲”之典營造作詩的清雅興味。在景徐看來,“苦吟”並非是在痛苦窮困的境遇中作詩,而是指寫作過程中冥搜覓句的刻苦艱辛,是一種沉浸於“我”與自然興會無間、冥想推敲的狀態,所以他對“月下推敲”之典的運用,更多是標榜作詩時的專注和自得,而非將鉤章棘句作為最終的詩美理想。他在為彥龍周興(1458—1491)的文集作序時說道:“昔育王橫川(按:宋僧橫川如珙),其提唱盡去雕巧之弊,獨振古風,視彼宋末諸老鉤章棘句、攢花簇錦相尚者,如隔天淵。”(《半陶文集序》)“宋末諸老”指的是效仿“晚唐體”的“四靈”和江湖詩派。景徐認為他們雖追摹晚唐,但極盡雕巧藻繪之能事,喪失了詩歌應有的清新自然與吟詩的清雅自得。這又體現出他與“晚唐體”保持疏離的一面。
綜上可見,景徐周麟對晚唐詩風的體認是多向度、有選擇的,呈現在其創作實踐中,就是一種努力“折中”的接受觀念:既推崇晚唐清新流麗的近體詩風,也難以擺脫詩僧身份帶來的寒僻蹇澀傾向;既重視苦吟與煉字,又力求避免詩歌的雕琢痕跡,追求“清絕可愛”“詩於窮者愈清新”的詩美理想。
只是受限於身份和時代,理想和創作實踐的矛盾有時無法調和。景徐周麟那些寫寒殘之象、帶有僧詩“蔬筍氣”的作品並非都“清絕可愛”,因此他對“郊寒島瘦”又表現出極為矛盾的態度,並以一種“自嘲”的焦慮呈現出來。上文所引“月下推敲”是景徐對賈島吟詩雅興的讚賞,但在另一首詩中,賈島卻成為被嘲笑的酸寒之士:“堪笑酸寒賈吟佛,每年除夜祭詩神。”(《詩有神助》)那麼同樣“苦吟”的自己,便也成為嘲笑物件:“小立近花身入畫,欄干影瘦作詩僧。”(《月移花影》)“卻遭僧氣奪春去,月下敲門詩尚寒。”(《門前梅意》)這種自嘲,幾乎成為同時代詩僧“共享”的焦慮。如景徐的師長橫川景三,嘲己詩之“寒”:“寺有衰僧詩更寒”(《溪寺餘寒》)、“吾詩雖夏亦言寒”(《次韻惟賢藏主》)、“寒於東野是吾詩”(《扇面·孟郊看花圖》)。賈島在他筆下也被調侃道:“用盡黃金徒鑄像,唐成吟佛宋詩奴。”(《賈島佛》)“吟佛”賈島在宋人風雅面前,更像一個酸寒的“詩奴”,這種落差不可謂不大。大致同時的希世靈彥(1403—1488),也批評晚唐詩的寒澀難以延續李杜的“光焰萬丈”:“灞雪驢邊都滅卻,不傳妙處冷於灰。”(《詩燈》)但他的創作中卻也有如“宿火吹爐無小暖,疏星落壁有餘光”(《次韻叢侍者螢窗之作》)這樣蹇澀的詩句。
進一步言,“自嘲”的前提是承認有“相似”的一面,但又不是詩人理想的樣子,因為有更出色的模仿物件,所以造成一種“焦慮”。而這種更理想的模仿物件,就是以蘇軾、黃庭堅為代表的宋代詩人。自鎌倉末以降,蘇、黃之詩在五山詩壇幾成風靡之狀:“叢林之徒,兄玉堂而弟豫章,治之殆如治經,解注之繁,幾充棟宇。”(伊藤東涯《杜律詩話序》)與景徐周麟有交的諸僧,也多有講注蘇、黃者。受此風氣影響,景徐對風流閒雅的宋人風調頗為景慕,他評價蘇軾是“手提詩律唱諸儒,宋二百年唯兩蘇。”(《詩律到阿虎》)評黃庭堅是繼陶淵明之後的“第二達摩”:“誰知第一達摩髓,分付江西魯直詩。”(《又次韻歲寒老人達磨忌之作》)而《翰林葫蘆集》中也多有作品寫日常生活的閒散意趣,風格衝澹閒遠。這也就解釋了景徐周麟為何將“幽暢平淡”“清絕可愛”視為詩美追求,以及為何更青睞晚唐清新淡遠的詩歌,除了其禪宗背景,“宋調”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然蘇軾之橫邁超絕、山谷之學養富贍,和老杜的沉鬱頓挫一樣難以步趨,相較之下,晚唐詩的鍛鍊工穩則意味著有跡可循,可以之為門徑,溯源而上;而其清新幽遠亦可結合禪居生活,合其環境與心境,此時“晚唐”便成為詩僧們“倒逼”之下的詩風選擇。
總之,以景徐周麟為代表,後期五山詩壇對晚唐詩風的接受具有複雜性和多面性,慕其流暢婉麗、煉字工穩、尖新奇絕,卻又為無法擺脫枯槁寒澀的詩風而苦惱。這一方面緣於晚唐詩歌本身是一個多元化的效法物件,另一方面,也與景徐周麟的身份境遇、五山詩壇風行的“宋調”影響有關,體現出唐詩在日本漢詩創作實踐中產生的影響和流變,在某種意義上也開啟了後來江戶時期聲勢浩大的“唐宋詩之爭”。
(作者:劉曉,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師資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