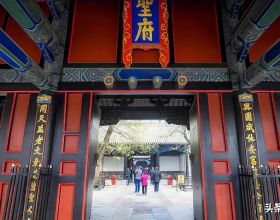孔氏家族係指以中國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為一世祖,以父系血緣關係為紐帶,逐漸子孫繁衍而形成的大家族,孔氏家族女性指孔子直系子孫的“妻”與“女”。秦漢以降,歷代帝王尊孔崇儒,對孔子後裔恩渥隆重。從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孔子第十三代孫孔霸獲賜“關內侯”、食邑八百戶以祀孔子(《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開始,孔子後裔獲得封爵以奉祀孔子延續近2000年。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願獲封“衍聖公”。其後,歷經宋、金、元、明、清和民國,至1935年方將這一封號改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其間,這一封號和爵位綿延八百餘年,雖屢經朝代更迭,孔氏家族卻世享“榮爵”,成就了其在中國古代社會“天下第一家”的傳奇。
孔子後裔,作為孔子身後榮爵的直接承襲者,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孔子和儒家文化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獨特象徵。與之相應,孔氏家族女性,作為孔子的女性後裔,亦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女性形象的標識。因此,藉助孔子女性後裔這一特殊群體,或可還原中國古代女性教育和生活的更多歷史側面。本文擬對清代孔氏家族的女子教育和女性詩人群體進行考察,藉此管窺清代乃至中國古代正統和主流的女教觀念與女性形象。
“詩禮傳家”的女子教育
春秋末年,孔子不僅設教杏壇,開私學之先河,亦授學子孫,創立孔氏家學。自孔鯉之後,孔氏後裔即將學詩習禮奉為祖訓,以傳承和發展儒學為己任,不僅在經學和文學等領域成就斐然,亦形成了“詩禮傳家”的家學傳統。
與之一脈相承,孔氏家族亦十分重視其女性成員的教育,這一點可從大量史料中得到印證。如孔子第75代女孫孔祥淑“六歲隨兄若弟,從袁石齋先生學”,“諸兄學詩,夫人亦詩;諸兄學文,夫人亦文”。15歲時,家人為其延請涇石公,學習“修己御眾之道”和“行文作詩之法”,“詩學大進”(劉樹堂:《孔夫人家傳·韻香閣詩草》)。可見,孔祥淑自幼即受學名師,並且與男性後裔接受了近乎相同的文學教育。又如第73代女孫孔璐華在《哭父六首》中有詩云:“痛想父言猶在耳,提攜親授國風篇。”並註解道:“餘幼年先君口誦國風,指而言曰:‘願汝他年能知此義。’”可見,她幼年時,父親即親授國風,督責女兒的教育。再如第68代女孫孔麗貞在《籍蘭閣草》的自序中稱:“餘幼居深閨中,蒙二親顧復,朝夕不離左右。每花晨月夕,吾父與伯兄,共四方執友,流連詩酒,竟日方休。我母,春則烹新茗,夏則設盆冰,秋則焚蘭香,冬則煮佳釀,以待吾父歸來。興若未闌,或評詩,或玩月,或理琴敲棋。”不難發現,這種與日常生活融為一體的文學交遊兼具教育功能,並向其女性成員“平等”開放。綜上可知,孔氏家族非常重視女孫的閨閣教育,或延聘名師、或父母親授、或在日常生活和人際交遊中教育習染,表現出對婦學和女教的高度重視。
此外,孔家女媳大多來自名門望族或書香門第,閨閣時期一般接受了良好的家族教育,于歸後,受孔氏家族推重婦學氛圍的影響和支援,往往迎來詩文創作的高峰期。如第66代女媳顏小來,“幼端慧,從父受書,旁及琴奕。夫既早亡,矢節甘貧,逾六十載”,與孔家女孫孔麗貞等時相唱和,有《恤緯齋詩》《晚香堂詞》行世。又如第67代“衍聖公”夫人葉粲英,早年“工詩善畫,與姊宏緗齊名,有‘閨中二難’之稱”,于歸孔家後,多有唱和之作,著有《繡餘草》《聽鳥草》(孔憲彝:《闕里孔氏詩鈔》)。另如第72代女媳朱璵,“功習詩詞、繪畫、隸楷”,其日常詩文及唱和之作結集為《小蓮花室遺稿》,並收錄多位孔家姻眾的題詩或評跋。
清人孔憲彝輯《闕里孔氏詩鈔》收錄孔家閨秀詩人18位,收其詩106首。其中,收錄女孫6位,詩作55首;女媳12位,詩作51首。作為孔氏家族的家集,《詩鈔》對閨秀詩作的公開選錄和刊刻,清晰闡明瞭孔氏家族的立場:作為孔子的女性後裔,孔氏家族女性亦是孔氏家學的重要繼承者和傳揚者。因此,無論是對其“為女”之時文學教育的重視,抑或是對其“為妻”“為母”之後文學才華和文學聲名的獎掖,均體現了“詩禮傳家”的女子教育風習。
女性詩人的大量出現
正是由於孔氏家族對女子教育的重視和女性才學的獎掖,使有清一代孔氏家族湧現出大量女性詩人。據現有史料,可考者40餘位,包括孔麗貞、孔素瑛、孔傳蓮、孔繼孟等孔家女孫,以及顏小來、葉粲英、蔣玉媛、葉俊傑等孔家女媳各20餘人。每人均有詩詞專集或詩作行世,共計刊刻詩詞專集30餘部,僅現存詩作即逾千首,其日常創作當更為豐富。她們的詩詞作品不僅在家族內部流傳,亦在社會公共領域獲得了較大範圍傳播:地方誌廣泛著錄,並列入《藝文志》,如《續修曲阜縣志·藝文志》收錄18位,收其詩50餘首。入選清代頗具影響力的詩詞選集,如《國朝山左詩鈔》(含續鈔和鈔後集)收錄12位,收其詩40餘首;《晚晴簃詩匯》收錄12位,收其詩50餘首;《國朝詞綜》(含續編)收錄4位,收其詞5首。入選清代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女性詩歌總集,如《擷芳集》收錄7位,收其詩30餘首;《國朝閨秀正始集》(含續集)收錄11位,收其詩15首;《國朝閨秀詩柳絮集》(含校補)收錄28位,收其詩140餘首。部分女性詩集被《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收錄,少數女性詩集得到清代重要文人為之作序,並獲極高讚譽。如該提要評價孔麗貞《鵠吟集》“其所為詩,清麗絕俗,聲律允諧,為閨閣中不可多得者”、孔璐華《唐宋舊經樓詩稿》“是編所收詠事、詠物、即景、抒懷之作,兼而有之,收集之富,實為閨閣中罕見者”。另如孔祥淑的《韻香閣詩草》得到清代著名文人鄒振嶽、趙實、劉印庚等為其作序。其中,桐城派後期重要代表人物吳汝綸盛讚其詩曰:“於雕刻山川、憑弔厄塞之作,以為古所稱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者,殆不是過。”
儘管清代是女性文學,尤其是家族女性文學異常繁榮的時期,但在一族之內出現如此眾多的女性詩人,且幾乎人人能詩,人人有集,詩詞創作數量之豐,文學水平之高,傳播之廣遠,依然罕見。
博學多才與女性意識
孔氏家族女性不僅在詩詞等文學領域成果豐碩,而且博學多才,涉及經史、書法、繪畫、醫藥、篆刻和音律等諸多領域。如孔淑成“工書善弈,通經史,年七歲即能詩”(孔憲彝:《闕里孔氏詩鈔》);孔素瑛“精小楷”,工寫山水畫畢“即題詩自書之,時稱‘三絕’,片紙人爭寶貴”(《國朝閨秀正始集》卷一);孔蘭英“工繪事”,“其《漢宮春曉圖》工緻微妙,必傳之作”(《國朝閨秀正始集》卷十二);顏小來“既侍夫及舅姑疾,博涉方書,常自制丸散,以濟鄉里之煢獨者”;孫苕玉“通書史,解音律”,“荃溪從伯所制樂府,皆為按拍,令諸婢歌之”(孔憲彝:《闕里孔氏詩鈔》)。
此外,孔氏家族女性在踐履婦德規範同時,又表現出比較清晰的女性意識。具體表現為:其一,她們以“女史”自稱和互稱,對自古以來的婦學傳統進行自覺梳理,並將自身置於其中,為女性的文學行為尋求淵源流自。如葉俊傑在《學靜軒遺詩》的序中稱:“讀《山左詩鈔》,如趙雲庭、周淑履諸女史,皆足繼古名媛。叔凝之詩,未知與諸家何如?”寥寥數筆即點出源遠流長的婦學傳統,並將孔淑成(字叔凝)置於其中。其二,她們依託血緣和姻親關係,透過詩詞唱和、歌詠題跋、結社交遊等文學活動,組成了一個孔氏家族女性詩人群,於閉塞的閨閣之外,建構了一個開闊豐富的精神空間。如朱璵“年二十歸孔氏”,與葉俊傑“初執弟子禮,繼則情同母女。”(朱璵:《序·小蓮花室遺稿》)其三,她們從女性視角出發,批評忽視或歧視女性的現象,表現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少數女性甚至表露一定的平權意識,發為近代兩性教育平權的先聲。如孔璐華反對將安史之亂歸咎於楊貴妃:“君主誤在漁陽事,空把傾城咎婦人。”又如葉俊傑公開批評北方不重閨秀詩作,孔淑成卒後,她聯合孫會祥、朱璵等孔家女性為其搜撿遺篇,編成《學靜軒遺詩》,併為之校對、刊刻、作序和題詩,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女性意識和聲名觀念。另如,孔祥淑七歲時,面對先生所說:“爾讀書不過記名姓耳,不似爾弟兄博取科名也”,問道:“不科名即不讀書耶?”“曉義理何分兒女耶?”(劉樹堂:《孔夫人家傳·韻香閣詩草》)從日後行跡來看,其才學和心志亦超出對傳統性別規制的簡單遵從。
綜上所述,與清代一些保守文人力倡“才可妨德”“才高累德”,甚至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而排斥婦學和女教不同,孔氏家族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婦女德才兼收幷蓄、相得益彰的融通態度,從而為孔氏家族女性的文學成就及多方面發展提供了可能,進而培育出卓然而立的女性詩人群體。
(作者:姜麗靜 吳佩林,均系曲阜師範大學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案“孔子直系女性後裔德育生活史研究”〔BEA160075〕階段性成果)